
精神康复之路的探寻 一筱敏散文阅读札记 李新宇 在刚刚过去的世纪里,人类经历了太多的灾难:两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 义、文化大革命、红色高棉.人类象走入一片屠宰场。这一切都是伴随着一场人类文明史 上罕见的精神瘟疫进行的 感谢上帝对人类的春 20世纪结束 优美的姿势,昭示 着健康终将战胜疾病。因此,全人类都有充分的理由为新世纪的到来而欢呼。但是,清醒的 人们应该意识到,瘟疫过后会留下一片什么样的疫区,如果得不到消毒处理,将会如何长期 威胁着人们的健康。因此,走出精神疫区,实现精神康复,显然是全球知识分子在告别20 世纪之际不应忘记的重大课题。 ,中国作家在这一重大课题面前的表现如何?回答的确不容乐观。但是,考察当下 散文创作 却不难发现一些作家所表现出的深沉思考和由此显示的责任感 在这些作家中 筱敏毫无疑问是个性鲜明而成绩显著的一位。 在此之前,我没有看见哪一位中国作家如此全面而系统地思考过20世纪人类所经历的 灾难,也没有看见哪一位女性作家有如此充分的知识准备和精神资源来把挥这场灾难。在我 的间读经验中 ,当代散文作家很善于抒发一般的情感,表现一般的情趣,或者刻意创造一种 所谓情景交融的境界 90年代的女性散文则更喜 展示自己手袋中那些小 。然而, 敏给文坛带来的不是这些,而是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上,通过一篇篇散文建构 个宏大的历 史空间和思想空间,全面而深入地揭示了20世纪人类遗遇的灾难特别是精神瘟疫的场景。 从希特勒到斯大林,从纳粹到文革,从俄罗斯作家伟岸的身影到我们自己的卑微和怯懦 她不是在书写,而是手持一支烛光,洞穿被遮蔽的历史,帮助人们恢复失掉的记忆:是使我 们爬到枪杆的顶端 瞰者甲板上和船舱里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人群,看我们是怎样疯狂 怎样失掉理智和选择的能力,而最终是怎样造就自身的悲剧。穿越疫区 寻求精神康复之路 筱敏集学者和作家的使命于一身,默默地承担了这一时代最为严峻的课题,在烦为孤独的路 上,进行了独到的探求。 人类在20世纪到底遭调了什么?是什么给人类带来如此百大的灾难?被敏的思考是 从法西斯主义开始的。在二战之后的辞典里, “法西斯 一词早已臭各昭著,但是,法西斯 义并未消失, 法西 暴行屡见 。也许正因为如此,筱敏没有满足于对法西斯主义的 批判,而是从个人的生命体验出发,注目于一些容易忽略的事实。在《群众汪洋》中,她考 察“法西斯”一词:“它原指捆在一起的一束棍棒,中间插一柄斧头,是古罗马高官的权力标 志,象征若万众团结一致,服从一个意志,一个权力。”二战之后的人们当然清楚那把斧头的 罪恶,但筱敏提醒人们的是,那捆棍棒比斧头更值得注意。因为希特勒及其纳粹党是在人民 的拥戴之下上台的: 上台之后消灭其他政党而实行 甚至解散工 取缔罢工, 杀犹太人 这一切都没有遇到抵抗。当时的“人民”在哪里?原来这个空洞的庞然大物并 不对任何事件负贵。它具有巨大的力量,却没有自己的意志。借助对纳粹时代的反思,筱敏 提出:“时至今日,我们究竞应该怎样描述极权统治下的人民群众呢?事实上,大多数德国人 并不在乎他们的个人自由遭到剥夺,他们似乎并不感到专制制度的残忍,相反,却怀着真正 的热情支持这个政权。”当然,原因并不复杂,因为这个政府消灭了失业,带来了表面的平等 而且许诺了国家和民族的富强。在它的统治下, 工人虽然失掉了自己的工会,却不再担心自 己的饭碗。贫穷常常是统治者所求之不得的,因为饭碗往往比任何东西都更有号召力和胁迫 力。如果能够成功地收缴人们的饭碗,然后再根据需要发成,不仅可以顺利地建立极权主义 统治,而且足以调动起民众的热情
精神康复之路的探寻 ——筱敏散文阅读札记 李新宇 在刚刚过去的世纪里,人类经历了太多的灾难:两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 义、文化大革命、红色高棉.人类象走入一片屠宰场。这一切都是伴随着一场人类文明史 上罕见的精神瘟疫进行的。感谢上帝对人类的眷顾,20世纪结束于一个优美的姿势,昭示 着健康终将战胜疾病。因此,全人类都有充分的理由为新世纪的到来而欢呼。但是,清醒的 人们应该意识到,瘟疫过后会留下一片什么样的疫区,如果得不到消毒处理,将会如何长期 威胁着人们的健康。因此,走出精神疫区,实现精神康复,显然是全球知识分子在告别20 世纪之际不应忘记的重大课题。 那么,中国作家在这一重大课题面前的表现如何?回答的确不容乐观。但是,考察当下 散文创作,却不难发现一些作家所表现出的深沉思考和由此显示的责任感。在这些作家中, 筱敏毫无疑问是个性鲜明而成绩显著的一位。 在此之前,我没有看见哪一位中国作家如此全面而系统地思考过20世纪人类所经历的 灾难,也没有看见哪一位女性作家有如此充分的知识准备和精神资源来把握这场灾难。在我 的阅读经验中,当代散文作家很善于抒发一般的情感,表现一般的情趣,或者刻意创造一种 所谓情景交融的境界,90年代的女性散文则更喜欢展示自己手袋中那些小零碎。然而,筱 敏给文坛带来的不是这些,而是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上,通过一篇篇散文建构了一个宏大的历 史空间和思想空间,全面而深入地揭示了20世纪人类遭遇的灾难特别是精神瘟疫的场景。 从希特勒到斯大林,从纳粹到文革,从俄罗斯作家伟岸的身影到我们自己的卑微和怯懦. 她不是在书写,而是手持一支烛光,洞穿被遮蔽的历史,帮助人们恢复失掉的记忆;是使我 们爬到桅杆的顶端,俯瞰着甲板上和船舱里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人群,看我们是怎样疯狂, 怎样失掉理智和选择的能力,而最终是怎样造就自身的悲剧。穿越疫区,寻求精神康复之路, 筱敏集学者和作家的使命于一身,默默地承担了这一时代最为严峻的课题,在颇为孤独的路 上,进行了独到的探求。 人类在20世纪到底遭遇了什么?是什么给人类带来如此巨大的灾难?筱敏的思考是 从法西斯主义开始的。在二战之后的辞典里,“法西斯”一词早已臭各昭著,但是,法西斯主 义并未消失,法西斯暴行屡见不鲜。也许正因为如此,筱敏没有满足于对法西斯主义的一般 批判,而是从个人的生命体验出发,注目于一些容易忽略的事实。在《群众汪洋》中,她考 察“法西斯”一词:“它原指捆在一起的一束棍棒,中间插一柄斧头,是古罗马高官的权力标 志,象征着万众团结一致,服从一个意志,一个权力。”二战之后的人们当然清楚那把斧头的 罪恶,但筱敏提醒人们的是,那捆棍棒比斧头更值得注意。因为希特勒及其纳粹党是在人民 的拥戴之下上台的;上台之后消灭其他政党而实行一党专制,甚至解散工会,取缔罢工,屠 杀犹太人.这一切都没有遇到抵抗。当时的“人民”在哪里?原来这个空洞的庞然大物并 不对任何事件负责。它具有巨大的力量,却没有自己的意志。借助对纳粹时代的反思,筱敏 提出:“时至今日,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描述极权统治下的人民群众呢?事实上,大多数德国人 并不在乎他们的个人自由遭到剥夺,他们似乎并不感到专制制度的残忍,相反,却怀着真正 的热情支持这个政权。”当然,原因并不复杂,因为这个政府消灭了失业,带来了表面的平等, 而且许诺了国家和民族的富强。在它的统治下,工人虽然失掉了自己的工会,却不再担心自 己的饭碗。贫穷常常是统治者所求之不得的,因为饭碗往往比任何东西都更有号召力和胁迫 力。如果能够成功地收缴人们的饭碗,然后再根据需要发放,不仅可以顺利地建立极权主义 统治,而且足以调动起民众的热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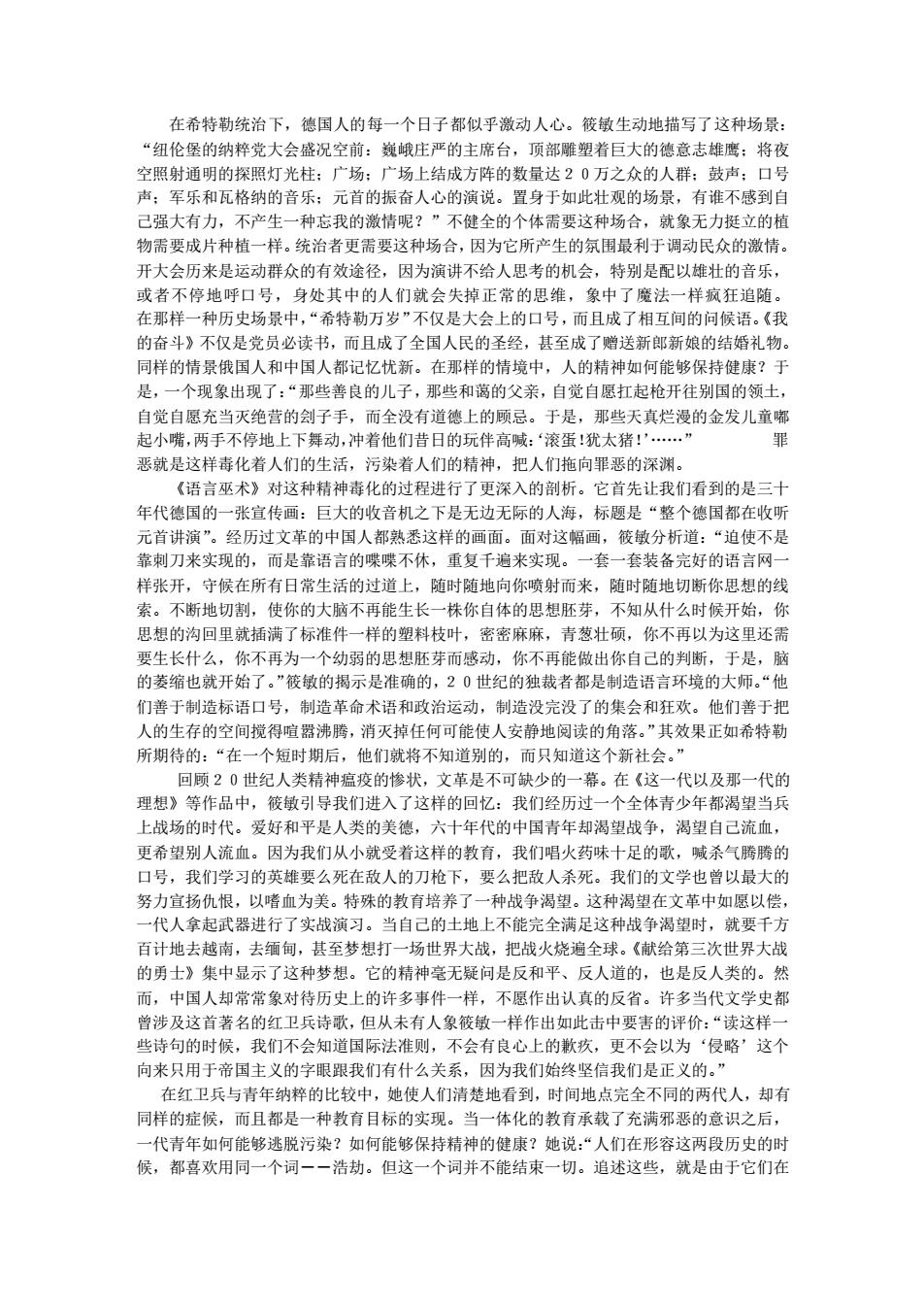
在希特勒统治下,德国人的每一个日子鄂似乎激动人心。笼嫩生动地描写了这种场晷 “纽伦堡的纳粹党大会盛况空前:巍峨庄严的主席台,顶部雕塑者巨大的德意志雄鹰:将夜 空照射通明的探照灯光柱 场上结成方 为数量达20万之众的人群 ,盐 :口号 声:军乐和瓦格纳的音乐:元首的振奋人心的演说。置身于如此壮观的场景,有谁不感到自 己强大有力,不产生一种忘我的激情呢? 不健全的个体需要这种场合,就象无力挺立的植 物需要成片种描一样。统治者更需要这种场合,因为它所产生的氛围最利干调动民众的意情 开大会历来是运动群众的有效途径,因为演讲不给人思考的机会,特别是配以雄壮的音乐 身处其中的人们就会失掉正常的 思维 在那样 种历史场景 希特勒万岁 不仅 的口号,而且成了相互间的问候语。 《我 的奋斗》不仅是党员必读书,而且成了全国人民的圣经,甚至成了赠送新郎新娘的结婚礼物 同样的情景俄国人和中国人都记忆忧新。在那样的情境中,人的精神如何能够保持健康?于 是,一个现象出现了:“那些善良的儿子,那些和蔼的父亲,自觉自愿扛起枪开往别国的领土, 自觉自愿充当灭绝营的剑子手,而全没有道德上的顾忌。 于是,那些天真烂漫的金发儿童 小嘴,两手不停 地上下舞动,冲若他们昔日 的玩件 喊:‘滚蛋:犹太猪! 恶就是这样毒化者人们的生活,污染者人们的精神,把人们拖向罪恶的深渊。 《语言巫术》对这种精神毒化的过程进行了更深入的剖析。它首先让我们看到的是三十 年代德国的一张宣传画:巨大的收音机之下是无边无际的人海,标题是“整个德国都在收听 玩首进溶”。经历讨文革的中国人都熟采这样的画面。面对这幅画,敏分折道:“使不月 靠刺刀来实现的,而是靠语言的喋喋不休,重复千遍来实现 套装备完好的语言网 样张开,守候在所有日常生活的过道上,随时随地向你喷射而来,随时随地切断你思想的线 索。不断地切割,使你的大脑不再能生长一株你自体的思想胚芽,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你 思想的沟回里就插满了标准件一样的塑料枝叶,密密麻麻,青葱壮硕,你不再以为这里还需 要生长什么,你不面为一个幼弱的思相麻芽而成动,你不面能做出你自已的判斯,干是, 的菱缩也就开始了。”筱敏的揭示是准确的,20世纪的独裁者都是制造语言环境的大师。“他 们善于制造标语口号 制造革命术语和政治运动, 制造没完没了的集会和狂欢 他们善于把 人的生存的空间搅得喧需沸腾,消灭掉任何可能使人安静地阅读的角落。”其效果正如希特物 所期待的:“在一个短时期后,他们就将不知道别的,而只知道这个新社会。 回顾20世纪人类结神瘟疫的惨状,文革是不可缺少的一幕。在《这一代以及那一代的 理想》等作品中,筱敏引导我们进入了这样的回忆:我们经历过一个全体青少年都渴望当兵 上战场的时代。 爱好和平是人类的美德, 六十年代的中国青年却渴望战争 渴望自己流 更希望别人流血。因为我们从小就受者这样的教有,我们唱火药味十足的歌,喊杀气腾腾的 口号,我们学习的英雄要么死在敌人的刀枪下,要么把敌人杀死。我们的文学也曾以最大的 努力宜扬仇恨,以塔血为美。特殊的教有培养了一种战争渴望。这种渴望在文革中如愿以偿 一代人拿起武器进行了实战演习。当自己的土地上不能完全满足这种战争渴望时,就要千方 百计地去越南,去缅甸,甚至梦想打一场世界大战,把战火烧遍全球。《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 的勇士》集中显示了这种梦 它的精神毫无疑问是反和平、 反人道的,也是反人类的。然 而,中国人却常常象对待历史上的许多事件一样,不属作出认真的反省。许多当代文学史都 曾涉及这首著名的红卫兵诗歌,但从未有人象筱敏一样作出如此击中要害的评价:“读这样 些诗句的时候,我们不会知道国际法准则,不会有良心上的歉疚,更不会以为‘侵略’这个 向来只用于帝国主义的字眼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始终坚信我们是正义的。” 在红卫兵与青年纳粹的比较中,她使人们清楚地看到, 对间地点完全不同的两代人,却有 同样的症候,而且都是一种教有目标的实现。当一体化的教有承载了充满邪恶的意识之后 一代青年如何能够逃脱污染?如何能够保持精神的健康?她说:“人们在形容这两段历史的时 候,都喜欢用同一个词一一浩劫。但这一个词并不能结束一切。追述这些,就是由于它们在
在希特勒统治下,德国人的每一个日子都似乎激动人心。筱敏生动地描写了这种场景: “纽伦堡的纳粹党大会盛况空前:巍峨庄严的主席台,顶部雕塑着巨大的德意志雄鹰;将夜 空照射通明的探照灯光柱;广场;广场上结成方阵的数量达20万之众的人群;鼓声;口号 声;军乐和瓦格纳的音乐;元首的振奋人心的演说。置身于如此壮观的场景,有谁不感到自 己强大有力,不产生一种忘我的激情呢?”不健全的个体需要这种场合,就象无力挺立的植 物需要成片种植一样。统治者更需要这种场合,因为它所产生的氛围最利于调动民众的激情。 开大会历来是运动群众的有效途径,因为演讲不给人思考的机会,特别是配以雄壮的音乐, 或者不停地呼口号,身处其中的人们就会失掉正常的思维,象中了魔法一样疯狂追随。 在那样一种历史场景中,“希特勒万岁”不仅是大会上的口号,而且成了相互间的问候语。《我 的奋斗》不仅是党员必读书,而且成了全国人民的圣经,甚至成了赠送新郎新娘的结婚礼物。 同样的情景俄国人和中国人都记忆忧新。在那样的情境中,人的精神如何能够保持健康?于 是,一个现象出现了:“那些善良的儿子,那些和蔼的父亲,自觉自愿扛起枪开往别国的领土, 自觉自愿充当灭绝营的刽子手,而全没有道德上的顾忌。于是,那些天真烂漫的金发儿童嘟 起小嘴,两手不停地上下舞动,冲着他们昔日的玩伴高喊:‘滚蛋!犹太猪!’.” 罪 恶就是这样毒化着人们的生活,污染着人们的精神,把人们拖向罪恶的深渊。 《语言巫术》对这种精神毒化的过程进行了更深入的剖析。它首先让我们看到的是三十 年代德国的一张宣传画:巨大的收音机之下是无边无际的人海,标题是“整个德国都在收听 元首讲演”。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都熟悉这样的画面。面对这幅画,筱敏分析道:“迫使不是 靠刺刀来实现的,而是靠语言的喋喋不休,重复千遍来实现。一套一套装备完好的语言网一 样张开,守候在所有日常生活的过道上,随时随地向你喷射而来,随时随地切断你思想的线 索。不断地切割,使你的大脑不再能生长一株你自体的思想胚芽,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你 思想的沟回里就插满了标准件一样的塑料枝叶,密密麻麻,青葱壮硕,你不再以为这里还需 要生长什么,你不再为一个幼弱的思想胚芽而感动,你不再能做出你自己的判断,于是,脑 的萎缩也就开始了。”筱敏的揭示是准确的,20世纪的独裁者都是制造语言环境的大师。“他 们善于制造标语口号,制造革命术语和政治运动,制造没完没了的集会和狂欢。他们善于把 人的生存的空间搅得喧嚣沸腾,消灭掉任何可能使人安静地阅读的角落。”其效果正如希特勒 所期待的:“在一个短时期后,他们就将不知道别的,而只知道这个新社会。” 回顾20世纪人类精神瘟疫的惨状,文革是不可缺少的一幕。在《这一代以及那一代的 理想》等作品中,筱敏引导我们进入了这样的回忆:我们经历过一个全体青少年都渴望当兵 上战场的时代。爱好和平是人类的美德,六十年代的中国青年却渴望战争,渴望自己流血, 更希望别人流血。因为我们从小就受着这样的教育,我们唱火药味十足的歌,喊杀气腾腾的 口号,我们学习的英雄要么死在敌人的刀枪下,要么把敌人杀死。我们的文学也曾以最大的 努力宣扬仇恨,以嗜血为美。特殊的教育培养了一种战争渴望。这种渴望在文革中如愿以偿, 一代人拿起武器进行了实战演习。当自己的土地上不能完全满足这种战争渴望时,就要千方 百计地去越南,去缅甸,甚至梦想打一场世界大战,把战火烧遍全球。《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 的勇士》集中显示了这种梦想。它的精神毫无疑问是反和平、反人道的,也是反人类的。然 而,中国人却常常象对待历史上的许多事件一样,不愿作出认真的反省。许多当代文学史都 曾涉及这首著名的红卫兵诗歌,但从未有人象筱敏一样作出如此击中要害的评价:“读这样一 些诗句的时候,我们不会知道国际法准则,不会有良心上的歉疚,更不会以为‘侵略’这个 向来只用于帝国主义的字眼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始终坚信我们是正义的。” 在红卫兵与青年纳粹的比较中,她使人们清楚地看到,时间地点完全不同的两代人,却有 同样的症候,而且都是一种教育目标的实现。当一体化的教育承载了充满邪恶的意识之后, 一代青年如何能够逃脱污染?如何能够保持精神的健康?她说:“人们在形容这两段历史的时 候,都喜欢用同一个词――浩劫。但这一个词并不能结束一切。追述这些,就是由于它们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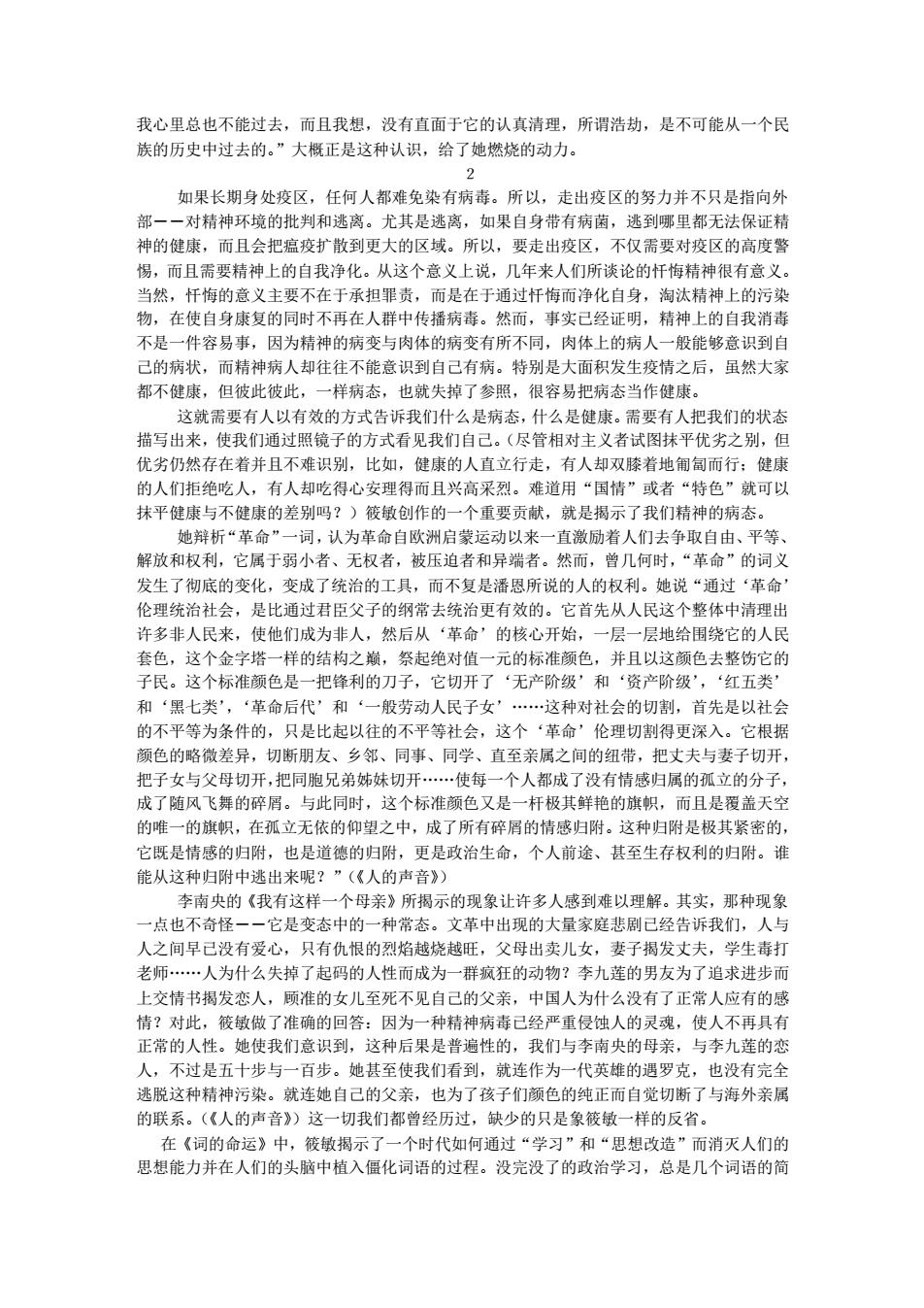
我心里总也不能过去,而且我想,没有直面于它的认真清理,所谓浩劫,是不可能从一个民 族的历史中过去的。”大概正是这种认识,给了她燃烧的动力 如果长期身处疫区,任何人都难免染有病毒。所以,走出疫区的努力并不只是指向外 部 一对精神环境的批判和逃离。尤其是逃离,如果自身带有病菊,逃到那里都无法保证精 神的健康,而且会把瘟疫扩散到更大的区域。所以,要走出疫区,不仅需要对疫区的高度警 惕,而且需要精神上的自我净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几年来人们所谈论的杆悔精神很有意义 杆悔的意义 在于通过杆悔而净化白身 淘汰精神 上的污 物,在使自身康复的同时不再在人群中传播病毒。然而,事实己经证明,精神上的自我消毒 不是一件容易事,因为精神的病变与肉体的病变有所不同,肉体上的病人一般能够意识到自 己的病状,而精神病人却往往不能意识到自己有病。特别是大面积发生疫情之后,虽然大家 都不能康,但彼此彼此,一样病态。也就失掉了参照,很容易把病态当作键康。 这就需要有人以有效的方式告诉我们什么是病态,什么是健康。需要有人把我们的状态 描写出来,使我们通过照镜子的方式看见我们自 (尽管相对主义者试图抹平优劣之别,但 优劣仍然存在者并且不难识别,比如,健康的人直立行走,有人却双膝着地匍匐而行:健康 的人们拒绝吃人,有人却吃得心安理得而且兴高采列。难道用“围情”或者“特色”就可以 抹平健康与不健康的差别吗?)筱敏创作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揭示了我们精神的病态。 她避折“盒”一词认为革白败洲启装运动以来 一有励若人们去角取自由、平 解放和权利,它属于弱小者 无权者 ,被压迫者和异端者 。然而,曾几何时 命”的词义 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变成了统治的工具,而不复是潘恩所说的人的权利。她说“通过 ‘革命 伦理统治社会,是比通过君臣父子的纲常去统治更有效的。它首先从人民这个整体中清理出 许多非人民来,使他们成为非人,然后从‘革命'的核心开始,一层一层地给围绕它的人民 伍,这个金字搭 一样的结构之巅,祭起绝对值一元的标准颜色,并且以这颜色去整饬它的 子民。这个标准颜色是 一把锋利的刀子 它切开了‘无产阶级 和‘资产阶级 ‘红五类 和‘黑七类, ‘革命后代’和 一股劳动人民子女 这种对社会的切割,首先是以社会 的不平等为条件的,只是比起以往的不平等社会,这个‘革命’伦理切割得更深入。 它根拒 颜色的略微差异,切断朋友、乡邻、同事、同学、直至亲属之间的纽带,把丈夫与妻子切开 把子女与父母切开,把同胞兄弟纯妹切开 ·使每一个人都成了没有情感归属的孤立的分子 成了随风飞舞的碎屑。与此同时,这个标准颜色又是一杆极其鲜艳的旗帜。 而日是覆盖天 的唯 一的旗 在孤立无依的仰望之中, 成了所有碎屑的情感归附。这种归附 是极其紧密的 它既是情感的归附,也是道德的归附,更是政治生命,个人前途、甚至生存权利的归附。谁 能从这种归附中逃出来呢?”(《人的声音》) 李南央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所揭示的现象让许多人感到难以理解。其实,那种现象 ,占出不资溪 它是变本中的 一种常态。文革中出现的大量家庭悲剧已经告诉我们,人与 人之间早已没有爱心,只有仇恨的烈焰越烧越旺 父母出卖儿女 妻子揭发丈 老师.人为什么失掉了起码的人性而成为一群疯狂的动物?李九莲的男友为了追求进步而 上交情书揭发恋人,顾准的女儿至死不见自己的父亲,中国人为什么没有了正常人应有的感 情?对此,筱敏做了准确的回答:因为一种精神病毒已经亚重侵蚀人的灵魂,使人不再具有 正常的人性。她使我们意识到,这种后果是普端性的,我们与李南央的母亲,与李九莲的心 人,不过是五十 与一百步 。她甚至使我们看到,就连作为一代英雄的遇罗克,也没有完全 逃脱这种精神污染。就连她自己的父亲,也为了孩子们颜色的纯正而自觉切断了与海外亲属 的联系。(《人的声音》)这一切我们都曾经历过,缺少的只是象筱敏一样的反省。 在《词的命运》中,筱敏揭示了一个时代如何通过“学习”和“思想改造”而消灭人们的 思想能力并在人们的头脑中植入僵化词语的过程。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总是几个词语的简
我心里总也不能过去,而且我想,没有直面于它的认真清理,所谓浩劫,是不可能从一个民 族的历史中过去的。”大概正是这种认识,给了她燃烧的动力。 2 如果长期身处疫区,任何人都难免染有病毒。所以,走出疫区的努力并不只是指向外 部――对精神环境的批判和逃离。尤其是逃离,如果自身带有病菌,逃到哪里都无法保证精 神的健康,而且会把瘟疫扩散到更大的区域。所以,要走出疫区,不仅需要对疫区的高度警 惕,而且需要精神上的自我净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几年来人们所谈论的忏悔精神很有意义。 当然,忏悔的意义主要不在于承担罪责,而是在于通过忏悔而净化自身,淘汰精神上的污染 物,在使自身康复的同时不再在人群中传播病毒。然而,事实已经证明,精神上的自我消毒 不是一件容易事,因为精神的病变与肉体的病变有所不同,肉体上的病人一般能够意识到自 己的病状,而精神病人却往往不能意识到自己有病。特别是大面积发生疫情之后,虽然大家 都不健康,但彼此彼此,一样病态,也就失掉了参照,很容易把病态当作健康。 这就需要有人以有效的方式告诉我们什么是病态,什么是健康。需要有人把我们的状态 描写出来,使我们通过照镜子的方式看见我们自己。(尽管相对主义者试图抹平优劣之别,但 优劣仍然存在着并且不难识别,比如,健康的人直立行走,有人却双膝着地匍匐而行;健康 的人们拒绝吃人,有人却吃得心安理得而且兴高采烈。难道用“国情”或者“特色”就可以 抹平健康与不健康的差别吗?)筱敏创作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揭示了我们精神的病态。 她辩析“革命”一词,认为革命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一直激励着人们去争取自由、平等、 解放和权利,它属于弱小者、无权者,被压迫者和异端者。然而,曾几何时,“革命”的词义 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变成了统治的工具,而不复是潘恩所说的人的权利。她说“通过‘革命’ 伦理统治社会,是比通过君臣父子的纲常去统治更有效的。它首先从人民这个整体中清理出 许多非人民来,使他们成为非人,然后从‘革命’的核心开始,一层一层地给围绕它的人民 套色,这个金字塔一样的结构之巅,祭起绝对值一元的标准颜色,并且以这颜色去整饬它的 子民。这个标准颜色是一把锋利的刀子,它切开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红五类’ 和‘黑七类’,‘革命后代’和‘一般劳动人民子女’.这种对社会的切割,首先是以社会 的不平等为条件的,只是比起以往的不平等社会,这个‘革命’伦理切割得更深入。它根据 颜色的略微差异,切断朋友、乡邻、同事、同学、直至亲属之间的纽带,把丈夫与妻子切开, 把子女与父母切开,把同胞兄弟姊妹切开.使每一个人都成了没有情感归属的孤立的分子, 成了随风飞舞的碎屑。与此同时,这个标准颜色又是一杆极其鲜艳的旗帜,而且是覆盖天空 的唯一的旗帜,在孤立无依的仰望之中,成了所有碎屑的情感归附。这种归附是极其紧密的, 它既是情感的归附,也是道德的归附,更是政治生命,个人前途、甚至生存权利的归附。谁 能从这种归附中逃出来呢?”(《人的声音》) 李南央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所揭示的现象让许多人感到难以理解。其实,那种现象 一点也不奇怪――它是变态中的一种常态。文革中出现的大量家庭悲剧已经告诉我们,人与 人之间早已没有爱心,只有仇恨的烈焰越烧越旺,父母出卖儿女,妻子揭发丈夫,学生毒打 老师.人为什么失掉了起码的人性而成为一群疯狂的动物?李九莲的男友为了追求进步而 上交情书揭发恋人,顾准的女儿至死不见自己的父亲,中国人为什么没有了正常人应有的感 情?对此,筱敏做了准确的回答:因为一种精神病毒已经严重侵蚀人的灵魂,使人不再具有 正常的人性。她使我们意识到,这种后果是普遍性的,我们与李南央的母亲,与李九莲的恋 人,不过是五十步与一百步。她甚至使我们看到,就连作为一代英雄的遇罗克,也没有完全 逃脱这种精神污染。就连她自己的父亲,也为了孩子们颜色的纯正而自觉切断了与海外亲属 的联系。(《人的声音》)这一切我们都曾经历过,缺少的只是象筱敏一样的反省。 在《词的命运》中,筱敏揭示了一个时代如何通过“学习”和“思想改造”而消灭人们的 思想能力并在人们的头脑中植入僵化词语的过程。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总是几个词语的简

单重复:没完没了的所谓讨论,说的总是相同的词语,的确机械而又乏味。然而,不要小看 这种虚伪的形式主义的东西,因为正是它导致了一种精神病变:“那些铺天盖地的运动,最终 但它们那种铺天盖地的锤 千遍万遍的锤打,到底已经把某出 逻辑、某些词,象楔子一样锤进了我们的头脑,以致那里许多年之后,都 块夯实了的地 还布满禊子,什么种子也播不下去。”这些楔子因其自身的性质而与现代化格格不入, 与人类 文明的健康主流格格不入,如果不能拔除,就会长期阻挡健康肌体的生长。在文章的最后, 被敏说:“我母亲在闭国的生存条件下学习·了一子,改浩·了一裴子,现在地老了 那此年复一年中她的吃子的 已经在那里淤积,使其硬化了,再也没有张开的可能了 我比她幸运 点儿的是 今天我还可能选择 一把凿子 点 点儿地清除我 子里的淤 物,使其不至于硬化成石。”用凿子清除我们大脑中的淤积物, 是筱敏为我们提供的一条精祥 康复之路。而她的文章本身,就常常是给予我们的“凿子”。 ,筱敏对俄罗斯作家及其承载的精神传统怀有深深的散意 显然, 这种敏意产生于一种孤独中的寻找 在《救援之手》中,筱敏写道:“在巨大的生存威胁面前,的确有许多人 这些人几 乎在任何时候都是多数一 一是屈从的,是纵容和散播‘丑陋的信仰”的,甚至是助纣为虑的, 但一个民族的精神高度,从来只能由另一些人去标识。”这另一些人是哪些人呢?筱敏看到了 “不合时宜”的高尔基。在十月革命那场无法可循的镇压中,高尔基曾经试图以个人的力量 造一只方舟,以营救那些濒临死亡的作家、学者和科学家 尽管高尔基后来的表现令人遗憾 但是,历史的确不应忘记他曾经有过的挣扎。他自己虽然深陷水中,但当他看到洪流将淹没 文明,自己参与的运动呈现出反人道面目的时候,仍然无法完全保持沉默。她看到了帕斯捷 尔纳卓。他是那样忧郁,那样沉默而且代柔宾断,很难被想象为横刀立马的英雄。但是。当 他听说诗人曼德尔施搭姆被捕的消息,他立即跑去找布哈林,在电话里与斯大林激列争辩, 表示他愤怒,沿有任何怯。在大读捕的年代里 ,有人迎合最高当局的意志而在作家当中组 织签名 表示拥护当局判处图哈切夫斯基等人死刑。帕斯捷尔 纳拒绝签名,他说:“就让那利 命运也轮到我头上好啦,我完全情愿死去。”他不会不明白,他签名和不签名并不能改变图哈 切夫等人的命云,但是,他仍然这样做了,为了人的尊严。在这些人身上,筱敏找到的,正 是人作为人应该有的一种人格。很显然,在中国,这种人格太少了。可是,正因为太少, 个民族就几乎谈不到什么结神高度 她赞扬奥威尔 因为奥威尔的《动物农庄》和《1984》所写的,并不是 一个假想的 言,而是一段真实的历史。奥威胁尔把极权者许诺的伊甸园一片一片解剖开来,使人们看到 了可怕的恐怖景象。筱敏则在奥威尔笔锋剖开的地方再进一步展开,把我们从·个作家在1 948年的想象带到了我们经历过的现实。 她赞美札米亚京,津津乐道他的《洞穴》和《我们》。因为札米亚京以他的敏感和真诚成 对“唯一国”的“符号”们的命运作了准确的预见,对“至高恩主”建立起的社会秩序有者 准确而深刻的洞察。札米亚京的作品写于1921年到1922年, 当时还很少有人意识至 这种危险,但是,请醒的作家己经向人类发出了警告。通过这样一些作品的介绍和评论,被 敏展示了俄罗斯先觉者伟大的身影。同时,它使人们不能不想,为什么他们能够那样敏感地 发现那些危险,而中国的一般作家却不能?为什么他们能够作顽强的精神坚守,而中国的作 家却不能?仅仅是因为外部力量的强大吗?筱敏写道:“每一块土地都生长杂草,每一场风暴 流沙 些士地是只配杂草 和流沙的,偶有 两株乔木灌木 也很快就超 化或枯死。而另一些士地,却总会有高大的树木站立起来,于是当风暴米袭,这里除了杂草 流沙琐琐碎碎战战兢兢的声音以外,还会有大树的声音。这是因为士土地自身不同的质地。”的 确,在俄罗斯,极权主义统治是那样残酷,然而,健康的因子并没有因为时间而被消灭,而
单重复;没完没了的所谓讨论,说的总是相同的词语,的确机械而又乏味。然而,不要小看 这种虚伪的形式主义的东西,因为正是它导致了一种精神病变:“那些铺天盖地的运动,最终 也随生产流水线流过去了,但它们那种铺天盖地的锤打,千遍万遍的锤打,到底已经把某些 逻辑、某些词,象楔子一样锤进了我们的头脑,以致那里许多年之后,都是一块夯实了的地, 还布满楔子,什么种子也播不下去。”这些楔子因其自身的性质而与现代化格格不入,与人类 文明的健康主流格格不入,如果不能拔除,就会长期阻挡健康肌体的生长。在文章的最后, 筱敏说:“我母亲在闭阖的生存条件下‘学习’了一辈子,‘改造’了一辈子,现在她老了。 那些年复一年冲刷她的脑子的词,已经在那里淤积,使其硬化了,再也没有张开的可能了。 我比她幸运一点儿的是,今天我还可能选择一把凿子,一点儿一点儿地清除我脑子里的淤积 物,使其不至于硬化成石。”用凿子清除我们大脑中的淤积物,是筱敏为我们提供的一条精神 康复之路。而她的文章本身,就常常是给予我们的“凿子”。 3 象刘烨园、摩罗等人一样,筱敏对俄罗斯作家及其承载的精神传统怀有深深的敬意。 显然,这种敬意产生于一种孤独中的寻找。 在《救援之手》中,筱敏写道:“在巨大的生存威胁面前,的确有许多人――这些人几 乎在任何时候都是多数――是屈从的,是纵容和散播‘丑陋的信仰’的,甚至是助纣为虐的, 但一个民族的精神高度,从来只能由另一些人去标识。”这另一些人是哪些人呢?筱敏看到了 “不合时宜”的高尔基。在十月革命那场无法可循的镇压中,高尔基曾经试图以个人的力量 造一只方舟,以营救那些濒临死亡的作家、学者和科学家。尽管高尔基后来的表现令人遗憾, 但是,历史的确不应忘记他曾经有过的挣扎。他自己虽然深陷水中,但当他看到洪流将淹没 文明,自己参与的运动呈现出反人道面目的时候,仍然无法完全保持沉默。她看到了帕斯捷 尔纳克。他是那样忧郁,那样沉默而且优柔寡断,很难被想象为横刀立马的英雄。但是,当 他听说诗人曼德尔施塔姆被捕的消息,他立即跑去找布哈林,在电话里与斯大林激烈争辩, 表示他愤怒,没有任何怯懦。在大逮捕的年代里,有人迎合最高当局的意志而在作家当中组 织签名,表示拥护当局判处图哈切夫斯基等人死刑。帕斯捷尔纳拒绝签名,他说:“就让那种 命运也轮到我头上好啦,我完全情愿死去。”他不会不明白,他签名和不签名并不能改变图哈 切夫等人的命运,但是,他仍然这样做了,为了人的尊严。在这些人身上,筱敏找到的,正 是人作为人应该有的一种人格。很显然,在中国,这种人格太少了。可是,正因为太少,一 个民族就几乎谈不到什么精神高度。 她赞扬奥威尔,因为奥威尔的《动物农庄》和《1984》所写的,并不是一个假想的预 言,而是一段真实的历史。奥威胁尔把极权者许诺的伊甸园一片一片解剖开来,使人们看到 了可怕的恐怖景象。筱敏则在奥威尔笔锋剖开的地方再进一步展开,把我们从一个作家在1 948年的想象带到了我们经历过的现实。 她赞美札米亚京,津津乐道他的《洞穴》和《我们》。因为札米亚京以他的敏感和真诚, 对“唯一国”的“符号”们的命运作了准确的预见,对“至高恩主”建立起的社会秩序有着 准确而深刻的洞察。札米亚京的作品写于1921年到1922年,当时还很少有人意识到 这种危险,但是,清醒的作家已经向人类发出了警告。通过这样一些作品的介绍和评论,筱 敏展示了俄罗斯先觉者伟大的身影。同时,它使人们不能不想,为什么他们能够那样敏感地 发现那些危险,而中国的一般作家却不能?为什么他们能够作顽强的精神坚守,而中国的作 家却不能?仅仅是因为外部力量的强大吗?筱敏写道:“每一块土地都生长杂草,每一场风暴 都制造流沙,.但是,一些土地是只配杂草和流沙的,偶有一两株乔木灌木,也很快就矮 化或枯死。而另一些土地,却总会有高大的树木站立起来,于是当风暴来袭,这里除了杂草 流沙琐琐碎碎战战兢兢的声音以外,还会有大树的声音。这是因为土地自身不同的质地。”的 确,在俄罗斯,极权主义统治是那样残酷,然而,健康的因子并没有因为时间而被消灭,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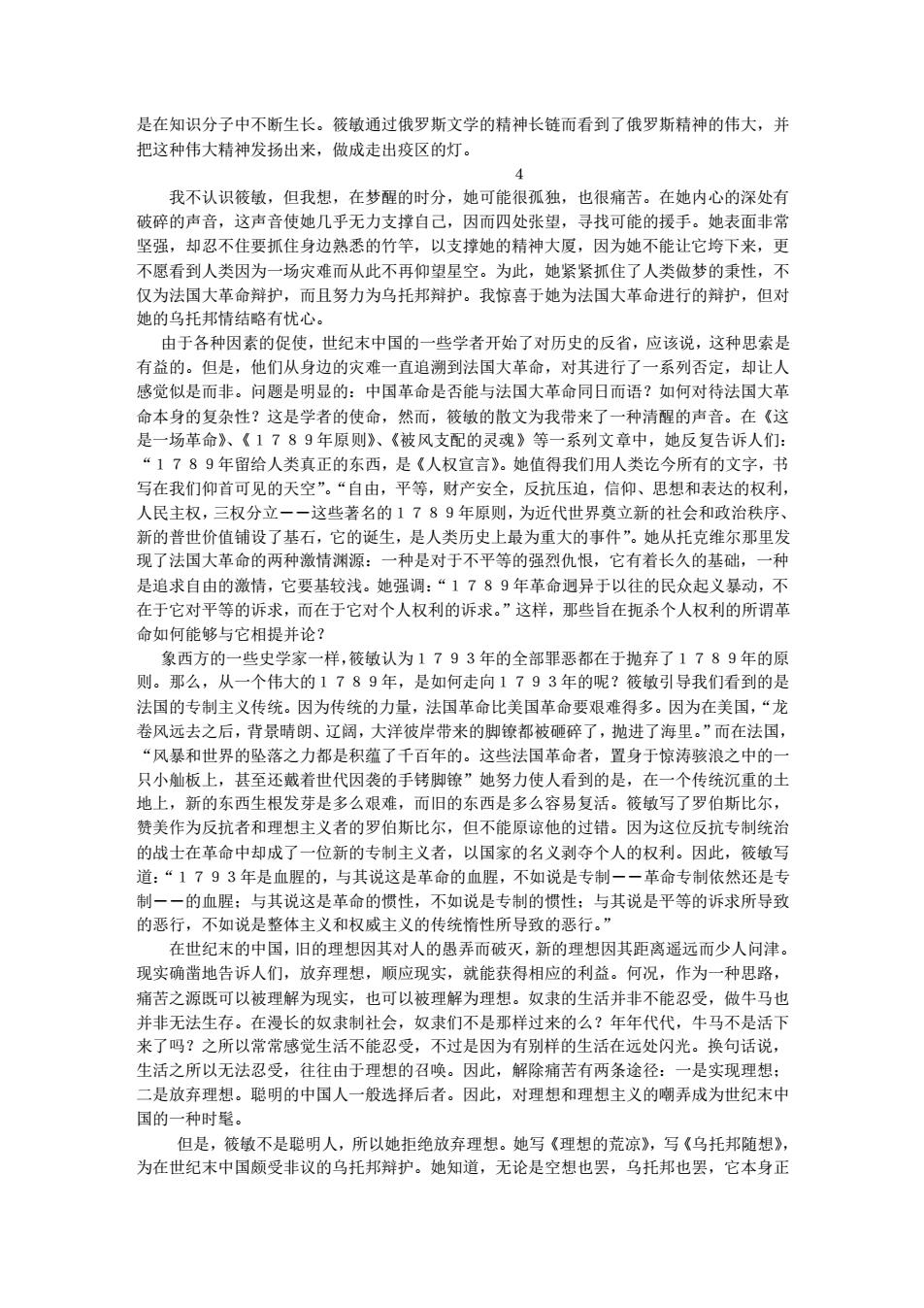
是在知识分子中不断生长。筱敏通过俄罗斯文学的精神长链而看到了俄罗斯精神的伟大,并 把这种伟大精神发扬出来,做成走出疫区的灯。 我不认识筱敏,但我想,在梦醒的时分,她可能很孤独,也很痛苦。在她内心的深处有 破碎的声音,这声音使她几平无力支撑自己,因而四处张望,寻找可能的援手。她表面非常 坚强,却忍不住要抓住身边熟悉的竹竿,以支撑她的精神大厦,因为她不能让它垮下来,更 不愿看到人类因为一场灾难而从此不再仰望星空。为此,她紧紧抓住了人类做梦的秉性,不 仅为法国大革命辩扩 而且努力为乌托邦辩护。我惊喜于她为法国大革命进行的护,但对 她的乌托邦情结略有忧 由于各种因素的促使,世纪末中国的一些学者开始了对历史的反省,应该说,这种思索是 有益的。但是,他们从身边的灾难一直追溯到法国大革命,对其进行了一系列否定,却让人 感微似是而非。问题是明显的:中国革命是否能与法国大革命同日而语?如何对待法国大革 命本身的复杂性?这是学者的 然而,筱敏的散文为我带来了 种清醒的声音。 在(这 一场革命》、 89年原则》、《被风支配的灵魂》等 一系列文章中,她反复告诉人们 1789年留给人类真正的东西,是《人权宣言》。她值得我们用人类讫今所有的文字,书 写在我们仰首可见的天空”。“自由,平等,财产安全,反抗压迫,信仰、思想和表达的权利, 人民主权,三权分立一一这些著名的】789年原则,为近代世界奠立新的社会和政治秩序 新的普世价值铺设了基石,它的诞生,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重大的事件”。她从托克维尔那里发 现了法国大革命的两种激行 种是对于不平等的强烈仇恨, 它有若长久的基础 是追求自由的激情,它要基较浅。她强调:“1789年革命迥异于以往的民众起义暴动,不 在于它对平等的诉求,而在于它对个人权利的诉求。”这样,那些旨在扼杀个人权利的所谓革 命如何能够与它相提并论? 象西方的一些史学家一样,筱敏认为1793年的全部罪恶都在于抛弃了1789年的原 则。那么 从一个伟大的1789年 是如何走向1793年的呢?筱敏引导我们看到的是 法国的专制主义传统。因为传统的力量,法国革命比美国革命要艰难得多。因为在美国,“龙 卷风远去之后,背景晴朗、辽阔,大洋彼岸带来的脚獠都被砸碎了,抛进了海里。”而在法国, “风暴和世界的坠落之力都是积蕴了千百年的。这些法国革命者,置身于惊涛骇浪之中的 只小射板上,其至还戴著世代因的手储脚”努力使人看到的是,在 一个传统沉重的土 地上,新的东西生根发芽是多么限难,而旧的东西是多么容易复活。敏写了罗伯比尔 赞美作为反抗者和理想主义者的罗伯斯比 尔,但不能原谅他的过错。因为这位反抗专制统 的战士在革命中却成了一位新的专制主义者,以国家的名义剥夺个人的权利。因此,筱敏写 道:“1793年是血眠的,与其说这是革命的血腥,不如说是专制一一革命专制依然还是专 制一一的血腥:与其说这是革命的惯性,不如说是专制的惯性:与其说是平等的诉求所导致 的恶行,不如说是整体主义和权威主义的传统惰性所导致的恶行。” 在世纪末的中国,旧的理想因其对人的愚弄而破灭 新的理想因其距离遥远而少人问津 现实确凿地告诉人们,放弃理想,顺应现实,就能获得相应的利益。何况,作为一种思路 痛苦之源既可以被理解为现实,也可以被理解为理想。奴隶的生活并非不能忍受,做牛马也 并非无法生存。在漫长的奴隶制社会,奴隶们不是那样过米的么?年年代代,牛马不是活下 米了吗?之所以常常感觉生活不能忍受,不过是因为有别样的生活在远处闪光。换句话说, 生活之所以无法忍受,往往由于理想的召唤。 因出 解除痛苦有两条途径 是实现理想 是放弃理想。聪明的中国人一般选择后者。因此,对理想和理想主义的嘲弄成为世纪末中 国的一种时髦。 但是,筱敏不是聪明人,所以她拒绝放弃理想。她写《理想的荒凉》,写《乌托邦随想》, 为在世纪末中国颇受非议的乌托邦辩护。她知道,无论是空想也罢,乌托邦也罢,它本身正
是在知识分子中不断生长。筱敏通过俄罗斯文学的精神长链而看到了俄罗斯精神的伟大,并 把这种伟大精神发扬出来,做成走出疫区的灯。 4 我不认识筱敏,但我想,在梦醒的时分,她可能很孤独,也很痛苦。在她内心的深处有 破碎的声音,这声音使她几乎无力支撑自己,因而四处张望,寻找可能的援手。她表面非常 坚强,却忍不住要抓住身边熟悉的竹竿,以支撑她的精神大厦,因为她不能让它垮下来,更 不愿看到人类因为一场灾难而从此不再仰望星空。为此,她紧紧抓住了人类做梦的秉性,不 仅为法国大革命辩护,而且努力为乌托邦辩护。我惊喜于她为法国大革命进行的辩护,但对 她的乌托邦情结略有忧心。 由于各种因素的促使,世纪末中国的一些学者开始了对历史的反省,应该说,这种思索是 有益的。但是,他们从身边的灾难一直追溯到法国大革命,对其进行了一系列否定,却让人 感觉似是而非。问题是明显的:中国革命是否能与法国大革命同日而语?如何对待法国大革 命本身的复杂性?这是学者的使命,然而,筱敏的散文为我带来了一种清醒的声音。在《这 是一场革命》、《1789年原则》、《被风支配的灵魂》等一系列文章中,她反复告诉人们: “1789年留给人类真正的东西,是《人权宣言》。她值得我们用人类讫今所有的文字,书 写在我们仰首可见的天空”。“自由,平等,财产安全,反抗压迫,信仰、思想和表达的权利, 人民主权,三权分立――这些著名的1789年原则,为近代世界奠立新的社会和政治秩序、 新的普世价值铺设了基石,它的诞生,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重大的事件”。她从托克维尔那里发 现了法国大革命的两种激情渊源:一种是对于不平等的强烈仇恨,它有着长久的基础,一种 是追求自由的激情,它要基较浅。她强调:“1789年革命迥异于以往的民众起义暴动,不 在于它对平等的诉求,而在于它对个人权利的诉求。”这样,那些旨在扼杀个人权利的所谓革 命如何能够与它相提并论? 象西方的一些史学家一样,筱敏认为1793年的全部罪恶都在于抛弃了1789年的原 则。那么,从一个伟大的1789年,是如何走向1793年的呢?筱敏引导我们看到的是 法国的专制主义传统。因为传统的力量,法国革命比美国革命要艰难得多。因为在美国,“龙 卷风远去之后,背景晴朗、辽阔,大洋彼岸带来的脚镣都被砸碎了,抛进了海里。”而在法国, “风暴和世界的坠落之力都是积蕴了千百年的。这些法国革命者,置身于惊涛骇浪之中的一 只小舢板上,甚至还戴着世代因袭的手铐脚镣”她努力使人看到的是,在一个传统沉重的土 地上,新的东西生根发芽是多么艰难,而旧的东西是多么容易复活。筱敏写了罗伯斯比尔, 赞美作为反抗者和理想主义者的罗伯斯比尔,但不能原谅他的过错。因为这位反抗专制统治 的战士在革命中却成了一位新的专制主义者,以国家的名义剥夺个人的权利。因此,筱敏写 道:“1793年是血腥的,与其说这是革命的血腥,不如说是专制――革命专制依然还是专 制――的血腥;与其说这是革命的惯性,不如说是专制的惯性;与其说是平等的诉求所导致 的恶行,不如说是整体主义和权威主义的传统惰性所导致的恶行。” 在世纪末的中国,旧的理想因其对人的愚弄而破灭,新的理想因其距离遥远而少人问津。 现实确凿地告诉人们,放弃理想,顺应现实,就能获得相应的利益。何况,作为一种思路, 痛苦之源既可以被理解为现实,也可以被理解为理想。奴隶的生活并非不能忍受,做牛马也 并非无法生存。在漫长的奴隶制社会,奴隶们不是那样过来的么?年年代代,牛马不是活下 来了吗?之所以常常感觉生活不能忍受,不过是因为有别样的生活在远处闪光。换句话说, 生活之所以无法忍受,往往由于理想的召唤。因此,解除痛苦有两条途径:一是实现理想; 二是放弃理想。聪明的中国人一般选择后者。因此,对理想和理想主义的嘲弄成为世纪末中 国的一种时髦。 但是,筱敏不是聪明人,所以她拒绝放弃理想。她写《理想的荒凉》,写《乌托邦随想》, 为在世纪末中国颇受非议的乌托邦辩护。她知道,无论是空想也罢,乌托邦也罢,它本身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