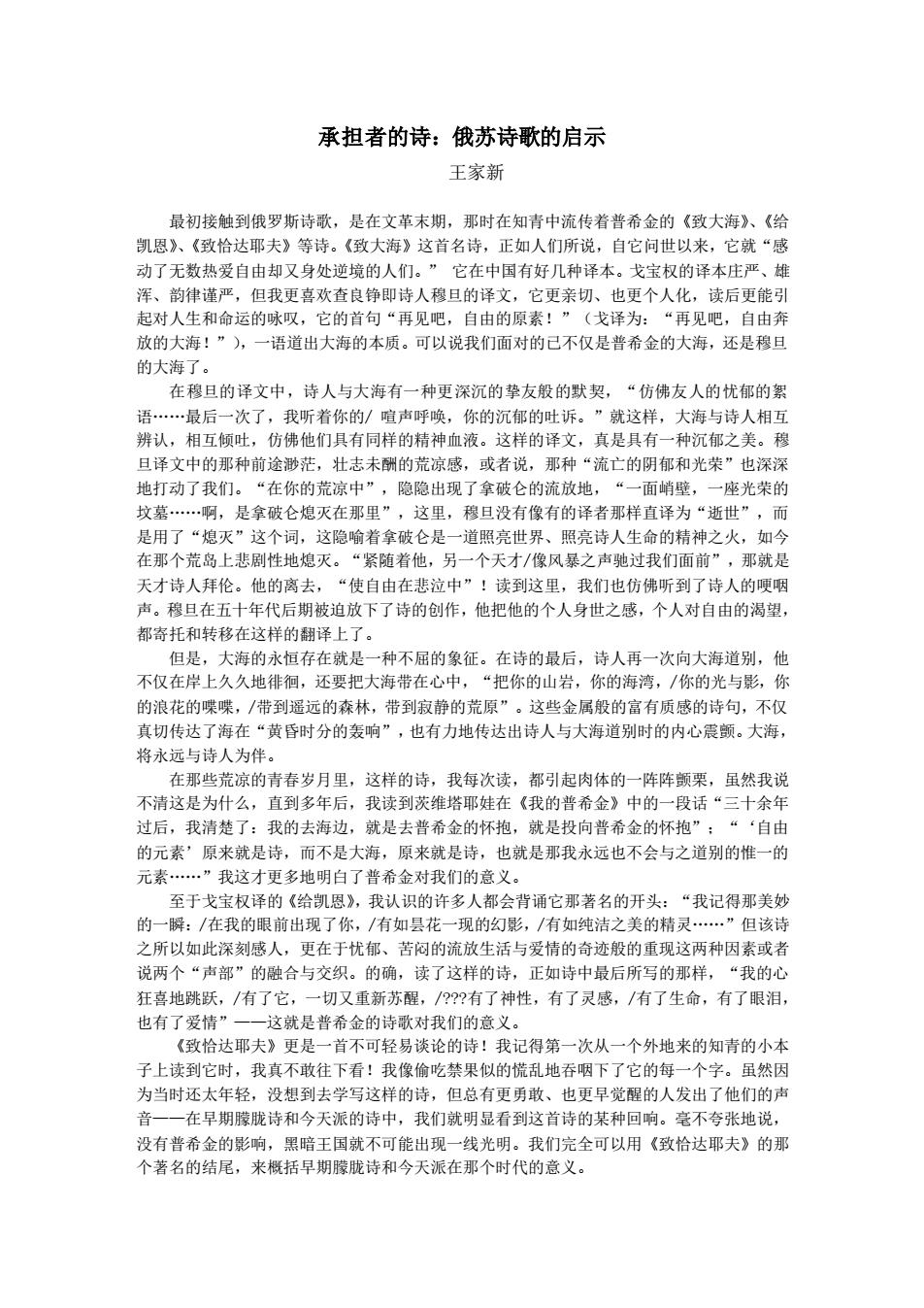
承担者的诗:俄苏诗歌的启示 王家新 最初接触到俄罗斯诗歌,是在文革末期,那时在知青中流传者普希金的《致大海》、《给 凯恩》、《致恰达耶夫》等诗。《致大海》这首名诗,正如人们所说,自它问世以来,它就“感 动了无热爱自由却又身处逆墙的人们。”它在中国有好几种译木。戈宝权的译木庄亚、雄 浑、韵律谨严 但我更喜欢查良铮即诗人穆旦的译文 更亲切、也更个人化,读后更能引 起对人生和命运的咏叹 它的首句“再见吧,自由的原素! (戈译为: 见吧,自由 放的大海!”),一语道出大海的本质。可以说我们面对的己不仅是普希金的大海,还是穆旦 的大海了。 在隐且的译文中,诗人与大海有一种更深沉的挚友般的默契,“仿佛友人的忧郁的 语.最后一次了,我听你的/喧声呼唤,你的沉郁的吐诉。”就这样 大海与诗人相互 辨认,相互倾吐,仿佛他们具有同样的精 ,真是具有一种沉郁之美】 旦译文中的那种前途渺茫,壮志未酬的荒凉感,或者说,那种 “流亡的阴郁和光荣”也深深 地打动了我们。“在你的荒凉中”,隐隐出现了拿破仑的流放地, 一面增壁, 一座光荣的 坟墓.啊,是拿破仑熄灭在那里”,这里,穆旦没有像有的译者那样直译为“逝世”,而 是用了“熄灭”这个词,这隐哈若盒破仑是一道照亮世界、照亮诗人生命的精神之火,加今 在那个岛上非剧性地灭。“紧若他 ,另一个天才/像风暴之声驰过我们面前”,那就是 天才诗人拜伦。他的离去 “使自由在悲泣中” 读到这里,我们也仿佛听到了诗人的哽咽 声。穆旦在五十年代后期被迫放下了诗的创作,他把他的个人身世之感,个人对自由的渴望, 都寄托和转移在这样的翻译上了。 但是,大海的永恒存在就是一种不屈的象征。在诗的最后,诗人再一次向大海道别,他 不仅在岸上久久地徘徊,还要把大海带在心中,“把你的山岩,你的海湾,/你的光与影,你 的浪花的喋噪 /带到遥远的森林,带到寂静的荒原 这 金属般的富有质感的诗句, 不仅 真切传达了海在“黄昏时分的轰响 ,也有力地传达出诗人与大海道别时的内心震颤。大海, 将永远与诗人为伴。 在那些荒凉的青春岁月里,这样的诗,我每次读,都引起肉体的一阵阵颜栗,虽然我说 不清这是为什么,直到多年后,我读到茨维塔耶娃在《我的普希金》中的一段话“三十余年 过后,我清楚了:我的去海边,就是去普希金的怀抱,就是投向普希金的 怀抱” “‘自由 的元素’原来就是诗,而不是大海,原来就是诗,也就是那我永远也不会与之道别的惟一的 元素.”我这才更多地明白了普希金对我们的意义。 至于戈宝权译的《给凯恩》,我认识的许多人都会背诵它那著名的开头:“我记得那美妙 的一瞬:/在我的眼前出现了你,/有如县花一现的幻影,/有如纯洁之美的精灵.”但该诗 之所以如此深刻感人,更在于忧郁、苦闷的流放生活与爱情的奇迹般的重现这两种因素或者 说两个“声部”的融合与交织。的确,读了这样的诗, 正如诗中最后所写的那样 “我的心 狂喜地跳跃,/有了它,一切又重新苏醒,??有了神性,有了灵感,/有了生命,有了眼泪, 也有了爱情” 一这就是普希金的诗歌对我们的意义。 《致恰达耶夫》更是一首不可经易谈论的诗!我记得第一次从一个外地来的知青的小本 子上读到它时,我真不敢往下看!我像偷吃禁果似的慌乱地吞咽下了它的每一个字。虽然因 轻, 没想到去学写这样的诗,但总有更勇敢 也更早觉醒的人发出了他们的 为当时期酸戴诗和今天派的诗中,我们就明显看到这首诗的某种回响。毫不夸张地烫 没有普希金的影响,黑暗王国就不可能出现一线光明。我们完全可以用《致恰达耶夫》的那 个著名的结尾,来概括早期朦胧诗和今天派在那个时代的意义
承担者的诗:俄苏诗歌的启示 王家新 最初接触到俄罗斯诗歌,是在文革末期,那时在知青中流传着普希金的《致大海》、《给 凯恩》、《致恰达耶夫》等诗。《致大海》这首名诗,正如人们所说,自它问世以来,它就“感 动了无数热爱自由却又身处逆境的人们。” 它在中国有好几种译本。戈宝权的译本庄严、雄 浑、韵律谨严,但我更喜欢查良铮即诗人穆旦的译文,它更亲切、也更个人化,读后更能引 起对人生和命运的咏叹,它的首句“再见吧,自由的原素!”(戈译为:“再见吧,自由奔 放的大海!”),一语道出大海的本质。可以说我们面对的已不仅是普希金的大海,还是穆旦 的大海了。 在穆旦的译文中,诗人与大海有一种更深沉的挚友般的默契,“仿佛友人的忧郁的絮 语.最后一次了,我听着你的/ 喧声呼唤,你的沉郁的吐诉。”就这样,大海与诗人相互 辨认,相互倾吐,仿佛他们具有同样的精神血液。这样的译文,真是具有一种沉郁之美。穆 旦译文中的那种前途渺茫,壮志未酬的荒凉感,或者说,那种“流亡的阴郁和光荣”也深深 地打动了我们。“在你的荒凉中”,隐隐出现了拿破仑的流放地,“一面峭壁,一座光荣的 坟墓.啊,是拿破仑熄灭在那里”,这里,穆旦没有像有的译者那样直译为“逝世”,而 是用了“熄灭”这个词,这隐喻着拿破仑是一道照亮世界、照亮诗人生命的精神之火,如今 在那个荒岛上悲剧性地熄灭。“紧随着他,另一个天才/像风暴之声驰过我们面前”,那就是 天才诗人拜伦。他的离去,“使自由在悲泣中”!读到这里,我们也仿佛听到了诗人的哽咽 声。穆旦在五十年代后期被迫放下了诗的创作,他把他的个人身世之感,个人对自由的渴望, 都寄托和转移在这样的翻译上了。 但是,大海的永恒存在就是一种不屈的象征。在诗的最后,诗人再一次向大海道别,他 不仅在岸上久久地徘徊,还要把大海带在心中,“把你的山岩,你的海湾,/你的光与影,你 的浪花的喋喋,/带到遥远的森林,带到寂静的荒原”。这些金属般的富有质感的诗句,不仅 真切传达了海在“黄昏时分的轰响”,也有力地传达出诗人与大海道别时的内心震颤。大海, 将永远与诗人为伴。 在那些荒凉的青春岁月里,这样的诗,我每次读,都引起肉体的一阵阵颤栗,虽然我说 不清这是为什么,直到多年后,我读到茨维塔耶娃在《我的普希金》中的一段话“三十余年 过后,我清楚了:我的去海边,就是去普希金的怀抱,就是投向普希金的怀抱”;“‘自由 的元素’原来就是诗,而不是大海,原来就是诗,也就是那我永远也不会与之道别的惟一的 元素.”我这才更多地明白了普希金对我们的意义。 至于戈宝权译的《给凯恩》,我认识的许多人都会背诵它那著名的开头:“我记得那美妙 的一瞬:/在我的眼前出现了你,/有如昙花一现的幻影,/有如纯洁之美的精灵.”但该诗 之所以如此深刻感人,更在于忧郁、苦闷的流放生活与爱情的奇迹般的重现这两种因素或者 说两个“声部”的融合与交织。的确,读了这样的诗,正如诗中最后所写的那样,“我的心 狂喜地跳跃,/有了它,一切又重新苏醒,/???有了神性,有了灵感,/有了生命,有了眼泪, 也有了爱情”——这就是普希金的诗歌对我们的意义。 《致恰达耶夫》更是一首不可轻易谈论的诗!我记得第一次从一个外地来的知青的小本 子上读到它时,我真不敢往下看!我像偷吃禁果似的慌乱地吞咽下了它的每一个字。虽然因 为当时还太年轻,没想到去学写这样的诗,但总有更勇敢、也更早觉醒的人发出了他们的声 音——在早期朦胧诗和今天派的诗中,我们就明显看到这首诗的某种回响。毫不夸张地说, 没有普希金的影响,黑暗王国就不可能出现一线光明。我们完全可以用《致恰达耶夫》的那 个著名的结尾,来概括早期朦胧诗和今天派在那个时代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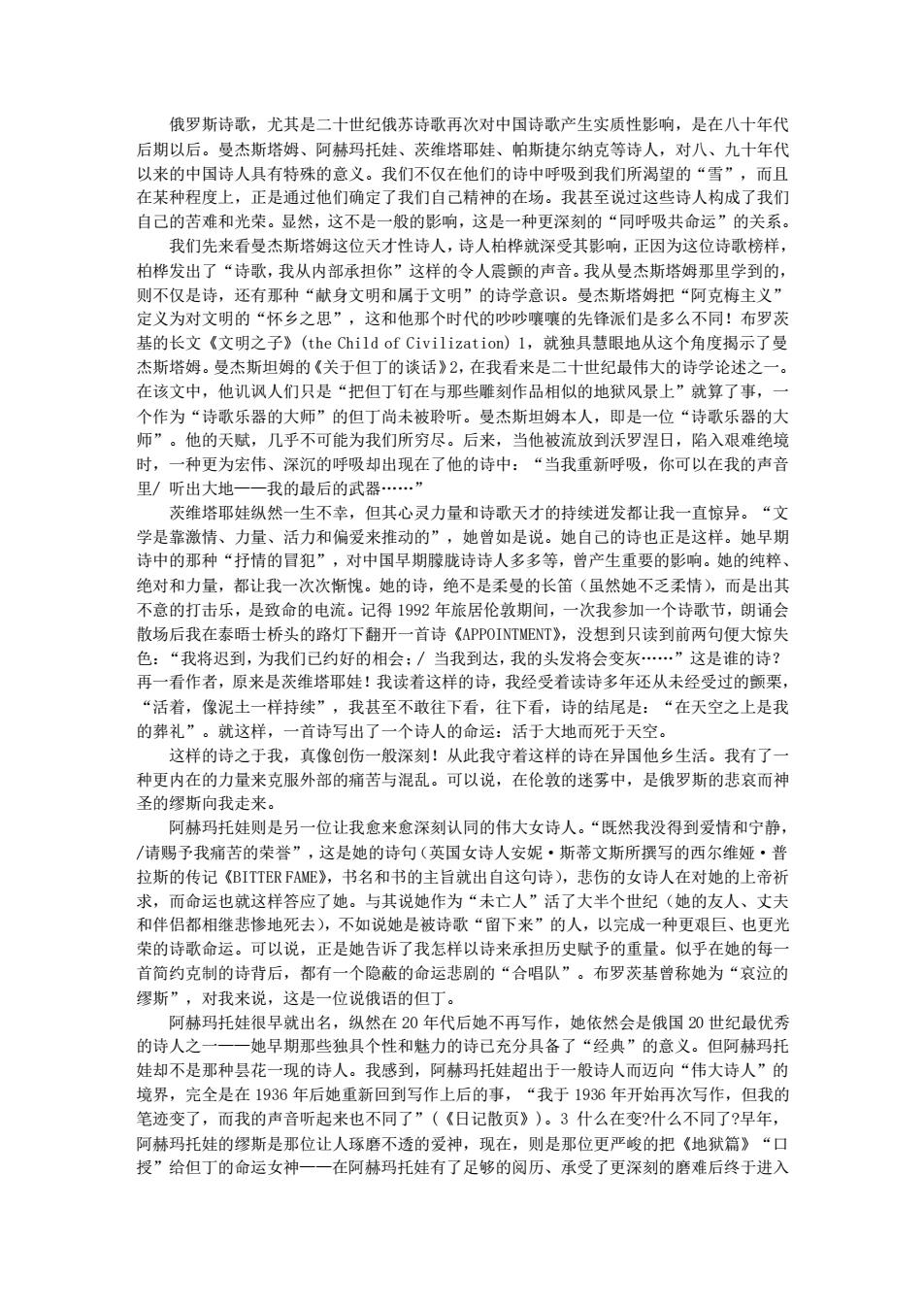
俄罗斯诗歌,尤其是二十世纪俄苏诗歌再次对中国诗歌产生实质性影响,是在八十年代 后期以后。曼杰斯塔姆、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等诗人,对八、九十年代 以来的中国诗人具有特殊的意义 ,我们不仅在他们的诗中呼吸到我们所渴望的 在某种程度上,正是通过他们确定了我们自己精神的在场。我甚至说过这些诗人构成了我们 自己的苦难和光荣。显然,这不是一般的影响,这是一种更深刻的“同呼吸共命运”的关系。 我们先来看曼杰斯塔姆这位天才性诗人,诗人柏桦就深受其影响,正因为这位诗歌榜样, 柏桦发出了“诗歌,我从内部承担你”这样的令人震颜的声音。我从曼杰斯塔姆那里学到的 则不仅是诗 还有那 状身文明 和属于文明”的诗学意识。 杰斯塔姆扑 “阿克梅主 定义为对文明的“怀乡之思”,这和他那个时代的吵吵嚷嚷的先锋派们是多么不同!布罗 基的长文《文明之子》(the Child of Civilization)l,就独具慧眼地从这个角度揭示了曼 杰斯塔姆。曼杰斯坦姆的《关于但丁的谈话》2,在我看来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学论述之一。 在该文中,他机讽人们只是“把但丁钉在与那些雕刻作品相似的地狱风量上”就算了事, 个作为“诗歌乐器的大师”的但丁尚未被聆听。曼杰斯坦姆本人, 即是 一位“诗歌乐器的大 他的天赋,几乎不可能为我们所穷尽 。后来 当他被流放到沃罗涅日,陷入艰难绝域 时, 一种更为宏伟、深沉的呼吸却出现在了他的诗中: “当我重新呼吸,你可以在我的声音 里/听出大地 我的最后的武器, 茨维塔耶硅织然一生不幸,但其心,灵力量和诗歌天木的持续讲发都让我一直惊异。“文 活力和信爱来推动的” ,她曾如是说。她自己的诗也正是这样。她早期 诗中的那 的犯 对中国早期朦胧诗 人多多等,曾产生重要的影 。她的纯料 绝对和力量,都让我一次次惭愧。她的诗,绝不是柔曼的长笛(虽然她不乏柔情,而是出其 不意的打击乐,是致命的电流。记得1992年旅居伦敦期间, 一次我参加一个诗歌节,朗通会 散场后我在泰晤士桥头的路灯下翻开一首诗《APPOINTMENT》,没想到只读到前两句便大惊失 色:“我将迟到,为我们已约好的相会:/当我到达,我的头发将会变灰.”这是谁的诗? 一看作者,原来是茨维塔耶娃:我读这样的诗,我经受者读诗多年还从未经受过的颜栗 活着,像泥士 一样持续”,我甚至不敢往下看,往下看,诗的结尾是 “在天空之上是我 的攀礼” 。就这样,一首诗写出了一个诗人的命运:活于大地而死于天空 这样的诗之于我,真像创伤一般深刻!从此我守者这样的诗在异国他乡生活。我有了一 种更内在的力量来克服外部的痛苦与混乱。可以说,在伦的迷雾中,是饿罗斯的悲哀而树 圣的斯向我走来 玛托娃则是另一位让我愈来愈深刻认同的伟大女诗人。“既然我没得到爱情和宁前 请赐予我痛苦的荣誉”,这是她的诗句(英国女诗人安妮·斯蒂文斯所撰写的西尔维娅·智 拉斯的传记《BITTER FAME》,书名和书的主旨就出自这句诗),悲伤的女诗人在对她的上帝祈 求,而命运也就这样答应了她。与其说她作为“未亡人”活了大半个世纪(她的友人、丈夫 和伴侣都相继悲惨地死去),不如说她是被诗歌“留下来”的人,以完成一种更艰巨、也更光 荣的诗歌命运。 可以说 正是她告诉了我怎样以诗来承担历史赋予的重量 似乎在她的 首简约克制的诗背后,都有一个隐蔽的命运悲刷的“合唱队”。布罗茨基曾称她为“哀泣的 缪斯”,对我来说,这是一位说俄语的但丁。 阿赫玛托娃很早就出名,纵然在20年代后她不再写作,她依然会是俄国0世纪最优秀 的诗人之 一她早期那些独具个性和魅力的诗已充分具备了“经典”的意义。但阿赫玛杆 娃却不是那种昙花一现的诗人。 我威阿抹现娃超出 一般诗人而迈向“伟大诗人”的 境界,完全是在1936年后她重新回到写作上后的事 “我于1936年开始再次写作,但我的 笔迹变了,而我的声音听起来也不同了”((日记散页》)。3什么在变什么不同了?早年, 阿赫玛托娃的缪斯是那位让人琢磨不透的爱神,现在,则是那位更严峻的把《地狱篇》“口 授”给但丁的命运女神一一在阿赫玛托娃有了足够的阅历、承受了更深刻的磨难后终于进入
俄罗斯诗歌,尤其是二十世纪俄苏诗歌再次对中国诗歌产生实质性影响,是在八十年代 后期以后。曼杰斯塔姆、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等诗人,对八、九十年代 以来的中国诗人具有特殊的意义。我们不仅在他们的诗中呼吸到我们所渴望的“雪”,而且 在某种程度上,正是通过他们确定了我们自己精神的在场。我甚至说过这些诗人构成了我们 自己的苦难和光荣。显然,这不是一般的影响,这是一种更深刻的“同呼吸共命运”的关系。 我们先来看曼杰斯塔姆这位天才性诗人,诗人柏桦就深受其影响,正因为这位诗歌榜样, 柏桦发出了“诗歌,我从内部承担你”这样的令人震颤的声音。我从曼杰斯塔姆那里学到的, 则不仅是诗,还有那种“献身文明和属于文明”的诗学意识。曼杰斯塔姆把“阿克梅主义” 定义为对文明的“怀乡之思”,这和他那个时代的吵吵嚷嚷的先锋派们是多么不同!布罗茨 基的长文《文明之子》(the Child of Civilization) 1,就独具慧眼地从这个角度揭示了曼 杰斯塔姆。曼杰斯坦姆的《关于但丁的谈话》2,在我看来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学论述之一。 在该文中,他讥讽人们只是“把但丁钉在与那些雕刻作品相似的地狱风景上”就算了事,一 个作为“诗歌乐器的大师”的但丁尚未被聆听。曼杰斯坦姆本人,即是一位“诗歌乐器的大 师”。他的天赋,几乎不可能为我们所穷尽。后来,当他被流放到沃罗涅日,陷入艰难绝境 时,一种更为宏伟、深沉的呼吸却出现在了他的诗中:“当我重新呼吸,你可以在我的声音 里/ 听出大地——我的最后的武器.” 茨维塔耶娃纵然一生不幸,但其心灵力量和诗歌天才的持续迸发都让我一直惊异。“文 学是靠激情、力量、活力和偏爱来推动的”,她曾如是说。她自己的诗也正是这样。她早期 诗中的那种“抒情的冒犯”,对中国早期朦胧诗诗人多多等,曾产生重要的影响。她的纯粹、 绝对和力量,都让我一次次惭愧。她的诗,绝不是柔曼的长笛(虽然她不乏柔情),而是出其 不意的打击乐,是致命的电流。记得 1992 年旅居伦敦期间,一次我参加一个诗歌节,朗诵会 散场后我在泰晤士桥头的路灯下翻开一首诗《APPOINTMENT》,没想到只读到前两句便大惊失 色:“我将迟到,为我们已约好的相会;/ 当我到达,我的头发将会变灰.”这是谁的诗? 再一看作者,原来是茨维塔耶娃!我读着这样的诗,我经受着读诗多年还从未经受过的颤栗, “活着,像泥土一样持续”,我甚至不敢往下看,往下看,诗的结尾是:“在天空之上是我 的葬礼”。就这样,一首诗写出了一个诗人的命运:活于大地而死于天空。 这样的诗之于我,真像创伤一般深刻!从此我守着这样的诗在异国他乡生活。我有了一 种更内在的力量来克服外部的痛苦与混乱。可以说,在伦敦的迷雾中,是俄罗斯的悲哀而神 圣的缪斯向我走来。 阿赫玛托娃则是另一位让我愈来愈深刻认同的伟大女诗人。“既然我没得到爱情和宁静, /请赐予我痛苦的荣誉”,这是她的诗句(英国女诗人安妮·斯蒂文斯所撰写的西尔维娅·普 拉斯的传记《BITTER FAME》,书名和书的主旨就出自这句诗),悲伤的女诗人在对她的上帝祈 求,而命运也就这样答应了她。与其说她作为“未亡人”活了大半个世纪(她的友人、丈夫 和伴侣都相继悲惨地死去),不如说她是被诗歌“留下来”的人,以完成一种更艰巨、也更光 荣的诗歌命运。可以说,正是她告诉了我怎样以诗来承担历史赋予的重量。似乎在她的每一 首简约克制的诗背后,都有一个隐蔽的命运悲剧的“合唱队”。布罗茨基曾称她为“哀泣的 缪斯”,对我来说,这是一位说俄语的但丁。 阿赫玛托娃很早就出名,纵然在 20 年代后她不再写作,她依然会是俄国 20 世纪最优秀 的诗人之一——她早期那些独具个性和魅力的诗已充分具备了“经典”的意义。但阿赫玛托 娃却不是那种昙花一现的诗人。我感到,阿赫玛托娃超出于一般诗人而迈向“伟大诗人”的 境界,完全是在 1936 年后她重新回到写作上后的事,“我于 1936 年开始再次写作,但我的 笔迹变了,而我的声音听起来也不同了”(《日记散页》)。3 什么在变?什么不同了?早年, 阿赫玛托娃的缪斯是那位让人琢磨不透的爱神,现在,则是那位更严峻的把《地狱篇》“口 授”给但丁的命运女神——在阿赫玛托娃有了足够的阅历、承受了更深刻的磨难后终于进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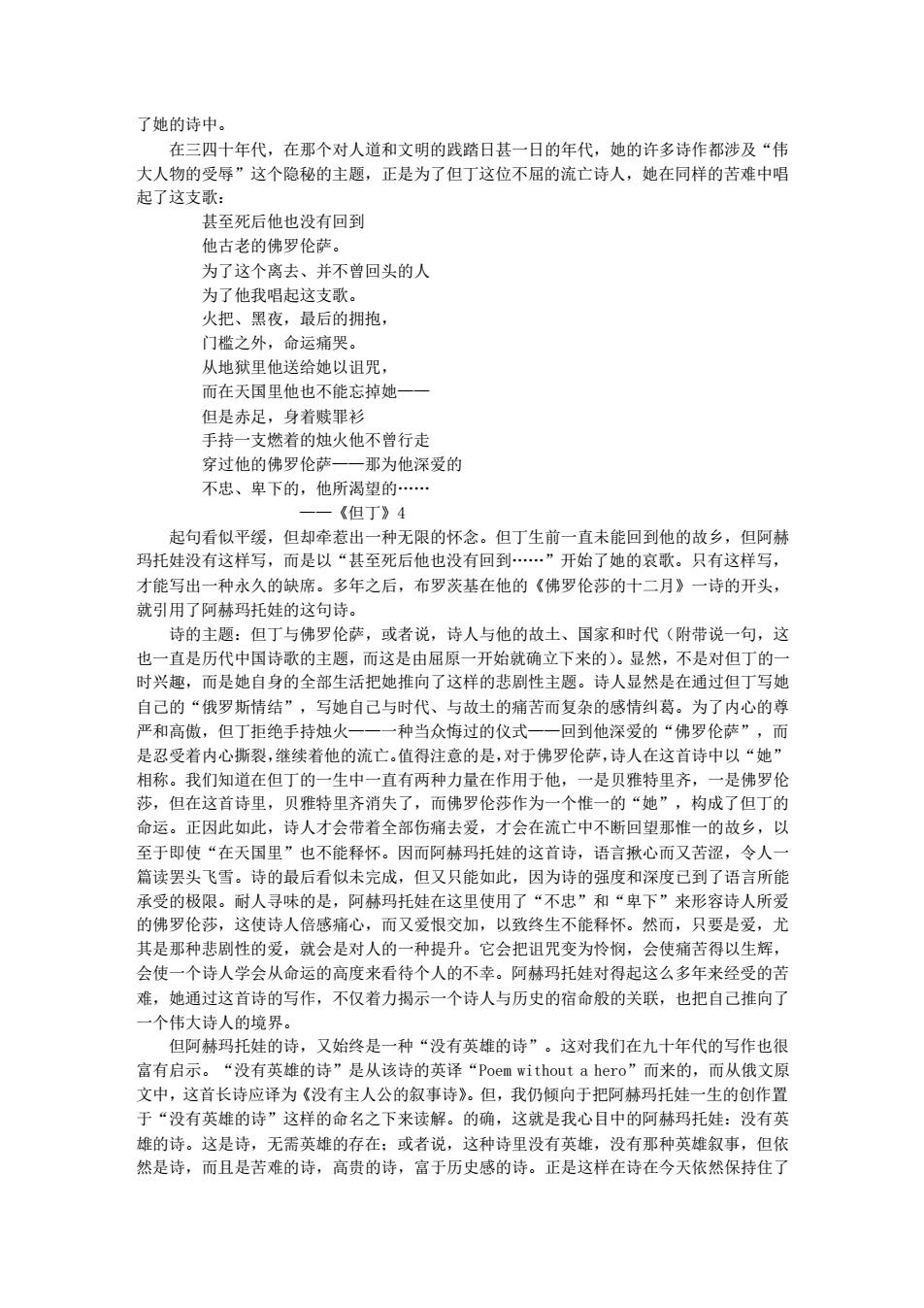
了她的诗中。 在二四十年代,在那个对人道和文明的践燃日其一日的年代,她的许多诗作都洗及“佳 大人物的受辱”这个隐秘的主题,正是为了但丁这位不屈的流亡诗人,她在同样的苦难中 起了这支歌 甚至死后他也没有回到 他古老的佛罗伦萨。 为了这个离去、并不曾回头的人 为了他我唱起这支彩 黑夜,最后的拥抱 门槛之外,命运痛哭。 从地狱里他送给她以诅咒 而在天国里他也不能忘掉她 但是赤足,身若赎罪衫 手持 支燃若的烛火他不曾行走 穿过他的佛罗伦萌 一那为他深爱的 不忠、卑下的,他所渴望的 《但丁》4 起句君似平缓,但却牵营出一种无限的怀今。但丁生前一直未能回到他的故乡,但阿林 玛托娃没有这样写,而是以“甚至死后他也没有回到.”开始了她的哀歌。只有这样写, 才能写出一种永久的缺席。 多年之后,布罗茨基在他的《佛罗伦莎的十二月》 一诗的开头 就引用了阿赫玛托娃的这句诗】 诗的主题:但丁与佛罗伦萨,或者说,诗人与他的故土、国家和时代(附带说一句,这 也一直是历代中国诗歌的主颗,而这是由届原一开始就确立下来的)。显然。不是对但丁的 时兴趣,而是她自身的全部生活把她推向了这样的悲刷性主题。诗人显然是在通过但丁写她 自己的“俄罗斯情 写她自己与时代、与故士的痛苦而复杂的感情纠葛 为了内心的膏 严和高做,但丁拒绝手持烛火 ·种当众悔过的仪式 回到他深爱的“佛罗伦萨” 而 是忍受着内心撕裂,继续若他的流亡。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佛罗伦蒸,诗人在这首诗中以“她 相称。我们知道在但工的一牛中一直有两种力量在作用于他,一是贝雅特里齐,一是佛罗伦 莎。但在这首诗里,贝雅特里齐消失了,而佛罗伦莎作为 个惟一的“她”。构成了但丁的 命运。 正因此如此,诗人才会带着全部伤痛 爱 ,才会在 亡中不断回望那惟 的故乡, 至于即使“在天国里”也不能释怀。因而阿赫玛托娃的这首诗,语言揪心而又苦涩,令人 篇读罢头飞雪。诗的最后看似未完成,但又只能如此,因为诗的强度和深度已到了语言所能 承受的极限。耐人寻味的是,阿赫玛托娃在这里使用了“不忠”和“卑下”来形容诗人所爱 的佛罗伦莎,这使诗人倍感痛心,而又爱恨交加,以致终生不能释怀。然而,只要是爱,尤 其是那种悲剧性的爱,就会是对人的一种提升。它会把诅咒变为怜悯,会使痛苦得以生辉 会使 个诗人学会从命运的高度来看待个人的不幸。阿赫玛托娃对得起这么多年来经受的 难,她通过这首诗的写作,不仅着力揭示一个诗人与历史的宿命般的关联,也把自己推向了 一个伟大诗人的境界。 但阿赫玛托娃的诗,又始终是一种“没有英雄的诗”。这对我们在九十年代的写作也很 宫有启示。“沿右英雄的诗”是从该诗的英译“P0 em with a hero”而来的,而从俄文原 文中,这首长诗应译为《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但,我仍向于 把阿赫玛托 生的创作置 于“没有英雄的诗”这样的命名之下米读解。的确,这就是我心目中的阿赫玛托娃:没有英 雄的诗。这是诗,无需英雄的存在:或者说,这种诗里没有英雄,没有那种英雄叙事,但依 然是诗,而且是苦难的诗,高贵的诗,富于历史感的诗。正是这样在诗在今天依然保持住了
了她的诗中。 在三四十年代,在那个对人道和文明的践踏日甚一日的年代,她的许多诗作都涉及“伟 大人物的受辱”这个隐秘的主题,正是为了但丁这位不屈的流亡诗人,她在同样的苦难中唱 起了这支歌: 甚至死后他也没有回到 他古老的佛罗伦萨。 为了这个离去、并不曾回头的人 为了他我唱起这支歌。 火把、黑夜,最后的拥抱, 门槛之外,命运痛哭。 从地狱里他送给她以诅咒, 而在天国里他也不能忘掉她—— 但是赤足,身着赎罪衫 手持一支燃着的烛火他不曾行走 穿过他的佛罗伦萨——那为他深爱的 不忠、卑下的,他所渴望的. ——《但丁》4 起句看似平缓,但却牵惹出一种无限的怀念。但丁生前一直未能回到他的故乡,但阿赫 玛托娃没有这样写,而是以“甚至死后他也没有回到.”开始了她的哀歌。只有这样写, 才能写出一种永久的缺席。多年之后,布罗茨基在他的《佛罗伦莎的十二月》一诗的开头, 就引用了阿赫玛托娃的这句诗。 诗的主题:但丁与佛罗伦萨,或者说,诗人与他的故土、国家和时代(附带说一句,这 也一直是历代中国诗歌的主题,而这是由屈原一开始就确立下来的)。显然,不是对但丁的一 时兴趣,而是她自身的全部生活把她推向了这样的悲剧性主题。诗人显然是在通过但丁写她 自己的“俄罗斯情结”,写她自己与时代、与故土的痛苦而复杂的感情纠葛。为了内心的尊 严和高傲,但丁拒绝手持烛火——一种当众悔过的仪式——回到他深爱的“佛罗伦萨”,而 是忍受着内心撕裂,继续着他的流亡。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佛罗伦萨,诗人在这首诗中以“她” 相称。我们知道在但丁的一生中一直有两种力量在作用于他,一是贝雅特里齐,一是佛罗伦 莎,但在这首诗里,贝雅特里齐消失了,而佛罗伦莎作为一个惟一的“她”,构成了但丁的 命运。正因此如此,诗人才会带着全部伤痛去爱,才会在流亡中不断回望那惟一的故乡,以 至于即使“在天国里”也不能释怀。因而阿赫玛托娃的这首诗,语言揪心而又苦涩,令人一 篇读罢头飞雪。诗的最后看似未完成,但又只能如此,因为诗的强度和深度已到了语言所能 承受的极限。耐人寻味的是,阿赫玛托娃在这里使用了“不忠”和“卑下”来形容诗人所爱 的佛罗伦莎,这使诗人倍感痛心,而又爱恨交加,以致终生不能释怀。然而,只要是爱,尤 其是那种悲剧性的爱,就会是对人的一种提升。它会把诅咒变为怜悯,会使痛苦得以生辉, 会使一个诗人学会从命运的高度来看待个人的不幸。阿赫玛托娃对得起这么多年来经受的苦 难,她通过这首诗的写作,不仅着力揭示一个诗人与历史的宿命般的关联,也把自己推向了 一个伟大诗人的境界。 但阿赫玛托娃的诗,又始终是一种“没有英雄的诗”。这对我们在九十年代的写作也很 富有启示。“没有英雄的诗”是从该诗的英译“Poem without a hero”而来的,而从俄文原 文中,这首长诗应译为《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但,我仍倾向于把阿赫玛托娃一生的创作置 于“没有英雄的诗”这样的命名之下来读解。的确,这就是我心目中的阿赫玛托娃:没有英 雄的诗。这是诗,无需英雄的存在;或者说,这种诗里没有英雄,没有那种英雄叙事,但依 然是诗,而且是苦难的诗,高贵的诗,富于历史感的诗。正是这样在诗在今天依然保持住了

它的尊亚和魅力。 在0世纪俄国诗人中,大概阿赫玛托娃是被辱骂最多的一位。最著名的自然是日丹诺夫 那粗暴的批判兼咒 同样让人惊异的是,阿赫玛托娃看上去几乎是在平静地承受 ,切, 据传记材料,1946年4月,就在苏共中央关于批判阿林玛托娃和左琴科的决议见报后的第 天,她仍不了解发生了什么事,到作协办事时,她不解地看着人们急忙躲着自己,而一位妇 女见到她后居然在楼道里哭了起来,直到她回家后打开用来包裹鲜鱼的报纸,这才发现上面 刊登的一切: 但是, 这又有什么呢?用一个国家机器来对付一个弱女子和几首诗,这不是太可笑、也太 虚弱了吗?作家协会要开除,那就让他们开除:人们要表态,那就让他们表态个够,她不是号 已被这样的文人们不止一次地“活埋”过吗?她照样活着。她照样听她的巴赫。她甚至从不期 待“历史的公正”,因为判断她一生的,已是另外一些更神圣、持久的事物。纵然她已成为 悲剧中的“焦点”,但她却无章去做那种过于高大或悲壮的悲剧人物,更不允许自己因与现 实的纠葛而妨碍了对存在的全部领域的散 这就是我所看到的阿赫玛托娃,她不是以自 已的不幸 而是以不断超越的诗篇 对自己的一生做出了更有力的总结! 1958年6月,已逾七十的女诗人写下了这样一首《海滨十四行》: 这里的一切都将活得比我更长久, 一切,其至那荒废的欧掠鸟窝, 和这微风,这完成了越洋飞行的 春季的微风」 个永恒的声音在召唤 带着异地不可抗拒的威力 而在开花的樱桃树上空 轮新月流浩若光辉 我不能不惊是 个承受了一生磨难的诗人在其晚年还能进发出这样的激情在这里 漫长的苦难不见了,甚至生与死的链条也断裂了,而存在的诗意、永恒的价值尺度在伸展它 自身。仿佛是穿过了“上帝的黑暗” ,她一下子置身于字宙的无穷性中发出了如此明亮的声 音!是的,这是不朽的一瞬,是对一个永恒王国的敞开。一个写出了或能写出这样的诗的人, 还在乎什么历史的公正或不公正呢? 现在该谈到帕斯捷尔纳克了!我心目中的“诗人”和“诗歌精神”正是和这个名字联系 在一起的。这个名字所代表的诗歌品质及其命运 对我几乎具有某种神话般的力 。他的完 美令人绝望。我在90年代初的两首诗《帕斯捷尔钠克》和《瓦雷金诺叙事曲》就是献给他的, 据我所知,还有其他中国诗人写过类似的诗篇。 帕斯捷尔纳克的早期诗具有一种惊人的比喻才能,如“高加索山脉就像一床堆得乱糟德 的被据那样铺展着”,“冰川震出了脸庞,就像死者灵建的复活”。在 首《出于迷信》的 爱情诗中,诗一开始就是一个隐喻 :“这藏着一只桔子的火柴盒/就是我的斗室” 。这是多 独特,又多么亲切!它像定音鼓一样为全诗确定了一种音色。至于诗中写到的爱人的衣裙“像 是一朵雪莲,在向四月请安/像是在轻声曼语”,一种无比清新、奇异的美感就像雪莲一样呈 现出来了: 怎能说你不是贞洁的圣女 你来时带来一把小椅子 你取下我的生命如同取自书架 并吹去名字上的蒙尘。 结尾一节的“小椅子”和开头的“小盒子”正好相对称。我曾写过一文“坐矮板凳的天 使”,来形容我喜欢的一位天才钢琴家格伦·古尔德。天使从来就是坐小板凳的,难道我们
它的尊严和魅力。 在 20 世纪俄国诗人中,大概阿赫玛托娃是被辱骂最多的一位。最著名的自然是日丹诺夫 那粗暴的批判兼咒骂。同样让人惊异的是,阿赫玛托娃看上去几乎是在平静地承受了一切, 据传记材料,1946 年 4 月,就在苏共中央关于批判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的决议见报后的第二 天,她仍不了解发生了什么事,到作协办事时,她不解地看着人们急忙躲着自己,而一位妇 女见到她后居然在楼道里哭了起来,直到她回家后打开用来包裹鲱鱼的报纸,这才发现上面 刊登的一切! 但是,这又有什么呢?用一个国家机器来对付一个弱女子和几首诗,这不是太可笑、也太 虚弱了吗?作家协会要开除,那就让他们开除;人们要表态,那就让他们表态个够,她不是早 已被这样的文人们不止一次地“活埋”过吗?她照样活着。她照样听她的巴赫。她甚至从不期 待“历史的公正”,因为判断她一生的,已是另外一些更神圣、持久的事物。纵然她已成为 悲剧中的“焦点”,但她却无意去做那种过于高大或悲壮的悲剧人物,更不允许自己因与现 实的纠葛而妨碍了对存在的全部领域的敞开——这就是我所看到的阿赫玛托娃,她不是以自 己的不幸,而是以不断超越的诗篇,对自己的一生做出了更有力的总结! 1958 年 6 月,已逾七十的女诗人写下了这样一首《海滨十四行》: 这里的一切都将活得比我更长久, 一切,甚至那荒废的欧椋鸟窝, 和这微风,这完成了越洋飞行的 春季的微风。 一个永恒的声音在召唤, 带着异地不可抗拒的威力; 而在开花的樱桃树上空 一轮新月流溢着光辉. 我不能不惊异,一个承受了一生磨难的诗人在其晚年还能迸发出这样的激情!在这里, 漫长的苦难不见了,甚至生与死的链条也断裂了,而存在的诗意、永恒的价值尺度在伸展它 自身。仿佛是穿过了“上帝的黑暗”,她一下子置身于宇宙的无穷性中发出了如此明亮的声 音!是的,这是不朽的一瞬,是对一个永恒王国的敞开。一个写出了或能写出这样的诗的人, 还在乎什么历史的公正或不公正呢? 现在该谈到帕斯捷尔纳克了!我心目中的“诗人”和“诗歌精神”正是和这个名字联系 在一起的。这个名字所代表的诗歌品质及其命运,对我几乎具有某种神话般的力量。他的完 美令人绝望。我在 90 年代初的两首诗《帕斯捷尔纳克》和《瓦雷金诺叙事曲》就是献给他的, 据我所知,还有其他中国诗人写过类似的诗篇。 帕斯捷尔纳克的早期诗具有一种惊人的比喻才能,如“高加索山脉就像一床堆得乱糟糟 的被褥那样铺展着”,“冰川露出了脸庞,就像死者灵魂的复活”。在一首《出于迷信》的 爱情诗中,诗一开始就是一个隐喻:“这藏着一只桔子的火柴盒/就是我的斗室”。这是多么 独特,又多么亲切!它像定音鼓一样为全诗确定了一种音色。至于诗中写到的爱人的衣裙“像 是一朵雪莲,在向四月请安/像是在轻声曼语”,一种无比清新、奇异的美感就像雪莲一样呈 现出来了! 怎能说你不是贞洁的圣女: 你来时带来一把小椅子, 你取下我的生命如同取自书架 并吹去名字上的蒙尘。 结尾一节的“小椅子”和开头的“小盒子”正好相对称。我曾写过一文“坐矮板凳的天 使”,来形容我喜欢的一位天才钢琴家格伦·古尔德。天使从来就是坐小板凳的,难道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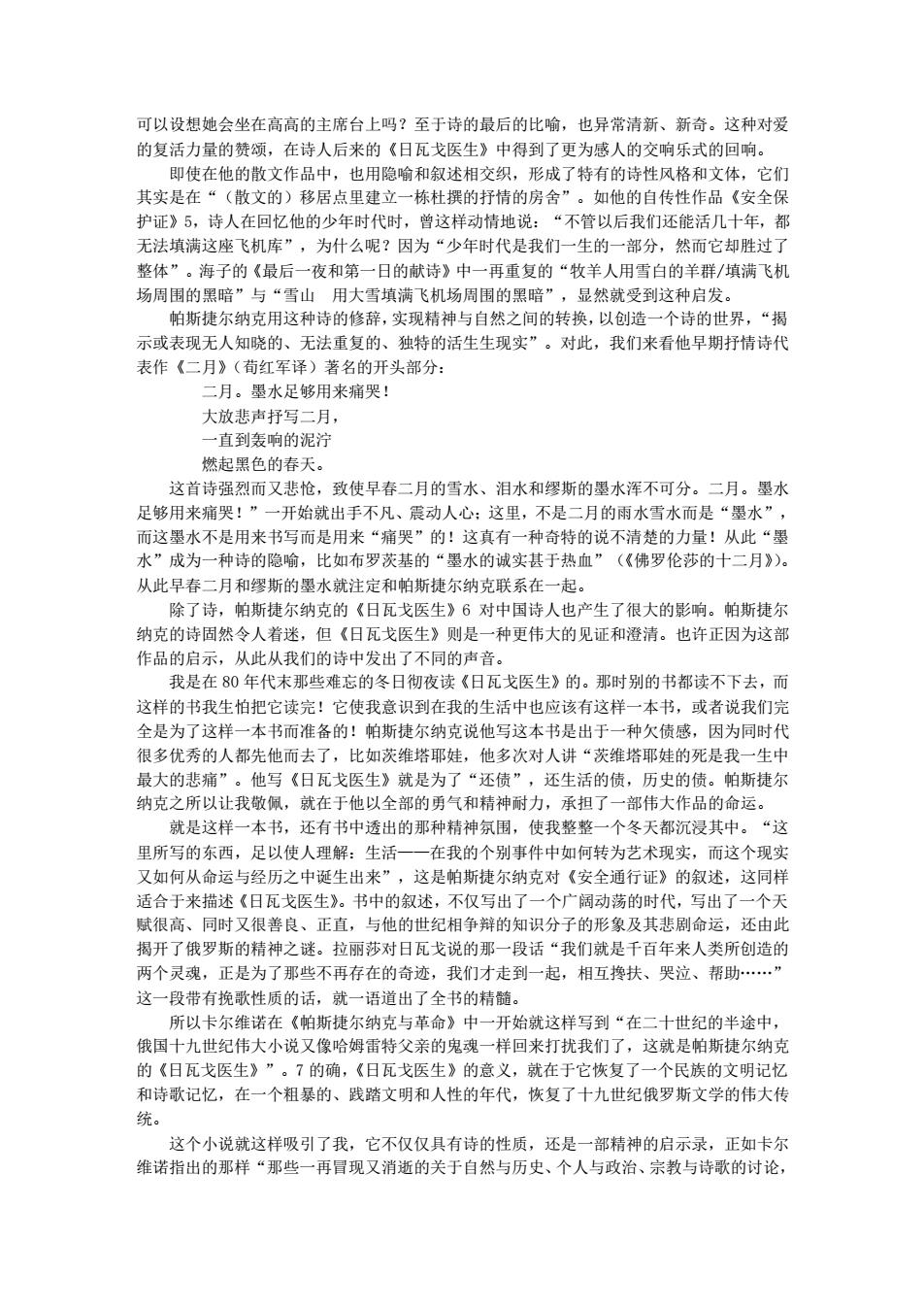
可以设想她会坐在高高的主席台上吗?至于诗的最后的比喻,也异常清新、新奇。这种对爱 的复活力量的赞颂,在诗人后来的《日瓦戈医生》中得到了更为感人的交响乐式的回响。 即使在他的散文作品中, 也用隐喻和叙述相交织 形 了特 的 性风格和文体 它们 其实 (散文的)移居点里建 栋杜撰的抒情的房舍” 如他的自传性作品《安 护证》5,诗人在回忆他的少年时代时,曾这样动情地说:“不管以后我们还能活几十年,都 无法填满这座飞机库”,为什么呢?因为“少年时代是我们一生的一部分,然而它却胜过了 整体”。海子的《最后一夜和第一日的献诗》中一面重复的“效羊人用雪白的羊群/填满飞机 场周围的黑暗”与“雪山 用大雪填满飞机场周围的黑暗 显然就受到这种启发 帕斯捷尔纳克用这种诗的修辞,实现精 然之间的转 ,以创 诗的世界 “揭 示或表现无人知晓的、无法重复的、独特的活生生现实”。对此,我们来看他早期抒情诗代 表作《二月》(苟红军译)著名的开头部分: 二月。墨水足够用来痛哭! 大放非声择写一日 直到轰响的泥 燃起黑色的春天。 这首诗强烈而又悲怆,致使早春二月的雪水、泪水和缪斯的墨水浑不可分。二月。墨水 足够用来痛哭!”一开始就出手不凡、震动人心:这里,不是二月的雨水雪水而是“墨水” 而这题水不是用来书写而是用来“痛哭”的!这直有一种奇特的说不清楚的力量!从此“器 水”成为 一种诗的隐喻,比如布罗茨基的“墨水的诚实甚于热血” (《佛罗伦莎的十二月》) 从此早春 二月和缪斯的墨水就注定和帕斯捷尔纳克联系在 除了诗,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6对中国诗人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帕斯捷尔 纳克的诗周然令人者迷,但《日瓦戈医生》则是一种更伟大的见证和澄清。也许正因为这部 作品的启示,从此从我们的诗中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我是在80年代末那些难忘的冬日彻夜读《日瓦戈医生》的。那时别的书都读不下去,而 这样的书我生怕把它读完 它使我意识到在我的生活中也应该有这样 一本书 或者说我们完 全是为了这样一本书而准备的:帕斯捷尔纳克说他写这本书是出于 一种欠债感,因为同时代 很多优秀的人都先他而去了,比如茨维塔耶娃,他多次对人进“茨维塔耶娃的死是我一生中 最大的悲痛”。他写《日瓦戈医生》就是为了“还债”,还生活的债,历史的债。帕斯捷尔 钠克之所以让我佩,就在于他以全部的勇气和精神耐力,承担了一部伟大作品的命运。 就是这样 有书中透出的那种精神氛目 使我整整 一个冬天都沉浸其中 里所写的东西,足以使人理解:生活一 在我的个别事件中如何转为艺术现实,而这个现实 又如何从命运与经历之中诞生出来”,这是帕斯捷尔纳克对《安全通行证》的叙述,这同样 适合于来描述《日瓦戈医生》。书中的叙述,不仅写出了一个广阔动荡的时代,写出了一个天 赋很高、同时又很善良、正直,与他的世纪相争辩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及其悲剧命运,还由此 揭开了俄罗斯的精神之谜。拉丽莎对日瓦戈说的那一段话“我们就是千百年来人类所创造的 两个灵魂 正是为了那些不再存在的奇迹,我们才走到一起,相互搀扶、 哭泣、帮助 这一段带有挽歌性质的话,就一语道出了全书的精髓。 所以卡尔维诺在《帕斯捷尔纳克与革命》中一开始就这样写到“在二十世纪的半途中, 俄国十九世纪伟大小说又像哈姆雷特父亲的鬼魂一样回来打扰我们了,这就是帕斯捷尔纳克 的《日瓦戈医生”,7的确,《日瓦戈医生》的意义就在于它恢复了个民族的文明记 和诗歌记忆,在一个粗暴的、践踏文明和人性的年代,恢复了十九世 我罗 斯文学的伟大 这个小说就这样吸引了我,它不仅仅具有诗的性质,还是一部精神的启示录,正如卡尔 维诺指出的那样“那些一再目现又消逝的关于自然与历史、个人与政治、宗教与诗歌的讨论
可以设想她会坐在高高的主席台上吗?至于诗的最后的比喻,也异常清新、新奇。这种对爱 的复活力量的赞颂,在诗人后来的《日瓦戈医生》中得到了更为感人的交响乐式的回响。 即使在他的散文作品中,也用隐喻和叙述相交织,形成了特有的诗性风格和文体,它们 其实是在“(散文的)移居点里建立一栋杜撰的抒情的房舍”。如他的自传性作品《安全保 护证》5,诗人在回忆他的少年时代时,曾这样动情地说:“不管以后我们还能活几十年,都 无法填满这座飞机库”,为什么呢?因为“少年时代是我们一生的一部分,然而它却胜过了 整体”。海子的《最后一夜和第一日的献诗》中一再重复的“牧羊人用雪白的羊群/填满飞机 场周围的黑暗”与“雪山 用大雪填满飞机场周围的黑暗”,显然就受到这种启发。 帕斯捷尔纳克用这种诗的修辞,实现精神与自然之间的转换,以创造一个诗的世界,“揭 示或表现无人知晓的、无法重复的、独特的活生生现实”。对此,我们来看他早期抒情诗代 表作《二月》(荀红军译)著名的开头部分: 二月。墨水足够用来痛哭! 大放悲声抒写二月, 一直到轰响的泥泞 燃起黑色的春天。 这首诗强烈而又悲怆,致使早春二月的雪水、泪水和缪斯的墨水浑不可分。二月。墨水 足够用来痛哭!”一开始就出手不凡、震动人心;这里,不是二月的雨水雪水而是“墨水”, 而这墨水不是用来书写而是用来“痛哭”的!这真有一种奇特的说不清楚的力量!从此“墨 水”成为一种诗的隐喻,比如布罗茨基的“墨水的诚实甚于热血”(《佛罗伦莎的十二月》)。 从此早春二月和缪斯的墨水就注定和帕斯捷尔纳克联系在一起。 除了诗,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6 对中国诗人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帕斯捷尔 纳克的诗固然令人着迷,但《日瓦戈医生》则是一种更伟大的见证和澄清。也许正因为这部 作品的启示,从此从我们的诗中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我是在 80 年代末那些难忘的冬日彻夜读《日瓦戈医生》的。那时别的书都读不下去,而 这样的书我生怕把它读完!它使我意识到在我的生活中也应该有这样一本书,或者说我们完 全是为了这样一本书而准备的!帕斯捷尔纳克说他写这本书是出于一种欠债感,因为同时代 很多优秀的人都先他而去了,比如茨维塔耶娃,他多次对人讲“茨维塔耶娃的死是我一生中 最大的悲痛”。他写《日瓦戈医生》就是为了“还债”,还生活的债,历史的债。帕斯捷尔 纳克之所以让我敬佩,就在于他以全部的勇气和精神耐力,承担了一部伟大作品的命运。 就是这样一本书,还有书中透出的那种精神氛围,使我整整一个冬天都沉浸其中。“这 里所写的东西,足以使人理解:生活——在我的个别事件中如何转为艺术现实,而这个现实 又如何从命运与经历之中诞生出来”,这是帕斯捷尔纳克对《安全通行证》的叙述,这同样 适合于来描述《日瓦戈医生》。书中的叙述,不仅写出了一个广阔动荡的时代,写出了一个天 赋很高、同时又很善良、正直,与他的世纪相争辩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及其悲剧命运,还由此 揭开了俄罗斯的精神之谜。拉丽莎对日瓦戈说的那一段话“我们就是千百年来人类所创造的 两个灵魂,正是为了那些不再存在的奇迹,我们才走到一起,相互搀扶、哭泣、帮助.” 这一段带有挽歌性质的话,就一语道出了全书的精髓。 所以卡尔维诺在《帕斯捷尔纳克与革命》中一开始就这样写到“在二十世纪的半途中, 俄国十九世纪伟大小说又像哈姆雷特父亲的鬼魂一样回来打扰我们了,这就是帕斯捷尔纳克 的《日瓦戈医生》”。7 的确,《日瓦戈医生》的意义,就在于它恢复了一个民族的文明记忆 和诗歌记忆,在一个粗暴的、践踏文明和人性的年代,恢复了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伟大传 统。 这个小说就这样吸引了我,它不仅仅具有诗的性质,还是一部精神的启示录,正如卡尔 维诺指出的那样“那些一再冒现又消逝的关于自然与历史、个人与政治、宗教与诗歌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