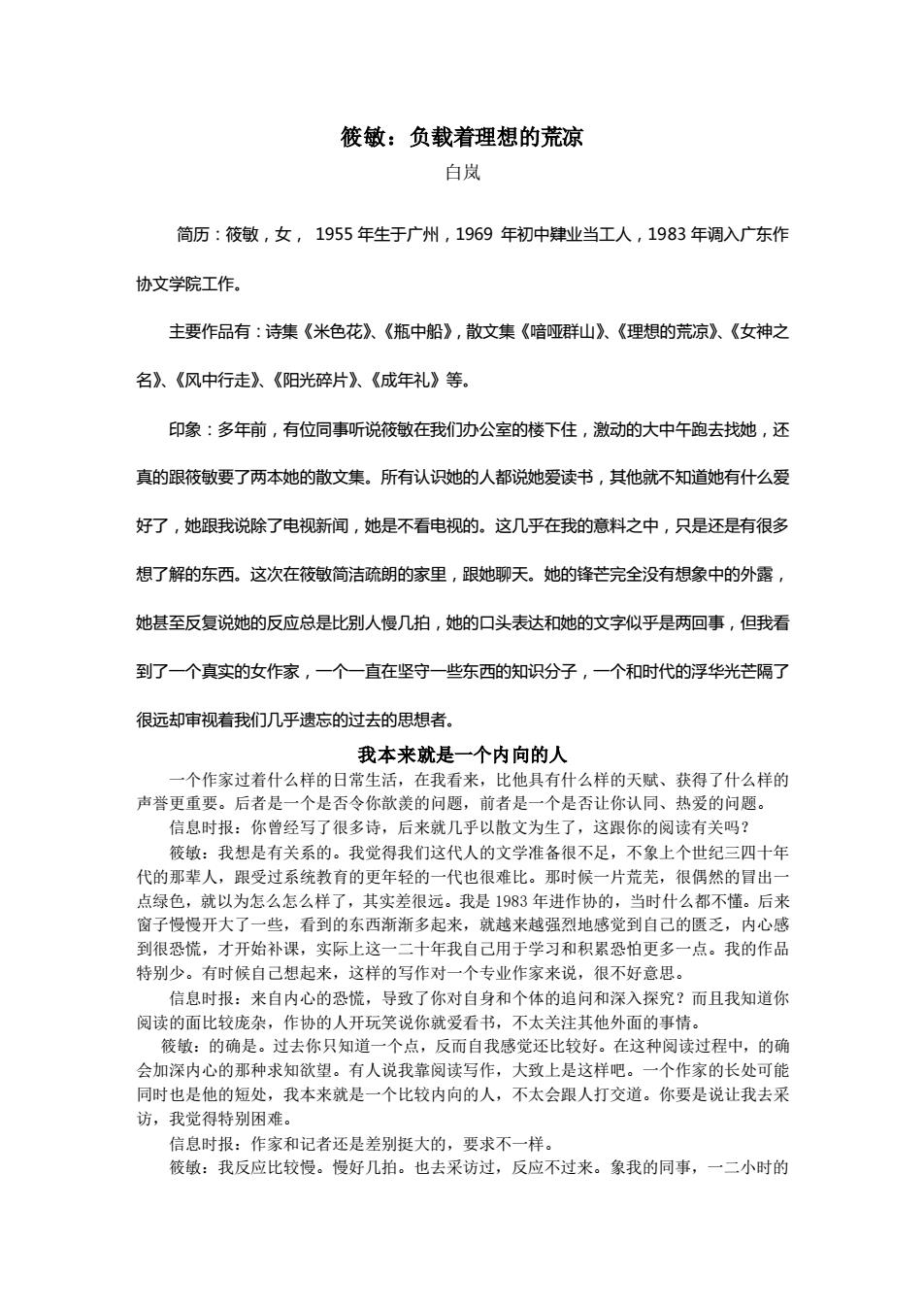
筱敏:负载着理想的荒凉 白岚 简历:筱敏,女,1955年生于广州,1969年初中肆业当工人,1983年调入广东作 协文学院工作 主要作品有:诗集《米色花》、《瓶中船》,散文集《喑哑群山》.、《理想的荒凉》、《女神之 名》、《风中行走》.《阳光碎片》.《成年礼》等。 印象:多年前,有位同事听说筱敏在我们办公室的楼下住,激动的大中午跑去找她,还 真的跟筱敏要了两本她的散文集。所有认识她的人都说她爱读书,其他就不知道她有什么爱 好了,她跟我说除了电视新闻,她是不看电视的。这几乎在我的意料之中,只是还是有很多 想了解的东西。这次在筱敏简洁疏朗的家里,跟她聊天。她的锋芒完全没有想象中的外露, 她甚至反复说她的反应总是比别人慢几拍,她的口头表达和她的文字似乎是两回事,但我看 到了一个真实的女作家,一个一直在坚守一些东西的知识分子,一个和时代的浮华光芒隔了 很远却审视着我们几乎遗忘的过去的思想者。 我本来就是一个内向的人 一个作家过着什么样的日常生活,在我看来,比他具有什么样的天赋、获得了什么样的 声誉更重要。后者是一个是否令你散羡的问题,前者是一个是否让你认同、热爱的问题。 信息时报:你曾经写了很多诗,后来就几乎以散文为生了,这跟你的阅读有关吗? 筱敏:我想是有关系的。我觉得我们这代人的文学准备很不足,不象上个世纪三四十年 代的那辈人,跟受过系统教育的更年轻的一代也很难比。那时候一片荒芜,很偶然的冒出 点绿色,就以为怎么怎么样了,其实差很远。我是1983年进作协的,当时什么都不懂。后来 窗子慢慢开大了一些,看到的东西渐渐多起来,就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自己的匮乏,内心感 到很恐慌,才开始补课,实际上这一二十年我自己用于学习和积累恐怕更多一点。我的作品 特别少。有时候自己想起来,这样的写作对一个专业作家米说,很不好意思 信息时报:来自内心的恐慌,导致了你对自身和个体的追问和深入探究?而且我知道你 阅读的面比较庞杂,作协的人开玩笑说你就爱看书,不太关注其他外面的事情。 筱敏:的确是。过去你只知道一个点,反而自我感觉还比较好。在这种阅读过程中,的确 会加深内心的那种求知欲望。有人说我靠阅读写作,大致上是这样吧。一个作家的长处可能 同时也是他的短处,我本来就是一 比较内向的人,不太会跟人打交道。你要是说让我去习 访,我觉得特别因难。 信息时报:作家和记者还是差别挺大的,要求不一样。 筱敏:我反应比较慢。慢好几拍。也去采访过,反应不过来。象我的同事,一二小时的
筱敏:负载着理想的荒凉 白岚 简历:筱敏,女, 1955 年生于广州,1969 年初中肄业当工人,1983 年调入广东作 协文学院工作。 主要作品有:诗集《米色花》、《瓶中船》,散文集《喑哑群山》、《理想的荒凉》、《女神之 名》、《风中行走》、《阳光碎片》、《成年礼》等。 印象:多年前,有位同事听说筱敏在我们办公室的楼下住,激动的大中午跑去找她,还 真的跟筱敏要了两本她的散文集。所有认识她的人都说她爱读书,其他就不知道她有什么爱 好了,她跟我说除了电视新闻,她是不看电视的。这几乎在我的意料之中,只是还是有很多 想了解的东西。这次在筱敏简洁疏朗的家里,跟她聊天。她的锋芒完全没有想象中的外露, 她甚至反复说她的反应总是比别人慢几拍,她的口头表达和她的文字似乎是两回事,但我看 到了一个真实的女作家,一个一直在坚守一些东西的知识分子,一个和时代的浮华光芒隔了 很远却审视着我们几乎遗忘的过去的思想者。 我本来就是一个内向的人 一个作家过着什么样的日常生活,在我看来,比他具有什么样的天赋、获得了什么样的 声誉更重要。后者是一个是否令你歆羡的问题,前者是一个是否让你认同、热爱的问题。 信息时报:你曾经写了很多诗,后来就几乎以散文为生了,这跟你的阅读有关吗? 筱敏:我想是有关系的。我觉得我们这代人的文学准备很不足,不象上个世纪三四十年 代的那辈人,跟受过系统教育的更年轻的一代也很难比。那时候一片荒芜,很偶然的冒出一 点绿色,就以为怎么怎么样了,其实差很远。我是 1983 年进作协的,当时什么都不懂。后来 窗子慢慢开大了一些,看到的东西渐渐多起来,就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自己的匮乏,内心感 到很恐慌,才开始补课,实际上这一二十年我自己用于学习和积累恐怕更多一点。我的作品 特别少。有时候自己想起来,这样的写作对一个专业作家来说,很不好意思。 信息时报:来自内心的恐慌,导致了你对自身和个体的追问和深入探究?而且我知道你 阅读的面比较庞杂,作协的人开玩笑说你就爱看书,不太关注其他外面的事情。 筱敏:的确是。过去你只知道一个点,反而自我感觉还比较好。在这种阅读过程中,的确 会加深内心的那种求知欲望。有人说我靠阅读写作,大致上是这样吧。一个作家的长处可能 同时也是他的短处,我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不太会跟人打交道。你要是说让我去采 访,我觉得特别困难。 信息时报:作家和记者还是差别挺大的,要求不一样。 筱敏:我反应比较慢。慢好几拍。也去采访过,反应不过来。象我的同事,一二小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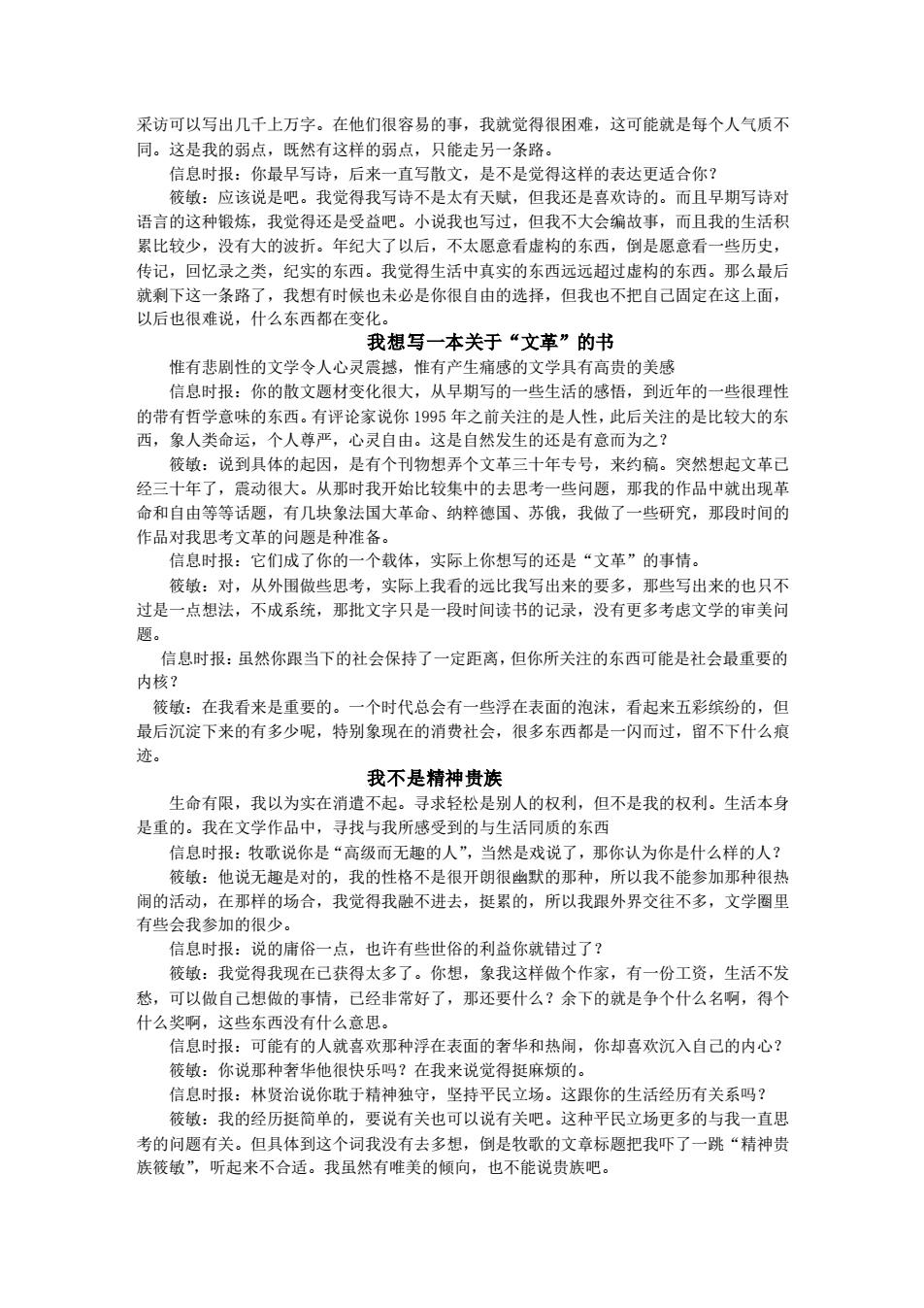
采访可以写出几千上万字。在他们很容易的事,我就觉得很困难,这可能就是每个人气质不 同。这是我的弱点,既然有这样的弱点,只能走另一条路 信息时报:你最早写诗,后来一直写散文,是不是觉得这样的表达更适合你 筱敏:应该说是吧。我觉得我写诗不是太有天赋,但我还是喜欢诗的。而且早期写诗对 语言的这种锻炼,我觉得还是受益吧。小说我也写过,但我不大会编故事,而且我的生活积 累比较少,没有大的波折。年纪大了以后,不太愿意看虚构的东西,倒是愿意看一些历史, 传记,回忆录之类,纪实的东西。我觉得生活中真实的东西远远超过虚构的东西。那么最后 就剩下这 条路 ,我想有时候也未必是你很自由的选择,但我也不把自己固定在这上面 以后也很难说,什么东西都在变化 我想写一本关于“文革”的书 惟有悲副性的文学令人心灵震撼,惟有产生痛感的文学具有高贵的美感 信息时报:你的散文题材变化很大,从早期写的一些生活的感悟,到近年的一些很理性 的带有哲学意味的东西。有评论家说你195年之前关注的是人性,此后关注的是比较大的东 西,象人类命运,个人尊严,心灵自由。这是自然发生的还是有意而为之 筱敏:说到具体的起因,是有个刊物想弄个文革三十年专号,来约稿。突然想起文革己 经三十年了,震动很大。从那时我开始比较集中的去思考一些问题,那我的作品中就出现革 命和自由等等话题,有几块象法国大革命、纳粹德国、苏俄,我做了一些研究,那段时间的 作品对我思考文革的问题是种准备。 信息时报: 它们成了你的 个载体,实际上你想写的还是“文革”的事情 筱敏:对,从外围做些思考,实际上我看的远比我写出来的要多,那些写出来的也只不 过是一点想法,不成系统,那批文字只是一段时间读书的记录,没有更多考虑文学的审美问 信息时报:虽然你跟当下的社会保持了一定距离,但你所关注的东西可能是社会最重要的 内 敏:在我看来是重要的。一个时代总会有一些浮在表面的泡沫,看起来五彩缤纷的,但 最后沉淀下来的有多少呢,特别象现在的消费社会,很多东西都是一闪而过,留不下什么痕 迹。 我不是精神贵族 生命有限我以为实在消遭不起 。寻求轻松是别人的权利,但不是我的权利。生活本身 是重的。我在文学作品中,寻找与我所感受到的与生活同质的东西 信息时报:牧歌说你是“高级而无趣的人”,当然是戏说了,那你认为你是什么样的人? 筱敏:他说无趣是对的,我的性格不是很开朗很幽默的那种,所以我不能参加那种很热 闹的活动,在那样的场合,我觉得我融不进去,挺累的,所以我跟外界交往不多,文学圈里 有些会我参加的很少。 信息时报:说的庸俗一点,也许有些世俗的利益你就错过了? 筱敏:我觉得我现在已获得太多了。你想,象我这样做个作家,有一份工资,生活不发 愁,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己经非常好了,那还要什么?余下的就是争个什么名啊,得个 什么奖啊,这些东西没有什么意思。 信息时报:可能有的人就喜欢那种浮在表面的考华和热闹,你却喜欢沉入自己的内心? 筱敏:你说那种奢华他很快乐吗?在我来说觉得挺麻烦的 信息时报:林贤治说你毗于精神独守,坚持平民立场。这跟你的生活经历有关系吗 筱敏:我的经历挺简单的,要说有关也可以说有关吧。这种平民立场更多的与我一直思 考的问题有关。但具体到这个词我没有去多想,倒是牧歌的文章标题把我吓了一跳“精神贵 族筱敏”,听起来不合适。我虽然有唯美的倾向,也不能说贵族吧
采访可以写出几千上万字。在他们很容易的事,我就觉得很困难,这可能就是每个人气质不 同。这是我的弱点,既然有这样的弱点,只能走另一条路。 信息时报:你最早写诗,后来一直写散文,是不是觉得这样的表达更适合你? 筱敏:应该说是吧。我觉得我写诗不是太有天赋,但我还是喜欢诗的。而且早期写诗对 语言的这种锻炼,我觉得还是受益吧。小说我也写过,但我不大会编故事,而且我的生活积 累比较少,没有大的波折。年纪大了以后,不太愿意看虚构的东西,倒是愿意看一些历史, 传记,回忆录之类,纪实的东西。我觉得生活中真实的东西远远超过虚构的东西。那么最后 就剩下这一条路了,我想有时候也未必是你很自由的选择,但我也不把自己固定在这上面, 以后也很难说,什么东西都在变化。 我想写一本关于“文革”的书 惟有悲剧性的文学令人心灵震撼,惟有产生痛感的文学具有高贵的美感 信息时报:你的散文题材变化很大,从早期写的一些生活的感悟,到近年的一些很理性 的带有哲学意味的东西。有评论家说你 1995 年之前关注的是人性,此后关注的是比较大的东 西,象人类命运,个人尊严,心灵自由。这是自然发生的还是有意而为之? 筱敏:说到具体的起因,是有个刊物想弄个文革三十年专号,来约稿。突然想起文革已 经三十年了,震动很大。从那时我开始比较集中的去思考一些问题,那我的作品中就出现革 命和自由等等话题,有几块象法国大革命、纳粹德国、苏俄,我做了一些研究,那段时间的 作品对我思考文革的问题是种准备。 信息时报:它们成了你的一个载体,实际上你想写的还是“文革”的事情。 筱敏:对,从外围做些思考,实际上我看的远比我写出来的要多,那些写出来的也只不 过是一点想法,不成系统,那批文字只是一段时间读书的记录,没有更多考虑文学的审美问 题。 信息时报:虽然你跟当下的社会保持了一定距离,但你所关注的东西可能是社会最重要的 内核? 筱敏:在我看来是重要的。一个时代总会有一些浮在表面的泡沫,看起来五彩缤纷的,但 最后沉淀下来的有多少呢,特别象现在的消费社会,很多东西都是一闪而过,留不下什么痕 迹。 我不是精神贵族 生命有限,我以为实在消遣不起。寻求轻松是别人的权利,但不是我的权利。生活本身 是重的。我在文学作品中,寻找与我所感受到的与生活同质的东西 信息时报:牧歌说你是“高级而无趣的人”,当然是戏说了,那你认为你是什么样的人? 筱敏:他说无趣是对的,我的性格不是很开朗很幽默的那种,所以我不能参加那种很热 闹的活动,在那样的场合,我觉得我融不进去,挺累的,所以我跟外界交往不多,文学圈里 有些会我参加的很少。 信息时报:说的庸俗一点,也许有些世俗的利益你就错过了? 筱敏:我觉得我现在已获得太多了。你想,象我这样做个作家,有一份工资,生活不发 愁,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已经非常好了,那还要什么?余下的就是争个什么名啊,得个 什么奖啊,这些东西没有什么意思。 信息时报:可能有的人就喜欢那种浮在表面的奢华和热闹,你却喜欢沉入自己的内心? 筱敏:你说那种奢华他很快乐吗?在我来说觉得挺麻烦的。 信息时报:林贤治说你耽于精神独守,坚持平民立场。这跟你的生活经历有关系吗? 筱敏:我的经历挺简单的,要说有关也可以说有关吧。这种平民立场更多的与我一直思 考的问题有关。但具体到这个词我没有去多想,倒是牧歌的文章标题把我吓了一跳“精神贵 族筱敏”,听起来不合适。我虽然有唯美的倾向,也不能说贵族吧

信息时报:你始终站在精神的高地。他是对你文章的激赏吧。 集永的文字是我的理想 我不认为诗人的出生必是因了曙光的鼓高,事实上,更多的诗人叫,是因为他们感受着 灾难的临近。无论在历史的深处,还是在人心的深处,最为重大的事件都是无法言说的,它 们处在一个言语从未抵达过的疆域,惟赖风的呼啸,还有骨胳在风中的震栗。 信息时报:你后期的散文选择了革命的话题,给自己设了一个很高的高度,在思想界和 文学界很受关注,会否曲高和寡? 筱敏:我写东西不大考虑读者的因素,读者有各种层次 我的东西肯定不是很畅销的 不可能有非常多的读者 我考虑的是怎么写出我 自己认可的东西,自己关心的东西。肯定世 有相当的读者关心这个东西。他们的关注对我也是一种鼓励吧。 信息时报:有人把你那些散文归纳为思想散文。 筱敏:这是评论家的事,但我自己对这部分东西不是太满意 信息时报:是审美上的不满意?其实你的文字即干净又绚丽 我还是希塑能够有种审美的效 也希望在文体和个人风格上有所追求。一个 成熟的作家必须有个人的风格,我比较在意这一点。 信息时报:你喜欢什么样的文字? 筱敏:还是那种比较隽永的东西。我对文字本身有一种特别的迷恋。仅仅说思想含量, 我不能跟思想家相比。我还是希望我的东西是文学的,而不是仅仅表达了一种观点,说明了 个问期。终文学这 一代也许会对这个不感兴趣, 会觉得非常 陈旧和时 这个无所谓 过时不过时,我觉得根本不是 个问趣。 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古希腊,看几百年几千年以前的 东西,还是会觉得很美,很震撼,而与自己很贴近的一些东西反而会觉得没什么意思。文学 作品没有新旧之分,只有好坏之 在宿命下有所作为 流亡者无论是从哪一个是攻缘治之下桃出来的,又在哪一片异乡酒泊,他们都不面有彦 然大物可以依仗,无论被迫还是自愿,他们都回到个人。爱因斯坦认为:“只有个人才能思考 群体或者庞然大物之内的分子,是不能思考的。流亡这个词指的是一种生存态度。她是拒绝 趋附,拒绝从屈:她是尊严,自由。 信息时报:那你最近都在读什么书? 筱敏:比较杂吧,没什么系统。看文学类的多一点,有时好像也不好分,像加缪的《反 抗者》, 类?我喜欢加缪,他具有很深的哲学思想, 又有一种忧郁的文学气质 信息时报:你喜欢的作家?你好象编过一本“流亡者散文” 筱敏:是啊,我喜欢俄罗斯和东欧的流亡者的散文。俄罗斯作家那里渗透着一种很深的 人文关怀和宗教情怀,那是中国作家少有的。美国的比较辽阔和大气。 信息时报:有人也评论说你的散文也有种磅礴之气,也是你有意追求的吗? 筱敏:啊,我要有就好了。我当然希望我有。我远远还没有 信息时报:在中国当代女性散文家里,我觉得你是比较大气的一个 筱敏:但愿吧。我的梦想,既要有一种磅礴之气,也要有幽深的美,这两者在我都是很 倾心的。至于能不能走到那一步,能走多远我不知道,但还是尽力往那个方向挪。 信息时报:有人说,你很象鲁迅,鲁迅在绝望中的坚持。筱敏也是这样。他认识到这种 绝望,但仍坚持他的反抗,他必须这样做。 筱敏:我对鲁迅没有研究,但我觉得有些东西我能理解他。他就是很绝望 ,也可以说是 虚无,对社会对人生都看得很暗淡。他的反抗是在绝望中的反抗,并不抱那种乐观主义的幻 想。但我肯定不能跟他相比。 信息时报:那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吗?
信息时报:你始终站在精神的高地。他是对你文章的激赏吧。 隽永的文字是我的理想 我不认为诗人的出生必是因了曙光的鼓荡,事实上,更多的诗人叫喊,是因为他们感受着 灾难的临近。无论在历史的深处,还是在人心的深处,最为重大的事件都是无法言说的,它 们处在一个言语从未抵达过的疆域,惟赖风的呼啸,还有骨骼在风中的震栗。 信息时报:你后期的散文选择了革命的话题,给自己设了一个很高的高度,在思想界和 文学界很受关注,会否曲高和寡? 筱敏:我写东西不大考虑读者的因素,读者有各种层次。我的东西肯定不是很畅销的, 不可能有非常多的读者。我考虑的是怎么写出我自己认可的东西,自己关心的东西。肯定也 有相当的读者关心这个东西。他们的关注对我也是一种鼓励吧。 信息时报:有人把你那些散文归纳为思想散文。 筱敏:这是评论家的事,但我自己对这部分东西不是太满意。 信息时报:是审美上的不满意?其实你的文字即干净又绚丽。 筱敏:我还是希望能够有种审美的效果,我也希望在文体和个人风格上有所追求。一个 成熟的作家必须有个人的风格,我比较在意这一点。 信息时报:你喜欢什么样的文字? 筱敏:还是那种比较隽永的东西。我对文字本身有一种特别的迷恋。仅仅说思想含量, 我不能跟思想家相比。我还是希望我的东西是文学的,而不是仅仅表达了一种观点,说明了 一个问题。网络文学这一代也许会对这个不感兴趣,会觉得非常陈旧和过时。这个无所谓。 过时不过时,我觉得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古希腊,看几百年几千年以前的 东西,还是会觉得很美,很震撼,而与自己很贴近的一些东西反而会觉得没什么意思。文学 作品没有新旧之分,只有好坏之分。 在宿命下有所作为 流亡者无论是从哪一个暴政统治之下逃出来的,又在哪一片异乡漂泊,他们都不再有庞 然大物可以依仗,无论被迫还是自愿,他们都回到个人。爱因斯坦认为:“只有个人才能思考”。 群体或者庞然大物之内的分子,是不能思考的。流亡这个词指的是一种生存态度。她是拒绝 趋附,拒绝从属;她是尊严,自由。 信息时报:那你最近都在读什么书? 筱敏:比较杂吧,没什么系统。看文学类的多一点,有时好像也不好分,像加缪的《反 抗者》,算哪一类?我喜欢加缪,他具有很深的哲学思想,又有一种忧郁的文学气质。 信息时报:你喜欢的作家?你好象编过一本“流亡者散文”? 筱敏:是啊,我喜欢俄罗斯和东欧的流亡者的散文。俄罗斯作家那里渗透着一种很深的 人文关怀和宗教情怀,那是中国作家少有的。美国的比较辽阔和大气。 信息时报:有人也评论说你的散文也有种磅礴之气,也是你有意追求的吗? 筱敏:啊,我要有就好了。我当然希望我有。我远远还没有。 信息时报:在中国当代女性散文家里,我觉得你是比较大气的一个。 筱敏:但愿吧。我的梦想,既要有一种磅礴之气,也要有幽深的美,这两者在我都是很 倾心的。至于能不能走到那一步,能走多远我不知道,但还是尽力往那个方向挪。 信息时报:有人说,你很象鲁迅,鲁迅在绝望中的坚持。筱敏也是这样。他认识到这种 绝望,但仍坚持他的反抗,他必须这样做。 筱敏:我对鲁迅没有研究,但我觉得有些东西我能理解他。他就是很绝望,也可以说是 虚无,对社会对人生都看得很暗淡。他的反抗是在绝望中的反抗,并不抱那种乐观主义的幻 想。但我肯定不能跟他相比。 信息时报:那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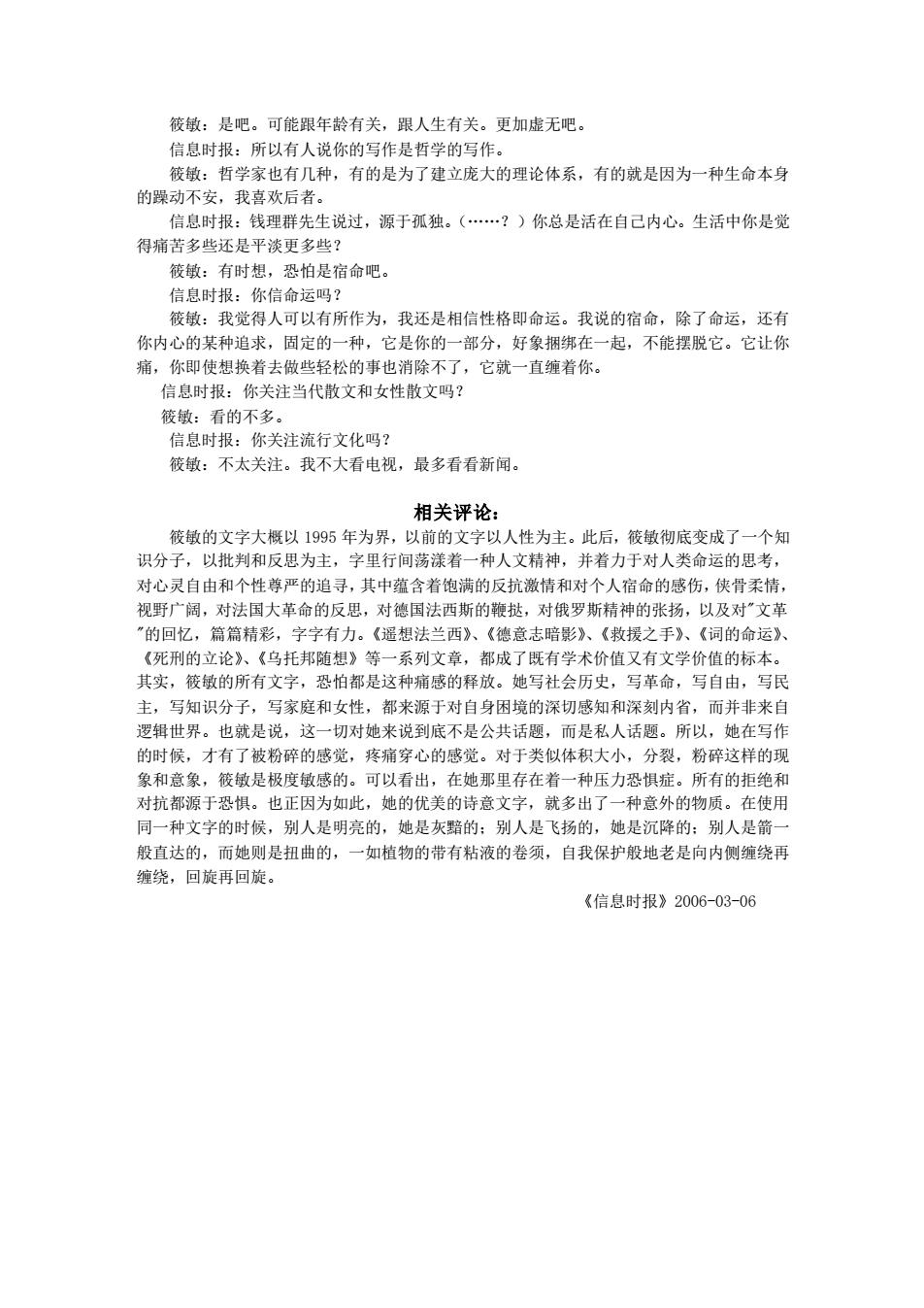
筱敏:是吧。可能跟年龄有关,跟人生有关。更加虑无吧 信息时报:所以有人说你的写作是哲学的写作 筱敏:哲学家也有几种,有的是为了建立庞大的理论体系,有的就是因为一种生命本身 的躁动不安,我喜欢后者· 信息时报:钱理群先生说过,源于孤独。(.?)你总是活在自己内心。生活中你是觉 得痛苦多些还是平淡更多些? 筱镇:有时想,恐怕是宿命吧 信息时报 你信命运 筱敏:我觉得人可以有所作为,我还是相信性格即命运。我说的宿命,除了命运,还有 你内心的某种追求,固定的一种,它是你的一部分,好象捆绑在一起,不能摆脱它。它让你 痛,你即使想换者去做些轻松的事也消除不了,它就一直维者你。 信息时报:你关注当代散文和女性散文吗? 筱敏:看的不多 信息时报:你关注流行文化吗? 筱敏:不太关注。我不大看电视,最多看看新闻 相关评论: 筱敏的文字大概以1995年为界,以前的文字以人性为主。此后,筱敏彻底变成了一个知 识分子,以批判和反思为主, 字里行间荡漾者 种人文精神,并着力于对 类命运的思考 对心灵自由和个性尊严的追寻,其中蕴含着饱满的反抗激情和对个人宿命的感伤,侠骨柔情, 视野广阔,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对德国法西斯的鞭挞,对俄罗斯精神的张扬,以及对“文革 “的回忆,篇篇精彩,字字有力。《遥想法兰西》、《德意志暗影》、《救援之手》、《词的命运》、 《死刑的立论》、《乌托邦随想》等一系列文章,都成了既有学术价值又有文学价值的标本。 其实,筱敏的所有文 子 ,恐怕都是这种痛感的释放。 她写社会历史,写革命,写自由 写民 主,写知识分子,写家庭和女性,都来源于对自身困境的深切感知和深刻内省,而并非来自 逻辑世界。也就是说,这一切对她来说到底不是公共话题,而是私人话题。所以,她在写作 的时候,才有了被粉碎的感觉,疼痛穿心的感觉。对于类似体积大小,分裂,粉碎这样的现 象和意象,被敏是极度敏成的。可以看出,在她那里存在着一种压力恐惧定。所右的拒绝和 对抗都源于恐惧。也正因为如此,她的优美的诗意文字, 就名出 了一种意外的物质。在使用 同一种文字的时候 ,别人是明亮的 她是灰黯的:别人是飞扬的,她是沉降的:别人是箭 般直达的,而她则是扭曲的,一如植物的带有粘液的卷须,自我保护般地老是向内侧缠绕再 缠绕,回旋再回旋。 《信息时报》2006-03-06
筱敏:是吧。可能跟年龄有关,跟人生有关。更加虚无吧。 信息时报:所以有人说你的写作是哲学的写作。 筱敏:哲学家也有几种,有的是为了建立庞大的理论体系,有的就是因为一种生命本身 的躁动不安,我喜欢后者。 信息时报:钱理群先生说过,源于孤独。(.?)你总是活在自己内心。生活中你是觉 得痛苦多些还是平淡更多些? 筱敏:有时想,恐怕是宿命吧。 信息时报:你信命运吗? 筱敏:我觉得人可以有所作为,我还是相信性格即命运。我说的宿命,除了命运,还有 你内心的某种追求,固定的一种,它是你的一部分,好象捆绑在一起,不能摆脱它。它让你 痛,你即使想换着去做些轻松的事也消除不了,它就一直缠着你。 信息时报:你关注当代散文和女性散文吗? 筱敏:看的不多。 信息时报:你关注流行文化吗? 筱敏:不太关注。我不大看电视,最多看看新闻。 相关评论: 筱敏的文字大概以 1995 年为界,以前的文字以人性为主。此后,筱敏彻底变成了一个知 识分子,以批判和反思为主,字里行间荡漾着一种人文精神,并着力于对人类命运的思考, 对心灵自由和个性尊严的追寻,其中蕴含着饱满的反抗激情和对个人宿命的感伤,侠骨柔情, 视野广阔,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对德国法西斯的鞭挞,对俄罗斯精神的张扬,以及对"文革 "的回忆,篇篇精彩,字字有力。《遥想法兰西》、《德意志暗影》、《救援之手》、《词的命运》、 《死刑的立论》、《乌托邦随想》等一系列文章,都成了既有学术价值又有文学价值的标本。 其实,筱敏的所有文字,恐怕都是这种痛感的释放。她写社会历史,写革命,写自由,写民 主,写知识分子,写家庭和女性,都来源于对自身困境的深切感知和深刻内省,而并非来自 逻辑世界。也就是说,这一切对她来说到底不是公共话题,而是私人话题。所以,她在写作 的时候,才有了被粉碎的感觉,疼痛穿心的感觉。对于类似体积大小,分裂,粉碎这样的现 象和意象,筱敏是极度敏感的。可以看出,在她那里存在着一种压力恐惧症。所有的拒绝和 对抗都源于恐惧。也正因为如此,她的优美的诗意文字,就多出了一种意外的物质。在使用 同一种文字的时候,别人是明亮的,她是灰黯的;别人是飞扬的,她是沉降的;别人是箭一 般直达的,而她则是扭曲的,一如植物的带有粘液的卷须,自我保护般地老是向内侧缠绕再 缠绕,回旋再回旋。 《信息时报》2006-0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