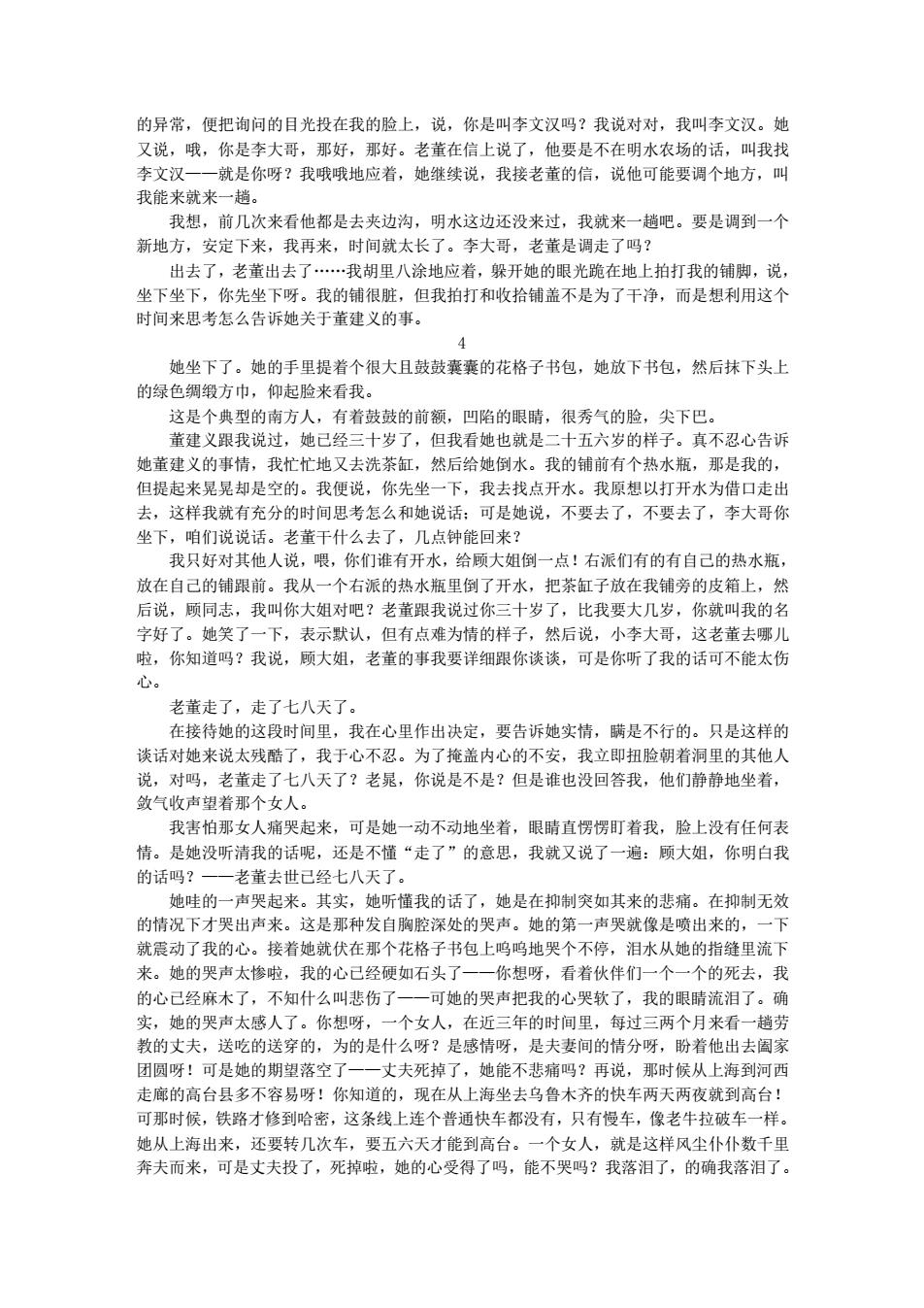
的异常,便把询问的目光投在我的脸上,说,你是叫李文汉吗?我说对对,我叫李文汉。她 又说,哦,你是李大哥,那好,那好。老董在信上说了,他要是不在明水农场的话,叫我找 李文汉 一就是你呀?我哦哦地应着,她继续说,我接老董的信,说他可能要调个地方,叫 我能来就米一趟。 我想,前几次来看他都是去夹边沟,明水这边还没来过,我就来一趟吧。要是调到一个 新地方,安定下来,我再来,时间就太长了。李大哥,老董是调走了吗? 出去了,老董出去了.我胡里八涂地应着,躲开她的眼光跪在地上拍打我的铺脚,说 坐下坐下 你先坐下 我的铺很脏,但我拍打和收拾铺盖不是为了干净,而是想利用这个 时间来思考怎么告诉她关于董建义的事。 她坐下了。她的手里提若个很大且鼓鼓囊囊的花格子书包,她放下书包,然后抹下头上 的绿色绸缎方巾,仰起脸来看我。 这是个典型的南方人,有着鼓鼓的前额,凹陷的眼 ,很秀气的脸 尖下巴 董建义跟我说过,她已经三十岁了,但我看她也就是二十五六岁的样子。真不忍心告诉 她董建义的事情,我忙忙地又去洗茶缸,然后给她倒水。我的铺前有个热水瓶,那是我的, 但提起来晃晃却是空的。我便说,你先坐一下,我去找点开水。我原想以打开水为借口走出 去,这样我就有充分的时间思考怎么和她说话:可是她说,不要去了,不要去了,李大哥你 坐下,咱们说说话。老董干什么去了,几点钟能回来? 我只好对其他人说,喂, 你们谁有开水,给瞬 大姐倒一点!右派们有的有自己的热水瓶 放在自己的铺跟前。我从一个右派的热水瓶里倒了开水,把茶缸子放在我铺旁的皮箱上,然 后说,顾同志,我叫你大姐对吧?老董跟我说过你三十岁了,比我要大几岁,你就叫我的名 字好了。她笑了一下,表示默认,但有点难为情的样子,然后说,小李大哥,这老董去哪儿 啦,你知道吗?我说,顾大姐,老董的事我要详细跟你谈谈,可是你听了我的话可不能太伤 老董走了,走了七八天了 在接待她的这段时间里,我在心里作出决定,要告诉她实情,瞒是不行的。只是这样的 谈话对她来说太残酷了,我于心不忍。为了掩盖内心的不安,我立即扭脸朝若洞里的其他人 说对吗,老芾走了七八天了?老录,你说是不是?但是谁也没回答我。他们静静地坐 敛气收声望者那个女人。 我害怕那女人痛哭起来,可是她 动不动地坐着,眼睛直愣愣盯着我,脸上没有任何表 情。是她没听清我的话呢,还是不懂“走了”的意思,我就又说了一遍:顾大姐,你明白我 的话吗? 一老董去世已经七八天了。 她哇的一声哭起来。其实,她听懂我的话了,她是在抑制突如其来的悲痛。在抑制无效 就震动了我的心。接着她就伏在那个 米。她的哭声太惨啦,我的心已经硬如石头了 一你想呀,看着伙伴们一个 个的死去,我 的心已经麻木了,不知什么叫悲伤了 一可她的哭声把我的心哭软了,我的眼晴流泪了。确 实,她的哭声太感人了。你想呀,一个女人,在近三年的时间里,每过三两个月来看一趟劳 教的丈夫,送吃的送穿的,为的是什么呀?是感情呀,是夫妻间的情分呀,盼若他出去图家 团圆呀!可是她的期望 落空了 丈夫死掉了,她能不悲痛吗?再说 ,那时候从上海到河西 走廊的高台县多不容易呀!你知道的,现在从上海坐去乌鲁木齐的快车两天两夜就到高台 可那时候,铁路才修到哈密,这条线上连个普通快车都没有,只有慢车,像老牛拉破车一样。 她从上海出来,还要转几次车,要五六天才能到高台。一个女人,就是这样风尘仆仆数千里 奔夫而来,可是丈夫投了,死掉啦,她的心受得了吗,能不哭吗?我落泪了,的确我落泪了
的异常,便把询问的目光投在我的脸上,说,你是叫李文汉吗?我说对对,我叫李文汉。她 又说,哦,你是李大哥,那好,那好。老董在信上说了,他要是不在明水农场的话,叫我找 李文汉——就是你呀?我哦哦地应着,她继续说,我接老董的信,说他可能要调个地方,叫 我能来就来一趟。 我想,前几次来看他都是去夹边沟,明水这边还没来过,我就来一趟吧。要是调到一个 新地方,安定下来,我再来,时间就太长了。李大哥,老董是调走了吗? 出去了,老董出去了.我胡里八涂地应着,躲开她的眼光跪在地上拍打我的铺脚,说, 坐下坐下,你先坐下呀。我的铺很脏,但我拍打和收拾铺盖不是为了干净,而是想利用这个 时间来思考怎么告诉她关于董建义的事。 4 她坐下了。她的手里提着个很大且鼓鼓囊囊的花格子书包,她放下书包,然后抹下头上 的绿色绸缎方巾,仰起脸来看我。 这是个典型的南方人,有着鼓鼓的前额,凹陷的眼睛,很秀气的脸,尖下巴。 董建义跟我说过,她已经三十岁了,但我看她也就是二十五六岁的样子。真不忍心告诉 她董建义的事情,我忙忙地又去洗茶缸,然后给她倒水。我的铺前有个热水瓶,那是我的, 但提起来晃晃却是空的。我便说,你先坐一下,我去找点开水。我原想以打开水为借口走出 去,这样我就有充分的时间思考怎么和她说话;可是她说,不要去了,不要去了,李大哥你 坐下,咱们说说话。老董干什么去了,几点钟能回来? 我只好对其他人说,喂,你们谁有开水,给顾大姐倒一点!右派们有的有自己的热水瓶, 放在自己的铺跟前。我从一个右派的热水瓶里倒了开水,把茶缸子放在我铺旁的皮箱上,然 后说,顾同志,我叫你大姐对吧?老董跟我说过你三十岁了,比我要大几岁,你就叫我的名 字好了。她笑了一下,表示默认,但有点难为情的样子,然后说,小李大哥,这老董去哪儿 啦,你知道吗?我说,顾大姐,老董的事我要详细跟你谈谈,可是你听了我的话可不能太伤 心。 老董走了,走了七八天了。 在接待她的这段时间里,我在心里作出决定,要告诉她实情,瞒是不行的。只是这样的 谈话对她来说太残酷了,我于心不忍。为了掩盖内心的不安,我立即扭脸朝着洞里的其他人 说,对吗,老董走了七八天了?老晁,你说是不是?但是谁也没回答我,他们静静地坐着, 敛气收声望着那个女人。 我害怕那女人痛哭起来,可是她一动不动地坐着,眼睛直愣愣盯着我,脸上没有任何表 情。是她没听清我的话呢,还是不懂“走了”的意思,我就又说了一遍:顾大姐,你明白我 的话吗?——老董去世已经七八天了。 她哇的一声哭起来。其实,她听懂我的话了,她是在抑制突如其来的悲痛。在抑制无效 的情况下才哭出声来。这是那种发自胸腔深处的哭声。她的第一声哭就像是喷出来的,一下 就震动了我的心。接着她就伏在那个花格子书包上呜呜地哭个不停,泪水从她的指缝里流下 来。她的哭声太惨啦,我的心已经硬如石头了——你想呀,看着伙伴们一个一个的死去,我 的心已经麻木了,不知什么叫悲伤了——可她的哭声把我的心哭软了,我的眼睛流泪了。确 实,她的哭声太感人了。你想呀,一个女人,在近三年的时间里,每过三两个月来看一趟劳 教的丈夫,送吃的送穿的,为的是什么呀?是感情呀,是夫妻间的情分呀,盼着他出去阖家 团圆呀!可是她的期望落空了——丈夫死掉了,她能不悲痛吗?再说,那时候从上海到河西 走廊的高台县多不容易呀!你知道的,现在从上海坐去乌鲁木齐的快车两天两夜就到高台! 可那时候,铁路才修到哈密,这条线上连个普通快车都没有,只有慢车,像老牛拉破车一样。 她从上海出来,还要转几次车,要五六天才能到高台。一个女人,就是这样风尘仆仆数千里 奔夫而来,可是丈夫投了,死掉啦,她的心受得了吗,能不哭吗?我落泪了,的确我落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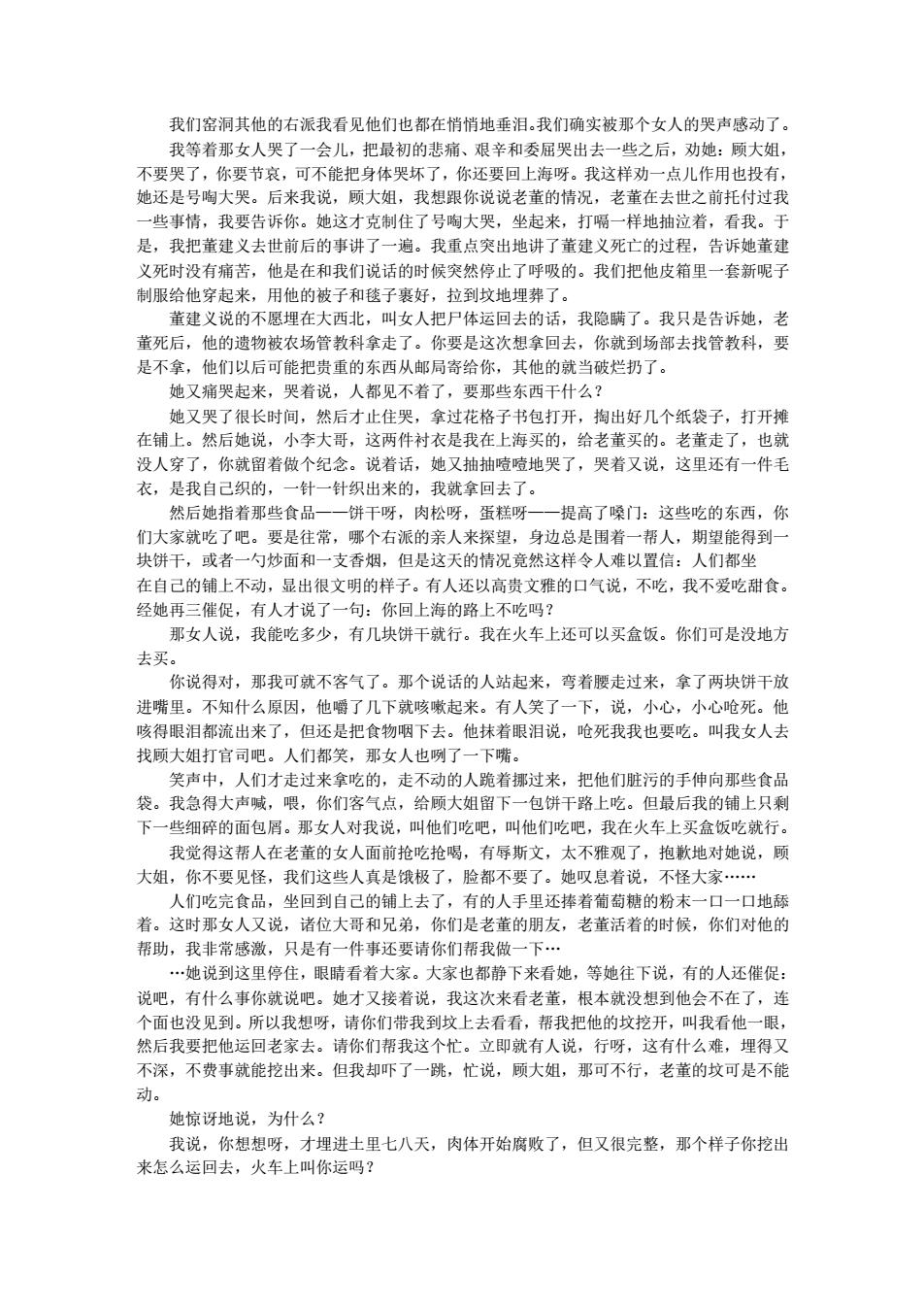
我们窑洞其他的右派我看见他们也都在悄悄地垂泪,我们确实被那个女人的哭声感动了。 我等着那女人哭了一会儿,把最初的悲痛、艰辛和委屈哭出去一些之后,劝她:顾大姐, 不要哭了,你要节哀,可不能把身体哭坏了,你还要回上海呀。我这样劝 点儿作用也投有 她还是号陶大哭。后来我说,顾大姐,我想跟你说说老董的情况,老董在去世之前托付过我 些事情,我要告诉你。她这才克制住了号陶大哭,坐起来,打隔一样地抽泣着,看我。于 是,我把董建义去世前后的事讲了一遍。我重点突出地讲了董建义死亡的过程,告诉她董建 义死时没有痛苦,他是在和我们说话的时候突然停止了呼吸的。我们把他皮箱里一套新呢子 制服给他穿起来,月 我隐瞒了。我只是告诉她,老 董死后,他的遗物被农场管教科拿走了。你要是这次想拿回去,你就到场部去找管教科,要 是不拿,他们以后可能把贵重的东西从邮局寄给你,其他的就当破烂扔了。 她又痛哭起来,哭着说,人都见不若了,要那些东西干什么? 她又哭了很长时间,然后才止住哭,拿过花格子书包打开,掏出好几个纸袋子,打开摊 在铺上。然后她说 小李大 两件衬衣是我在上海 给老董买的 老董走 了,也 没人穿了,你就留者做个纪念。说着话,她又抽抽噎噎地哭了,哭着又说,这里还有一件毛 衣,是我自己织的, 一针一针织出来的,我就拿回去了。 然后她指者那些食品一一饼干呀,肉松呀,蛋糕呀 一提高了嗓门:这些吃的东西,你 们大家就吃了吧。要是往常,哪个右派的亲人来探望,身边总是围着一帮人,期望能得到一 块饼干,或者一勺炒面和一支香烟,但是这天的情况竟然这样令人难以置信:人们都坐 在自己的铺上不动,显出很文明的样子。有人还以高贵文雅的口气说,不吃,我不爱吃甜食。 经她再三催促,有人才说了一句:你回上海的路上不吃吗? 那女人说,我能吃多少,有几块饼干就行。我在火车上还可以买盒饭。你们可是没地方 去买。 你说得对,那我可就不客气了。那个说话的人站起来,弯者腰走过来,拿了两块饼干放 进嘴里。不知什么原因,他嚼了几下就咳嗽起来 。有人笑了 下说, 小 ,小心呛死。他 咳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但还是把食物咽下去。他抹者眼泪说,呛死我我也要吃。叫我女人去 找顾大姐打官司吧。人们都笑,那女人也咧了一下嘴。 笑声中,人们才走过来拿吃的,走不动的人跪着那过来,把他们脏污的手伸向那些食品 袋。我急得大声城,喂,你们安气点,给原大组留下一包饼干路上吃。但最后我的铺上只 一些细碎的面包屑。那女人对我说,叫他们吃吧 叫他们吃吧,我在火车上买盒饭吃就行 我觉得这帮人在老董的女人面前抢吃抢喝,有辱斯文,太不雅观了,抱歉地对她说,顾 大姐,你不要见怪,我们这些人真是饿极了,脸都不要了。她叹息着说,不怪大家. 人们吃完食品,坐回到自己的铺上去了,有的人手里还捧若葡萄糖的粉末一口一口地舔 若。这时那女人又说,诸位大哥和兄弟,你们是老董的朋友,老董活若的时候,你们对他的 帮助,我非常感激,只是有一件事还要请你们帮我做一下. 她说到这里停住,眼睛看着大家。大家也都静下来看她,等她往下说,有的人还催促 说吧,有什么事你就说吧。她才又接着说,我这次来看老董,根本就没想到他会不在了,连 个面也没见到。所以我想呀,请你们带我到坟上去看看,帮我把他的坟挖开,叫我看他一眼, 然后我要把他运回老家去。请你们帮我这个忙。立即就有人说,行呀,这有什么难,埋得又 不深,不费事就能挖出来。但我却吓了一跳,忙说,顾大姐,那可不行,老董的坟可是不能 她惊讶地说,为什么? 我说,你想想呀,才埋进土里七八天,肉体开始腐败了,但又很完整,那个样子你挖出 来怎么运回去,火车上叫你运吗?
我们窑洞其他的右派我看见他们也都在悄悄地垂泪。我们确实被那个女人的哭声感动了。 我等着那女人哭了一会儿,把最初的悲痛、艰辛和委屈哭出去一些之后,劝她:顾大姐, 不要哭了,你要节哀,可不能把身体哭坏了,你还要回上海呀。我这样劝一点儿作用也投有, 她还是号啕大哭。后来我说,顾大姐,我想跟你说说老董的情况,老董在去世之前托付过我 一些事情,我要告诉你。她这才克制住了号啕大哭,坐起来,打嗝一样地抽泣着,看我。于 是,我把董建义去世前后的事讲了一遍。我重点突出地讲了董建义死亡的过程,告诉她董建 义死时没有痛苦,他是在和我们说话的时候突然停止了呼吸的。我们把他皮箱里一套新呢子 制服给他穿起来,用他的被子和毯子裹好,拉到坟地埋葬了。 董建义说的不愿埋在大西北,叫女人把尸体运回去的话,我隐瞒了。我只是告诉她,老 董死后,他的遗物被农场管教科拿走了。你要是这次想拿回去,你就到场部去找管教科,要 是不拿,他们以后可能把贵重的东西从邮局寄给你,其他的就当破烂扔了。 她又痛哭起来,哭着说,人都见不着了,要那些东西干什么? 她又哭了很长时间,然后才止住哭,拿过花格子书包打开,掏出好几个纸袋子,打开摊 在铺上。然后她说,小李大哥,这两件衬衣是我在上海买的,给老董买的。老董走了,也就 没人穿了,你就留着做个纪念。说着话,她又抽抽噎噎地哭了,哭着又说,这里还有一件毛 衣,是我自己织的,一针一针织出来的,我就拿回去了。 然后她指着那些食品——饼干呀,肉松呀,蛋糕呀——提高了嗓门:这些吃的东西,你 们大家就吃了吧。要是往常,哪个右派的亲人来探望,身边总是围着一帮人,期望能得到一 块饼干,或者一勺炒面和一支香烟,但是这天的情况竟然这样令人难以置信:人们都坐 在自己的铺上不动,显出很文明的样子。有人还以高贵文雅的口气说,不吃,我不爱吃甜食。 经她再三催促,有人才说了一句:你回上海的路上不吃吗? 那女人说,我能吃多少,有几块饼干就行。我在火车上还可以买盒饭。你们可是没地方 去买。 你说得对,那我可就不客气了。那个说话的人站起来,弯着腰走过来,拿了两块饼干放 进嘴里。不知什么原因,他嚼了几下就咳嗽起来。有人笑了一下,说,小心,小心呛死。他 咳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但还是把食物咽下去。他抹着眼泪说,呛死我我也要吃。叫我女人去 找顾大姐打官司吧。人们都笑,那女人也咧了一下嘴。 笑声中,人们才走过来拿吃的,走不动的人跪着挪过来,把他们脏污的手伸向那些食品 袋。我急得大声喊,喂,你们客气点,给顾大姐留下一包饼干路上吃。但最后我的铺上只剩 下一些细碎的面包屑。那女人对我说,叫他们吃吧,叫他们吃吧,我在火车上买盒饭吃就行。 我觉得这帮人在老董的女人面前抢吃抢喝,有辱斯文,太不雅观了,抱歉地对她说,顾 大姐,你不要见怪,我们这些人真是饿极了,脸都不要了。她叹息着说,不怪大家. 人们吃完食品,坐回到自己的铺上去了,有的人手里还捧着葡萄糖的粉末一口一口地舔 着。这时那女人又说,诸位大哥和兄弟,你们是老董的朋友,老董活着的时候,你们对他的 帮助,我非常感激,只是有一件事还要请你们帮我做一下. .她说到这里停住,眼睛看着大家。大家也都静下来看她,等她往下说,有的人还催促: 说吧,有什么事你就说吧。她才又接着说,我这次来看老董,根本就没想到他会不在了,连 个面也没见到。所以我想呀,请你们带我到坟上去看看,帮我把他的坟挖开,叫我看他一眼, 然后我要把他运回老家去。请你们帮我这个忙。立即就有人说,行呀,这有什么难,埋得又 不深,不费事就能挖出来。但我却吓了一跳,忙说,顾大姐,那可不行,老董的坟可是不能 动。 她惊讶地说,为什么? 我说,你想想呀,才埋进土里七八天,肉体开始腐败了,但又很完整,那个样子你挖出 来怎么运回去,火车上叫你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