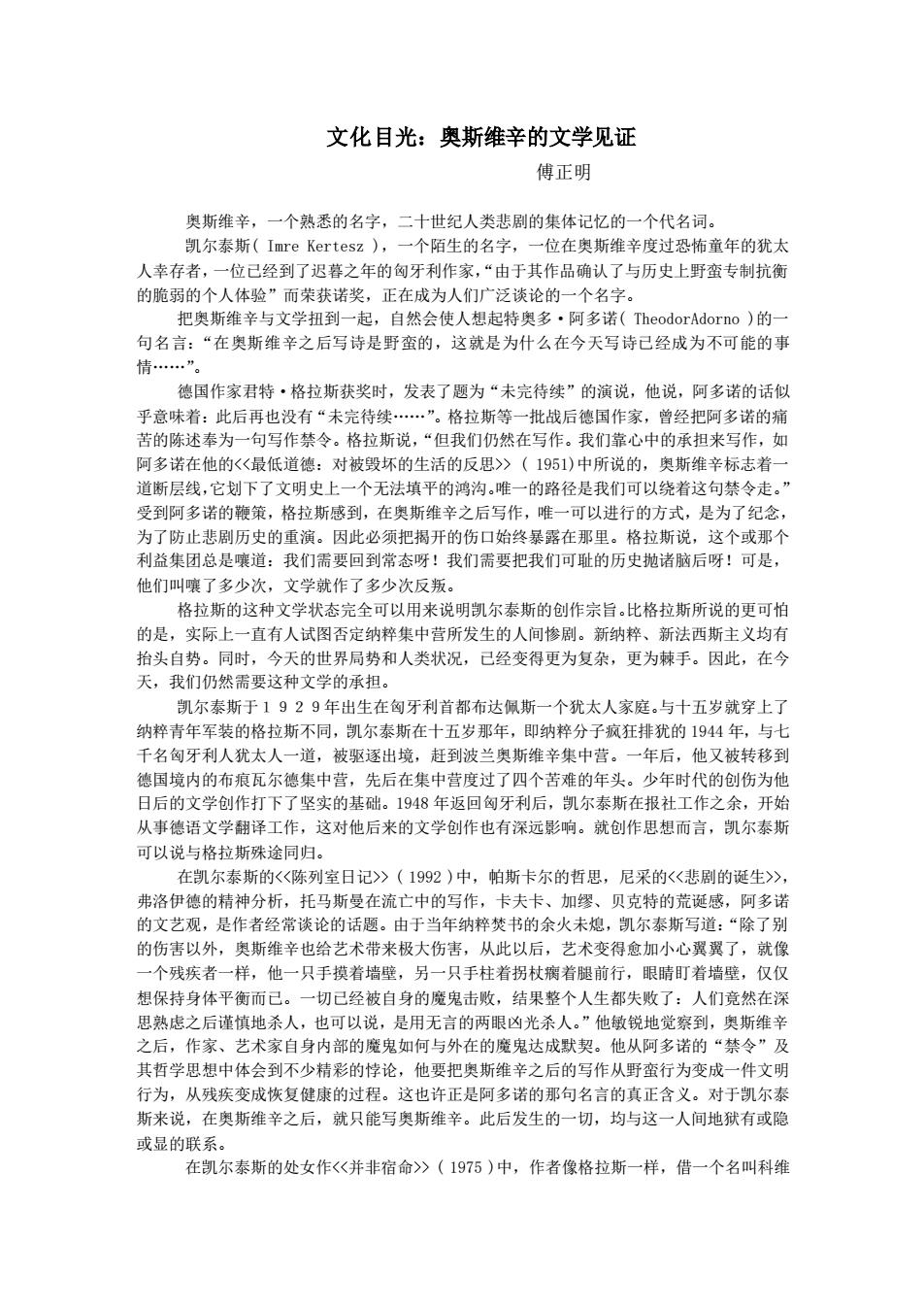
文化目光:奥斯维辛的文学见证 傅正明 奥斯维辛,一个熟悉的名字,二十世纪人类悲剧的集体记忆的一个代名词。 凯尔泰斯(Imre Kertesz),一个陌生的名字,一位在奥斯维辛度过恐怖童年的犹太 人幸存者,一位已经到了迟暮之年的匈牙利作家,“由于其作品确认了与历史上野蛮专制抗衡 的脆弱的个人体验” 而荣获诺奖,正在成为人们广泛谈论的 名字 把奥斯维辛与文学扭到一起,自然会使人想起特奥多·阿多诺(TheodorAdorno)的 句名言:“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写诗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 情.”。 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获奖时,发表了题为“未完待续”的演说,他说,阿多诺的话似 乎意味着:此后再也没有“未完待续 ”。格拉斯等 批战后德国作家, 曾经把阿多诺的痛 苦的陈述奉为句写作禁令格拉说,“自我们然在写作我们心中 承担来写作,如 阿多诺在他的<《最低道德:对被毁坏的生活的反思>》(1951)中所说的,奥斯维辛标志着 道断层线,它划下了文明史上一个无法填平的鸿沟。唯一的路径是我们可以绕着这句禁令走。” 受到阿多诺的鞭策,格拉斯感到,在奥斯维辛之后写作,唯一可以讲行的方式,是为了纪念 为了防止悲剧历史的重演。因此必须把揭开的伤口始终暴露在那里。格拉斯说,这个或那个 利益集团总是嚷道:我们需要回到常态呀:我们需要把我们可耻的历史抛诸后呀!可是 他们叫嚷了多少次,文学就作了多少次反叛。 格拉斯的这种文学状态完全可以用来说明凯尔泰斯的创作宗旨。比格拉斯所说的更可怕 的是,实际上一直有人试图否定纳粹集中营所发生的人间惨剧。新纳粹、新法西斯主义均有 拍头自势。同时,今天的世界局势和人类状况,已经变得更为复杂,更为棘手。因此,在今 天,我们仍然需要这种文学的 承担 凯尔泰斯于1929年出生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一个犹太人家庭。与十五岁就穿上了 纳粹青年军装的格拉斯不同,凯尔泰斯在十五岁那年,即纳粹分子疯狂排犹的1944年,与七 千名匈牙利人犹太人一道,被驱逐出境,赶到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一年后,他又被转移到 德国境内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先后在集中营度时了四个苦难的年头。少年时代的创伤为他 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8年返回匈牙利后,凯尔泰斯在报社工作之余, 开始 从事德语文学翻译工作,这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也有深远影响。就创作思想而言,凯尔泰 可以说与格拉斯殊途同归。 在凯尔泰斯的<陈列室日记>》(1992)中,帕斯卡尔的哲思,尼采的<悲剧的诞生>,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托马撕曼在流亡中的写作,卡夫卡、加缪、贝克特的荒诞感,阿多诺 的文艺观,是作者经常谈论的话题。由于当年纳粹焚书的余火未熄,凯尔泰斯写道:“除了别 的伤害以外,奥斯维辛也给 艺术带来极大伤 从此以后 艺术变得愈加小心翼翼了,就 个残疾者一样,他一只手摸着墙壁,另一只手柱着拐杖摘着腿前行,眼睛町者墙壁,仅仅 想保持身体平衡而已。一切己经被自身的魔鬼击数,结果整个人生都失败了:人们竟然在深 思熟虑之后谨慎地杀人,也可以说,是用无言的两眼凶光杀人。”他敏锐地觉察到,奥斯维辛 之后,作家、艺术家自身内部的魔鬼如何与外在的魔鬼达成默契。他从阿多诺的“禁令”及 其哲学思想中体会到不少精彩的样论,他要把奥斯维辛之后的写作从野蛮行为变成一件文明 行为,从残疾变成恢复健康的过程。这也许正是阿多诺的那句名言的真正含义。对于凯尔素 斯来说,在奥斯维辛之后,就只能写奥斯维辛。此后发生的一切,均与这一人间地狱有或隐 或显的联系。 在凯尔泰斯的处女作<《并非宿命>(1975)中,作者像格拉斯一样,借一个名叫科维
文化目光:奥斯维辛的文学见证 傅正明 奥斯维辛,一个熟悉的名字,二十世纪人类悲剧的集体记忆的一个代名词。 凯尔泰斯( Imre Kertesz ),一个陌生的名字,一位在奥斯维辛度过恐怖童年的犹太 人幸存者,一位已经到了迟暮之年的匈牙利作家,“由于其作品确认了与历史上野蛮专制抗衡 的脆弱的个人体验”而荣获诺奖,正在成为人们广泛谈论的一个名字。 把奥斯维辛与文学扭到一起,自然会使人想起特奥多·阿多诺( TheodorAdorno )的一 句名言:“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就是为什么在今天写诗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 情.”。 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获奖时,发表了题为“未完待续”的演说,他说,阿多诺的话似 乎意味着:此后再也没有“未完待续.”。格拉斯等一批战后德国作家,曾经把阿多诺的痛 苦的陈述奉为一句写作禁令。格拉斯说,“但我们仍然在写作。我们靠心中的承担来写作,如 阿多诺在他的<<最低道德:对被毁坏的生活的反思>> ( 1951)中所说的,奥斯维辛标志着一 道断层线,它划下了文明史上一个无法填平的鸿沟。唯一的路径是我们可以绕着这句禁令走。” 受到阿多诺的鞭策,格拉斯感到,在奥斯维辛之后写作,唯一可以进行的方式,是为了纪念, 为了防止悲剧历史的重演。因此必须把揭开的伤口始终暴露在那里。格拉斯说,这个或那个 利益集团总是嚷道:我们需要回到常态呀!我们需要把我们可耻的历史抛诸脑后呀!可是, 他们叫嚷了多少次,文学就作了多少次反叛。 格拉斯的这种文学状态完全可以用来说明凯尔泰斯的创作宗旨。比格拉斯所说的更可怕 的是,实际上一直有人试图否定纳粹集中营所发生的人间惨剧。新纳粹、新法西斯主义均有 抬头自势。同时,今天的世界局势和人类状况,已经变得更为复杂,更为棘手。因此,在今 天,我们仍然需要这种文学的承担。 凯尔泰斯于1929年出生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一个犹太人家庭。与十五岁就穿上了 纳粹青年军装的格拉斯不同,凯尔泰斯在十五岁那年,即纳粹分子疯狂排犹的 1944 年,与七 千名匈牙利人犹太人一道,被驱逐出境,赶到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一年后,他又被转移到 德国境内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先后在集中营度过了四个苦难的年头。少年时代的创伤为他 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8 年返回匈牙利后,凯尔泰斯在报社工作之余,开始 从事德语文学翻译工作,这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也有深远影响。就创作思想而言,凯尔泰斯 可以说与格拉斯殊途同归。 在凯尔泰斯的<<陈列室日记>> ( 1992 )中,帕斯卡尔的哲思,尼采的<<悲剧的诞生>>,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托马斯曼在流亡中的写作,卡夫卡、加缪、贝克特的荒诞感,阿多诺 的文艺观,是作者经常谈论的话题。由于当年纳粹焚书的余火未熄,凯尔泰斯写道:“除了别 的伤害以外,奥斯维辛也给艺术带来极大伤害,从此以后,艺术变得愈加小心翼翼了,就像 一个残疾者一样,他一只手摸着墙壁,另一只手柱着拐杖瘸着腿前行,眼睛盯着墙壁,仅仅 想保持身体平衡而已。一切已经被自身的魔鬼击败,结果整个人生都失败了:人们竟然在深 思熟虑之后谨慎地杀人,也可以说,是用无言的两眼凶光杀人。”他敏锐地觉察到,奥斯维辛 之后,作家、艺术家自身内部的魔鬼如何与外在的魔鬼达成默契。他从阿多诺的“禁令”及 其哲学思想中体会到不少精彩的悖论,他要把奥斯维辛之后的写作从野蛮行为变成一件文明 行为,从残疾变成恢复健康的过程。这也许正是阿多诺的那句名言的真正含义。对于凯尔泰 斯来说,在奥斯维辛之后,就只能写奥斯维辛。此后发生的一切,均与这一人间地狱有或隐 或显的联系。 在凯尔泰斯的处女作<<并非宿命>> ( 1975 )中,作者像格拉斯一样,借一个名叫科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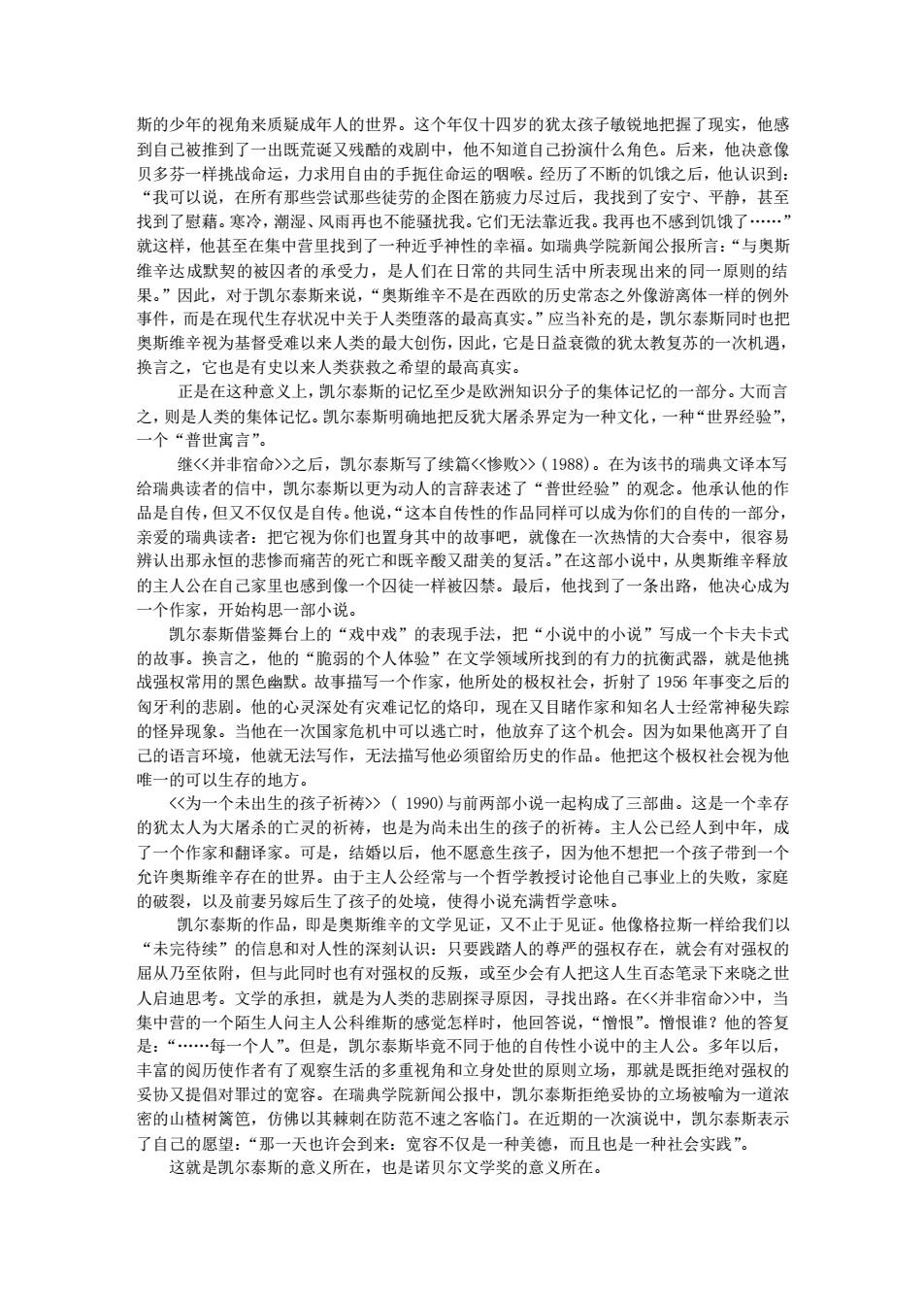
斯的少年的视角来历疑成年人的世界。这个年仅十四岁的犹太孩子敏操地把握了现实,他成 到自己被推到了一出旺荒证又残酷的戏调中,他不知道白己粉宿什么角色。后来,他决意俊 贝多 二样排战命运 力求用自由的手扼住命运的咽喉 经历了不断的饥饿之后 他认识至 我可以说,在所有那些尝试那些徒劳的企图在筋疲力尽过后, 我找到了安行 平静,甚至 找到了慰藉。寒冷,潮湿、风雨再也不能骚扰我。它们无法靠近我。我再也不感到饥饿了· 就这样,他其至在集中营里找到了一种近平神性的幸温。加瑞典学院新闻公报所言:“与奥期 维辛达成默契的被闪者的承受力,是人们在日常的共同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同一原则的结 果。”因此, “爽斯维辛不是在西欧 态之外像游离体 一样的例外 事件 而是在现代生存 状况中 关于人类堕落的最高真实 补充的是,凯尔泰斯同时世 奥斯维辛视为基督受难以来人类的最大创伤,因此,它是日益衰微的犹太教复苏的一次机遇 换言之,它也是有史以来人类获救之希望的最高直实。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凯尔泰斯的记忆至少是欧洲知识分子的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大而言 之,则是人类的集体记忆。凯尔泰斯明确地把反犹大屠杀界定为一种文化, 种“世界经验” 个“普世寓言 继<《并非宿命>之后,凯尔泰斯写了续篇<惨败>》(1988)。在为该书的瑞典文译本三 给瑞典读者的信中,凯尔泰斯以更为动人的言辞表述了“普世经验”的观念。他承认他的作 品是自传,但又不仅仅是自传。他说,“这本自传性的作品同样可以成为你们的自传的一部分, 亲爱的瑞典读者:把它视为你们也置身其中的故事,就像在一次热情的大合奉中,很容易 排认出那永恒的非橡而痛的死亡和辛酸又甜羊的复话。”在这部小中,从奥断维辛拯成 的主人公在自己家里也感到像一个囚徒一样被囚禁。最后,他找到了一条出路,他决心成为 个作家,开始构思一部小说。 凯尔泰斯借鉴舞台上的“戏中戏”的表现手法,把“小说中的小说”写成一个卡夫卡式 的故事。换言之,他的“脆弱的个人体验”在文学领域所找到的有力的抗衡武器,就是他桃 战强权常用的黑色幽默。故事描写一个作家,他所处的极权社会 折射了1956年事弯之后的 匈牙利的悲剧。他的心灵深处有灾难记忆的烙印,现在又目睹作家和知名人士经常神秘失 的怪异现象。当他在一次国家危机中可以逃亡时,他放弃了这个机会。因为如果他离开了自 己的语言环境,他就无法写作,无法描写他必须留给历史的作品。他把这个极权社会视为他 唯一的可以生存的地方。 《为一个未出生的该子祈铸>》(1990)与前两部小说一起构成了三部曲。这是一个幸存 的犹太人为大屠杀的亡灵的析祷,也是为尚未出生的孩 子的析祷 主人公已经人到中年,成 一个作家和翻译家。可是,结婚以后,他不愿意生孩子,因为他不想把 个孩子带到一个 允许奥斯维辛存在的世界。由于主人公经常与一个哲学教授讨论他自己事业上的失败,家庭 的破裂,以及前妻另嫁后生了孩子的处境,使得小说充满哲学意味。 凯尔泰斯的作品,即是奥斯维辛的文学见证,又不止于见证。他像格拉斯一样给我们以 “未完待续”的信息和对人性的深刻认识:只要践踏人的尊严的强权存在,就会有对强权的 屈从乃至依附,但与此同时也有对强权的反叛,或至少会有人把这人生百态笔录下来晓之 人启迪思考。文学的承担,就是为人类的悲剧探寻原因,寻找出路。在(《并非宿命>>中,当 集中营的一个陌生人问主人公科维斯的感觉怎样时,他回答说,“僧根”。憎恨谁?他的答复 是:“.每一个人”。但是,凯尔泰断毕竞不同于他的自传性小说中的主人公。多年以后 丰富的阅历使作者有了观察生活的多重视角和立身处世的原则立场,那就是既拒绝对强权的 妥协又提倡对罪过 在瑞典学院新间 公报中,凯尔泰斯拒绝妥协的立场被喻为 密的山楂树篱笆,仿佛以其棘刺在防范不速之客临门。在近期的一次演说中,凯尔泰斯表示 了自己的愿望:“那一天也许会到来:宽容不仅是一种美德,而且也是一种社会实践”。 这就是凯尔泰斯的意义所在,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意义所在
斯的少年的视角来质疑成年人的世界。这个年仅十四岁的犹太孩子敏锐地把握了现实,他感 到自己被推到了一出既荒诞又残酷的戏剧中,他不知道自己扮演什么角色。后来,他决意像 贝多芬一样挑战命运,力求用自由的手扼住命运的咽喉。经历了不断的饥饿之后,他认识到: “我可以说,在所有那些尝试那些徒劳的企图在筋疲力尽过后,我找到了安宁、平静,甚至 找到了慰藉。寒冷,潮湿、风雨再也不能骚扰我。它们无法靠近我。我再也不感到饥饿了.” 就这样,他甚至在集中营里找到了一种近乎神性的幸福。如瑞典学院新闻公报所言:“与奥斯 维辛达成默契的被囚者的承受力,是人们在日常的共同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同一原则的结 果。”因此,对于凯尔泰斯来说,“奥斯维辛不是在西欧的历史常态之外像游离体一样的例外 事件,而是在现代生存状况中关于人类堕落的最高真实。”应当补充的是,凯尔泰斯同时也把 奥斯维辛视为基督受难以来人类的最大创伤,因此,它是日益衰微的犹太教复苏的一次机遇, 换言之,它也是有史以来人类获救之希望的最高真实。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凯尔泰斯的记忆至少是欧洲知识分子的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大而言 之,则是人类的集体记忆。凯尔泰斯明确地把反犹大屠杀界定为一种文化,一种“世界经验”, 一个“普世寓言”。 继<<并非宿命>>之后,凯尔泰斯写了续篇<<惨败>> ( 1988)。在为该书的瑞典文译本写 给瑞典读者的信中,凯尔泰斯以更为动人的言辞表述了“普世经验”的观念。他承认他的作 品是自传,但又不仅仅是自传。他说,“这本自传性的作品同样可以成为你们的自传的一部分, 亲爱的瑞典读者:把它视为你们也置身其中的故事吧,就像在一次热情的大合奏中,很容易 辨认出那永恒的悲惨而痛苦的死亡和既辛酸又甜美的复活。”在这部小说中,从奥斯维辛释放 的主人公在自己家里也感到像一个囚徒一样被囚禁。最后,他找到了一条出路,他决心成为 一个作家,开始构思一部小说。 凯尔泰斯借鉴舞台上的“戏中戏”的表现手法,把“小说中的小说”写成一个卡夫卡式 的故事。换言之,他的“脆弱的个人体验”在文学领域所找到的有力的抗衡武器,就是他挑 战强权常用的黑色幽默。故事描写一个作家,他所处的极权社会,折射了 1956 年事变之后的 匈牙利的悲剧。他的心灵深处有灾难记忆的烙印,现在又目睹作家和知名人士经常神秘失踪 的怪异现象。当他在一次国家危机中可以逃亡时,他放弃了这个机会。因为如果他离开了自 己的语言环境,他就无法写作,无法描写他必须留给历史的作品。他把这个极权社会视为他 唯一的可以生存的地方。 <<为一个未出生的孩子祈祷>> ( 1990)与前两部小说一起构成了三部曲。这是一个幸存 的犹太人为大屠杀的亡灵的祈祷,也是为尚未出生的孩子的祈祷。主人公已经人到中年,成 了一个作家和翻译家。可是,结婚以后,他不愿意生孩子,因为他不想把一个孩子带到一个 允许奥斯维辛存在的世界。由于主人公经常与一个哲学教授讨论他自己事业上的失败,家庭 的破裂,以及前妻另嫁后生了孩子的处境,使得小说充满哲学意味。 凯尔泰斯的作品,即是奥斯维辛的文学见证,又不止于见证。他像格拉斯一样给我们以 “未完待续”的信息和对人性的深刻认识:只要践踏人的尊严的强权存在,就会有对强权的 屈从乃至依附,但与此同时也有对强权的反叛,或至少会有人把这人生百态笔录下来晓之世 人启迪思考。文学的承担,就是为人类的悲剧探寻原因,寻找出路。在<<并非宿命>>中,当 集中营的一个陌生人问主人公科维斯的感觉怎样时,他回答说,“憎恨”。憎恨谁?他的答复 是:“.每一个人”。但是,凯尔泰斯毕竟不同于他的自传性小说中的主人公。多年以后, 丰富的阅历使作者有了观察生活的多重视角和立身处世的原则立场,那就是既拒绝对强权的 妥协又提倡对罪过的宽容。在瑞典学院新闻公报中,凯尔泰斯拒绝妥协的立场被喻为一道浓 密的山楂树篱笆,仿佛以其棘刺在防范不速之客临门。在近期的一次演说中,凯尔泰斯表示 了自己的愿望:“那一天也许会到来:宽容不仅是一种美德,而且也是一种社会实践”。 这就是凯尔泰斯的意义所在,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