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醒的说梦者 莫言 1987年,有一位古怪而残酷的青年小说家以他的几部血腥的作品,震动了文坛。一时 间,大部分评论家的目光,都集中在他的身上。此人姓余名华,浙江海盐人。后来,有幸我 与他同居一室,进行者同学的岁月,逐渐对这个诡异的灵魂有所了解。坦言地说,这是个令 人不愉快的家伙。他说话期期艾艾,双目长放精光,不会顺人情说好话,尤其不会崇拜“名 流,据说他 当过五年牙医,我不敢想象病人 这个狂生的铁钳下将造受什么样的酷刑。 然,余华有他的另一面,这一面与大家差不多。这一面在文学的目光下显得通俗而平庸。我 欣赏的是那些独步雄鸡式的、令人不愉快的东西。“正常”的人一般都在浴室里引吭高歌,余 华则在大庭广众面前狂叫,他基本不理会别人会有的反应,而比较自由地表现他狂欢的本性。 狂欢是童心的最露骨的表现,是浪漫精神最充分的体验。这家伙在某种意义上是个顽童, 某种意义上又是个成熟得可怕的老翁 对人的了解促使我重新考虑他的小说,试图 点老 于艺术的话 尽管这显得多余。任何一位有异秉的人都是 个深不可测的陷阱 都是 一本鸡 念的经,都是一颗难剃的头颅,对他的分析注定是出力不讨好的营生。这里用得上孔夫子精 神: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我首先要做的工作,是缩小范围,把这个复杂的性格抛到一边,简单地,从思想和文学 的能力方面给他定性: 首先这是 个具有很强的理性思维能力的人他清晰的思想脉络借助若有条不素的逻辑 转换词,曲折但是并不隐晦地表达出来。其次这个人具有在小说中施放烟雾弹和在烟雾中捕 捉亦鬼亦人的幻影的才能,而且是那么超卓。 上述两方面的结合,正如矛盾的统一,构成了他的一批条理清楚的一一仿梦小说。 干是金华便成了中国当代文坛上的第一个洁丽的说梦者 这种类型的小说,我认为并非从余华始,如奥人卡夫卡的作品,可以说篇篇都有梦中境 界,最典型的如《乡村医生》等,简直是一个梦的实录,也许是他确实记录了一个梦,也许 他编织了一个梦,这都无关紧要。余华曾坦率地述说过卡夫卡对他的启示,在他之前,加西 亚·马尔克斯在巴黎的阁楼上读《变形记》后,也曾如梦初醒地骂道:“他妈的小说原来可 以这样写。” 这是一种对于小说的顿悟,而那当头的棒喝,完全来自卡夫卡小说中那种对生活或者是 世界的独特的处理方法。卡夫卡如同博尔赫斯一样,是一位为作家写作的作家。他的意义 于他的小说中那种超越生活的、神谕般的力量。每隔些年头,总有些有慧根的天才,从他的 著作中,读出一些法门米,从而羽化成仙。余华是这样的一个幸运儿郎. 毫无疑问,这个令人不愉快的家伙,是个“残酷的天才”,也许是牙医的生涯培养和发 展了他的这种天性,促使他像拔牙一样把客观事物中包涵的确定性意义全部拔除了。据说他 当牙医时就是这样:全部拔光。 不管 牙还是坏牙。 这是 个彻底的牙医,改行后,变成 个彻底的小说家。于是,在他营造的文学口腔里,剩下的只有血肉模糊的牙床,向人们昭示 着牙齿们曾经存在过的幻影。由此推演,可以下这样的断语:如果让他画一棵树,他只画树 的倒影。 当然,我捕捉到的,也仅仅是他的幻影 是什么样的因缘,使余华成为这样的小说家?回答这个问题,是传记作家的任务。现在, 我翻开他的第一本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我没有精力读完这本集子,况且,我认为,对 个作家米说,并没有读完同行的全部作品的必要,无论他是多么优秀。 我来分析《十八岁出门远行》这篇小说里的仿梦成分: 他写道:“柏油马路起伏不止,马路像是贴在海浪上。我走在这条山区公路上,我像一
清醒的说梦者 莫言 1987 年,有一位古怪而残酷的青年小说家以他的几部血腥的作品,震动了文坛。一时 间,大部分评论家的目光,都集中在他的身上。此人姓余名华,浙江海盐人。后来,有幸我 与他同居一室,进行着同学的岁月,逐渐对这个诡异的灵魂有所了解。坦言地说,这是个令 人不愉快的家伙。他说话期期艾艾,双目长放精光,不会顺人情说好话,尤其不会崇拜“名 流”。据说他曾当过五年牙医,我不敢想象病人在这个狂生的铁钳下将遭受什么样的酷刑。当 然,余华有他的另一面,这一面与大家差不多。这一面在文学的目光下显得通俗而平庸。我 欣赏的是那些独步雄鸡式的、令人不愉快的东西。“正常”的人一般都在浴室里引吭高歌,余 华则在大庭广众面前狂叫,他基本不理会别人会有的反应,而比较自由地表现他狂欢的本性。 狂欢是童心的最露骨的表现,是浪漫精神最充分的体验。这家伙在某种意义上是个顽童,在 某种意义上又是个成熟得可怕的老翁。对人的了解促使我重新考虑他的小说,试图说一点关 于艺术的话,尽管这显得多余。任何一位有异秉的人都是一个深不可测的陷阱,都是一本难 念的经,都是一颗难剃的头颅,对他的分析注定是出力不讨好的营生。这里用得上孔夫子精 神;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我首先要做的工作,是缩小范围,把这个复杂的性格抛到一边,简单地,从思想和文学 的能力方面给他定性: 首先这是一个具有很强的理性思维能力的人。他清晰的思想脉络借助着有条不紊的逻辑 转换词,曲折但是并不隐晦地表达出来。其次这个人具有在小说中施放烟雾弹和在烟雾中捕 捉亦鬼亦人的幻影的才能,而且是那么超卓。 上述两方面的结合,正如矛盾的统一,构成了他的一批条理清楚的——仿梦小说。 于是余华便成了中国当代文坛上的第一个清醒的说梦者。 这种类型的小说,我认为并非从余华始,如奥人卡夫卡的作品,可以说篇篇都有梦中境 界,最典型的如《乡村医生》等,简直是一个梦的实录,也许是他确实记录了一个梦,也许 他编织了一个梦,这都无关紧要。余华曾坦率地述说过卡夫卡对他的启示,在他之前,加西 亚·马尔克斯在巴黎的阁楼上读《变形记》后,也曾如梦初醒地骂道:“他妈的!小说原来可 以这样写。” 这是一种对于小说的顿悟,而那当头的棒喝,完全来自卡夫卡小说中那种对生活或者是 世界的独特的处理方法。卡夫卡如同博尔赫斯一样,是一位为作家写作的作家。他的意义在 于他的小说中那种超越生活的、神谕般的力量。每隔些年头,总有些有慧根的天才,从他的 著作中,读出一些法门来,从而羽化成仙。余华是这样的一个幸运儿郎. 毫无疑问,这个令人不愉快的家伙,是个“残酷的天才”,也许是牙医的生涯培养和发 展了他的这种天性,促使他像拔牙一样把客观事物中包涵的确定性意义全部拔除了。据说他 当牙医时就是这样:全部拔光,不管好牙还是坏牙。这是一个彻底的牙医,改行后,变成一 个彻底的小说家。于是,在他营造的文学口腔里,剩下的只有血肉模糊的牙床,向人们昭示 着牙齿们曾经存在过的幻影。由此推演,可以下这样的断语;如果让他画一棵树,他只画树 的倒影。 当然,我捕捉到的,也仅仅是他的幻影。 是什么样的因缘,使余华成为这样的小说家?回答这个问题,是传记作家的任务。现在, 我翻开他的第一本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我没有精力读完这本集子,况且,我认为,对一 个作家来说,并没有读完同行的全部作品的必要,无论他是多么优秀。 我来分析《十八岁出门远行》这篇小说里的仿梦成分: 他写道:“柏油马路起伏不止,马路像是贴在海浪上。我走在这条山区公路上,我像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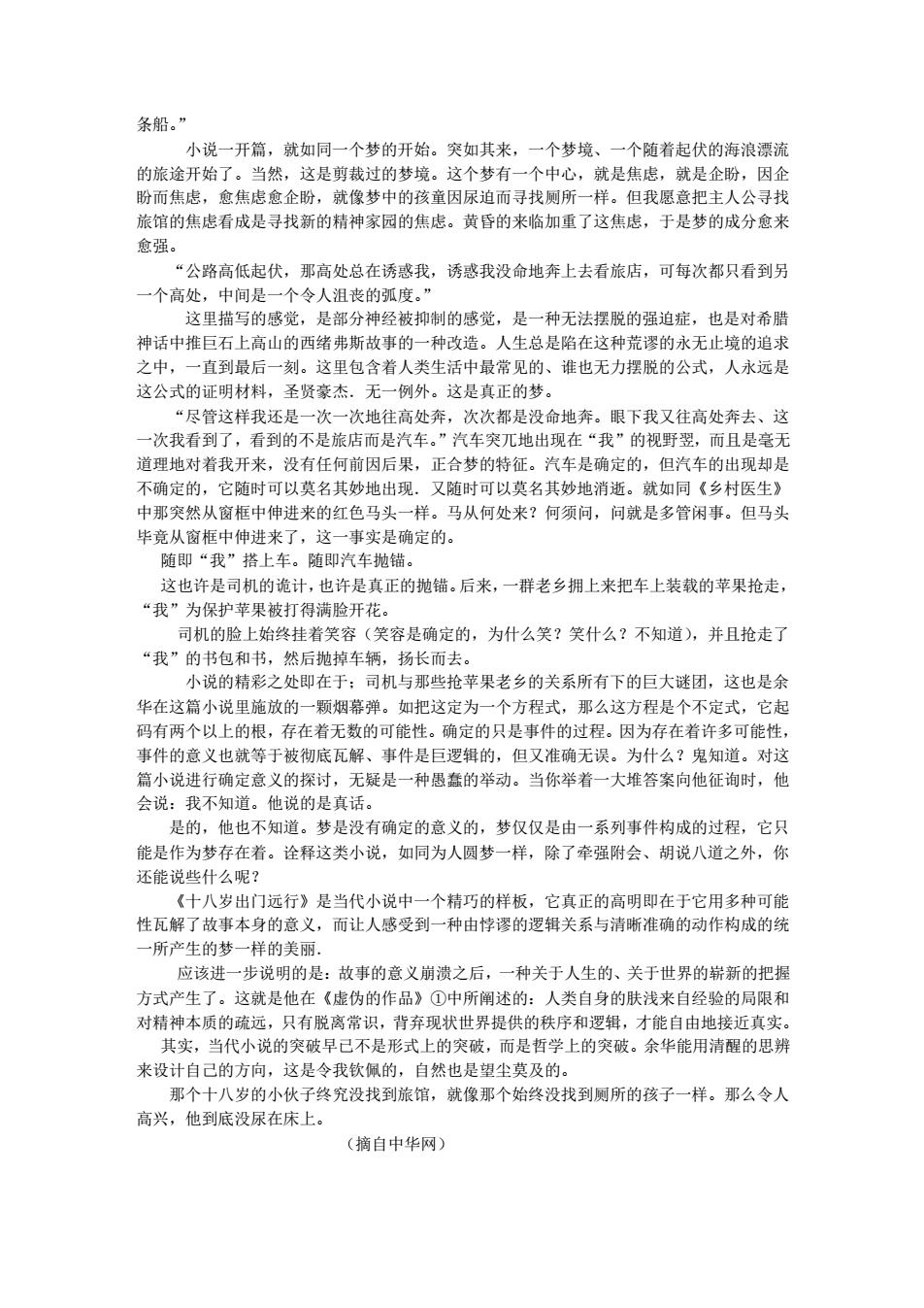
条船。” 小说一开篇就加同一个梦的开始。其来一个梦培 一个浦若起伏的海浪潭洁 的旅途开始了 然,这是剪裁过的梦 境。这个梦有 一个中 就是焦 就是企盼 因金 盼而焦虑 愈焦虑愈企盼,就像梦中的孩童因尿迫而寻找厕所一样。但我愿意把主人公寻找 旅馆的焦虑看成是寻找新的精神家园的焦虑。黄昏的来临加重了这焦虑,于是梦的成分愈来 愈强。 “公路高低起伏,那高处总在诱或我,诱或我沿命地森上去看旅店,可每次都只看到另 个高处 一个令人沮丧的弧度。 是部分神经被抑制的感觉, 一种无法摆脱的强迫症,也是对希脂 神话中推巨石上高山的西绪弗斯故事的一种改造。人生总是陷在这种荒谬的水无止境的追求 之中,一直到最后一刻。这里包含着人类生活中最常见的、谁也无力摆脱的公式,人永远是 这公式的证明材料,圣贤豪杰。无一例外。这是真正的梦。 “尽管这样我还是 一次一次地往高处奔,次次都是没命地奔。眼下我又往高处奔去、 次我看到 看到的不是旅店而是汽车。”汽车突兀地出现在 “我 的视野多,而且是毫无 道理地对者我开来,没有任何前因后果,正合梦的特征。汽车是确定的,但汽车的出现却是 不确定的,它随时可以莫名其妙地出现。又随时可以莫名其妙地消逝。就如同《乡村医生》 中那突然从窗框中伸进来的红色马头一样。马从何处来?何须问,问就是多管闲事。但马头 共意从窗框中伸讲来了,议一事实是确定的 随即“我”搭上车。随即汽车抛锚 这也许是司机的诡计,也许是真正的抛错。后来,一群老乡拥上来把车上装载的苹果抢走, “我”为保护苹果被打得满脸开花。 司机的脸上始终挂着笑容(笑容是确定的,为什么笑?笑什么?不知道),并且抢走了 “我”的书包和书,然后抛掉车辆,扬长而去 小说的精彩之处即在于:司机与那些抢苹果老乡的关系所有下的巨大谜团,这也是余 华在这篇小说里施放的 一颗烟幕弹。如把这定为一个方程式,那么这方程是个不定式,它起 码有两个以上的根,存在者无数的可能性。确定的只是事件的过程。因为存在着许多可能性 事件的意义也就等于被彻底瓦解、事件是巨逻辑的,但又准确无误。为什么?鬼知道。对这 篇小说进行确定意义的探讨,无疑是一种愚意的举动。当你举着一大堆答案向他征询时,他 会说:我不知道。他说的是真话。 是的,他也不知道。梦是没有确定的意义的,梦仅仅是由一系列事件构成的过程,它只 能是作为梦存在着。诠释这类小说,如同为人圆梦一样,除了牵强附会、胡说八道之外,你 还能说些什么呢? 《十八岁出门远行》是当代小说中一个精巧的样板,它真正的高明即在于它用多种可能 性瓦解了故事本身的意义,而让人感受到一种由悖谬的逻辑关系与清晰准确的动作构成的统 所产生的梦一样的丽 应该进一步说明的是:故事的意义崩溃之后,一种关于人生的、关于世界的崭新的把 方式产生了。这就是他在《虚伪的作品》①中所阐述的:人类自身的肤浅来自经验的局限和 对精神本质的疏远,只有脱离常识,背弃现状世界提供的秩序和逻辑,才能自由地接近真实。 其实,当代小说的突破早已不是形式上的突破,而是哲学上的突破。余华能用清醒的思辨 来设计自己的方向,这是令我钦佩的,自然也是望尘莫及的 那个十八岁的小伙子终究没找到旅馆,就像那个始终没找到厕所的孩子一样。那么令人 高兴,他到底没尿在床上。 (摘自中华网)
条船。” 小说一开篇,就如同一个梦的开始。突如其来,一个梦境、一个随着起伏的海浪漂流 的旅途开始了。当然,这是剪裁过的梦境。这个梦有一个中心,就是焦虑,就是企盼,因企 盼而焦虑,愈焦虑愈企盼,就像梦中的孩童因尿迫而寻找厕所一样。但我愿意把主人公寻找 旅馆的焦虑看成是寻找新的精神家园的焦虑。黄昏的来临加重了这焦虑,于是梦的成分愈来 愈强。 “公路高低起伏,那高处总在诱惑我,诱惑我没命地奔上去看旅店,可每次都只看到另 一个高处,中间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弧度。” 这里描写的感觉,是部分神经被抑制的感觉,是一种无法摆脱的强迫症,也是对希腊 神话中推巨石上高山的西绪弗斯故事的一种改造。人生总是陷在这种荒谬的永无止境的追求 之中,一直到最后一刻。这里包含着人类生活中最常见的、谁也无力摆脱的公式,人永远是 这公式的证明材料,圣贤豪杰.无一例外。这是真正的梦。 “尽管这样我还是一次一次地往高处奔,次次都是没命地奔。眼下我又往高处奔去、这 一次我看到了,看到的不是旅店而是汽车。”汽车突兀地出现在“我”的视野翌,而且是毫无 道理地对着我开来,没有任何前因后果,正合梦的特征。汽车是确定的,但汽车的出现却是 不确定的,它随时可以莫名其妙地出现.又随时可以莫名其妙地消逝。就如同《乡村医生》 中那突然从窗框中伸进来的红色马头一样。马从何处来?何须问,问就是多管闲事。但马头 毕竟从窗框中伸进来了,这一事实是确定的。 随即“我”搭上车。随即汽车抛锚。 这也许是司机的诡计,也许是真正的抛锚。后来,一群老乡拥上来把车上装载的苹果抢走, “我”为保护苹果被打得满脸开花。 司机的脸上始终挂着笑容(笑容是确定的,为什么笑?笑什么?不知道),并且抢走了 “我”的书包和书,然后抛掉车辆,扬长而去。 小说的精彩之处即在于;司机与那些抢苹果老乡的关系所有下的巨大谜团,这也是余 华在这篇小说里施放的一颗烟幕弹。如把这定为一个方程式,那么这方程是个不定式,它起 码有两个以上的根,存在着无数的可能性。确定的只是事件的过程。因为存在着许多可能性, 事件的意义也就等于被彻底瓦解、事件是巨逻辑的,但又准确无误。为什么?鬼知道。对这 篇小说进行确定意义的探讨,无疑是一种愚蠢的举动。当你举着一大堆答案向他征询时,他 会说:我不知道。他说的是真话。 是的,他也不知道。梦是没有确定的意义的,梦仅仅是由一系列事件构成的过程,它只 能是作为梦存在着。诠释这类小说,如同为人圆梦一样,除了牵强附会、胡说八道之外,你 还能说些什么呢? 《十八岁出门远行》是当代小说中一个精巧的样板,它真正的高明即在于它用多种可能 性瓦解了故事本身的意义,而让人感受到一种由悖谬的逻辑关系与清晰准确的动作构成的统 一所产生的梦一样的美丽. 应该进一步说明的是:故事的意义崩溃之后,一种关于人生的、关于世界的崭新的把握 方式产生了。这就是他在《虚伪的作品》①中所阐述的:人类自身的肤浅来自经验的局限和 对精神本质的疏远,只有脱离常识,背弃现状世界提供的秩序和逻辑,才能自由地接近真实。 其实,当代小说的突破早已不是形式上的突破,而是哲学上的突破。余华能用清醒的思辨 来设计自己的方向,这是令我钦佩的,自然也是望尘莫及的。 那个十八岁的小伙子终究没找到旅馆,就像那个始终没找到厕所的孩子一样。那么令人 高兴,他到底没尿在床上。 (摘自中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