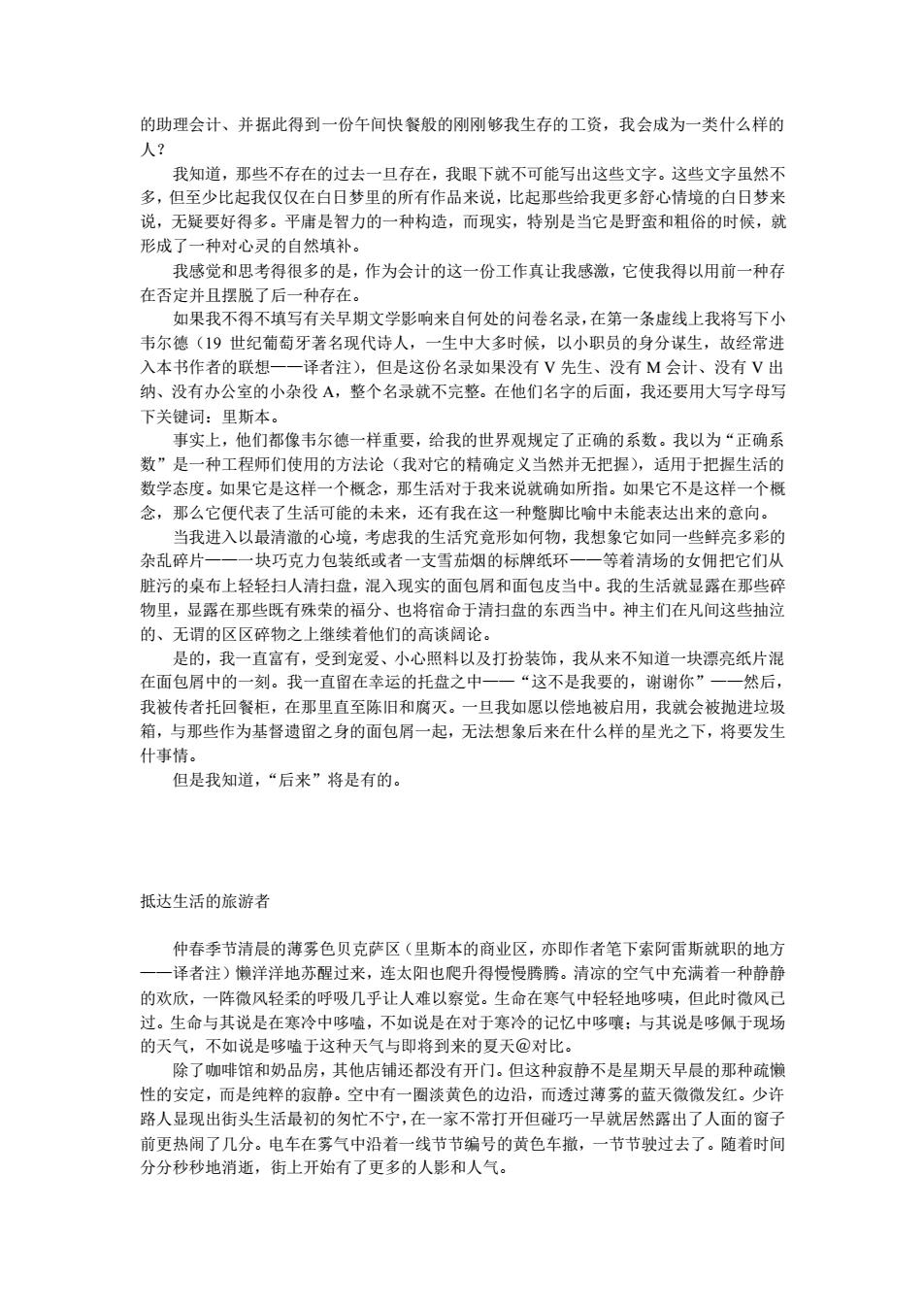
的助理会计、并据此得到一份午间快餐般的刚刚够我生存的工资,我会成为一类什么样的 我知道,那些不存在的过去一旦存在,我眼下就不可能写出这些文字。 这些文字虽然不 多,但至少比起我仅仅在白日梦里的所有作品来说,比起那些给我更多舒心情境的白日梦来 说,无疑要好得多。平庸是智力的一种构造,而现实,特别是当它是野蛮和相俗的时候,就 形成了一种对心灵的自然填补 我感觉和思考得很多的是,作为会计的这一份工作真让我感激,它使我得以用前一种存 在香定并且摆脱了后 种存在 如果我不得不填写有关早期文学影响来自何处的问卷名录,在第一条虚线上我将写下小 韦尔德(19世纪葡萄牙著名现代诗人,一生中大多时候,以小职员的身分谋生,故经常进 入本书作者的联想一一译者注),但是这份名录如果没有V先生、没有M会计、没有V出 纳、没有办公室的小杂役A,整个名录就不完整。在他们名字的后面,我还要用大写字母写 下关键词:里斯 事实上,他们都像韦尔德一样重要,给我的世界观规定了正确的系数。我以为“正确系 数”是一种工程师们使用的方法论(我对它的精确定义当然并无把握),适用于把握生活的 数学态度。如果它是这样一个概念,那生活对于我来说就确如所指。如果它不是这样一个概 念,那么它便代表了生活可能的未来,还有我在这一种整脚比喻中未能表达出来的意向。 当我进入以最清澉的心境,考虑我的生活究竟形如何物,我想象它如同一些鲜亮多彩的 杂乱碎片 巧克 包装纸或者 一支雪茄烟的标 等若清场的女佣把它们 脏污的桌布上轻轻扫人清扫盘,混入现实的面包屑和面包皮当中。我的生活就显露在那些碎 物里,显露在那些既有殊荣的福分、也将宿命于清扫盘的东西当中。神主们在凡间这些抽泣 的、无谓的区区碎物之上维续着他们的高谈阔论。 是的,我一直富有,受到宠爱、小心照料以及打扮装饰,我从来不知道一块漂亮纸片混 在面包屑中的一刻。我一直留在幸运的托盘之中 ,“这不是我要的 我被传者托回餐柜,在那里直至陈旧和腐灭。 一旦我如愿以偿地被启用,我就会被抛进垃圾 箱,与那些作为基督遗留之身的面包屑一起,无法想象后米在什么样的星光之下,将要发生 什事情。 但是我知道,“后来”将是有的 抵达生活的旅游者 仲春季节清晨的薄雾色贝克萨区(里斯本的商业区,亦即作者笔下索阿雷斯就职的地方 译者注)懒洋洋地苏醒过来,连太阳也爬升得慢慢腾腾。清凉的空气中充满着一种静前 的欢欣,一阵微风轻柔的呼吸几乎让人难以察觉。生命在寒气中轻轻地哆咦,但此时微风己 过。生命与其说是在寒冷中哆啮,不如说是在对于寒冷的记忆中哆嚷:与其说是哆佩于现场 的天气,不如说是哆赌于这种天气与即将到来的夏天@对比 除了咖啡馆和奶品房,其他店铺还都没有开门。但这种寂静不是星期天早晨的那种疏懒 性的安定,而是纯粹的寂静。空中有一图淡黄色的边沿,而透过薄雾的蓝天微微发红。少 路人显现出街头生活最初的匆忙不宁,在一家不常打开但碰巧一早就居然露出了人面的窗了 前更热闹了几分。电车在雾气中沿着一线节节编号的黄色车撒, 一节节驶过去了。随着时间 分分秒秒地消浙,街上开始有了更多的人量影和人气
的助理会计、并据此得到一份午间快餐般的刚刚够我生存的工资,我会成为一类什么样的 人? 我知道,那些不存在的过去一旦存在,我眼下就不可能写出这些文字。这些文字虽然不 多,但至少比起我仅仅在白日梦里的所有作品来说,比起那些给我更多舒心情境的白日梦来 说,无疑要好得多。平庸是智力的一种构造,而现实,特别是当它是野蛮和粗俗的时候,就 形成了一种对心灵的自然填补。 我感觉和思考得很多的是,作为会计的这一份工作真让我感激,它使我得以用前一种存 在否定并且摆脱了后一种存在。 如果我不得不填写有关早期文学影响来自何处的问卷名录,在第一条虚线上我将写下小 韦尔德(19 世纪葡萄牙著名现代诗人,一生中大多时候,以小职员的身分谋生,故经常进 入本书作者的联想——译者注),但是这份名录如果没有 V 先生、没有 M 会计、没有 V 出 纳、没有办公室的小杂役 A,整个名录就不完整。在他们名字的后面,我还要用大写字母写 下关键词:里斯本。 事实上,他们都像韦尔德一样重要,给我的世界观规定了正确的系数。我以为“正确系 数”是一种工程师们使用的方法论(我对它的精确定义当然并无把握),适用于把握生活的 数学态度。如果它是这样一个概念,那生活对于我来说就确如所指。如果它不是这样一个概 念,那么它便代表了生活可能的未来,还有我在这一种蹩脚比喻中未能表达出来的意向。 当我进入以最清澈的心境,考虑我的生活究竟形如何物,我想象它如同一些鲜亮多彩的 杂乱碎片——一块巧克力包装纸或者一支雪茄烟的标牌纸环——等着清场的女佣把它们从 脏污的桌布上轻轻扫人清扫盘,混入现实的面包屑和面包皮当中。我的生活就显露在那些碎 物里,显露在那些既有殊荣的福分、也将宿命于清扫盘的东西当中。神主们在凡间这些抽泣 的、无谓的区区碎物之上继续着他们的高谈阔论。 是的,我一直富有,受到宠爱、小心照料以及打扮装饰,我从来不知道一块漂亮纸片混 在面包屑中的一刻。我一直留在幸运的托盘之中——“这不是我要的,谢谢你”——然后, 我被传者托回餐柜,在那里直至陈旧和腐灭。一旦我如愿以偿地被启用,我就会被抛进垃圾 箱,与那些作为基督遗留之身的面包屑一起,无法想象后来在什么样的星光之下,将要发生 什事情。 但是我知道,“后来”将是有的。 抵达生活的旅游者 仲春季节清晨的薄雾色贝克萨区(里斯本的商业区,亦即作者笔下索阿雷斯就职的地方 ——译者注)懒洋洋地苏醒过来,连太阳也爬升得慢慢腾腾。清凉的空气中充满着一种静静 的欢欣,一阵微风轻柔的呼吸几乎让人难以察觉。生命在寒气中轻轻地哆咦,但此时微风已 过。生命与其说是在寒冷中哆嗑,不如说是在对于寒冷的记忆中哆嚷;与其说是哆佩于现场 的天气,不如说是哆嗑于这种天气与即将到来的夏天@对比。 除了咖啡馆和奶品房,其他店铺还都没有开门。但这种寂静不是星期天早晨的那种疏懒 性的安定,而是纯粹的寂静。空中有一圈淡黄色的边沿,而透过薄雾的蓝天微微发红。少许 路人显现出街头生活最初的匆忙不宁,在一家不常打开但碰巧一早就居然露出了人面的窗子 前更热闹了几分。电车在雾气中沿着一线节节编号的黄色车撤,一节节驶过去了。随着时间 分分秒秒地消逝,街上开始有了更多的人影和人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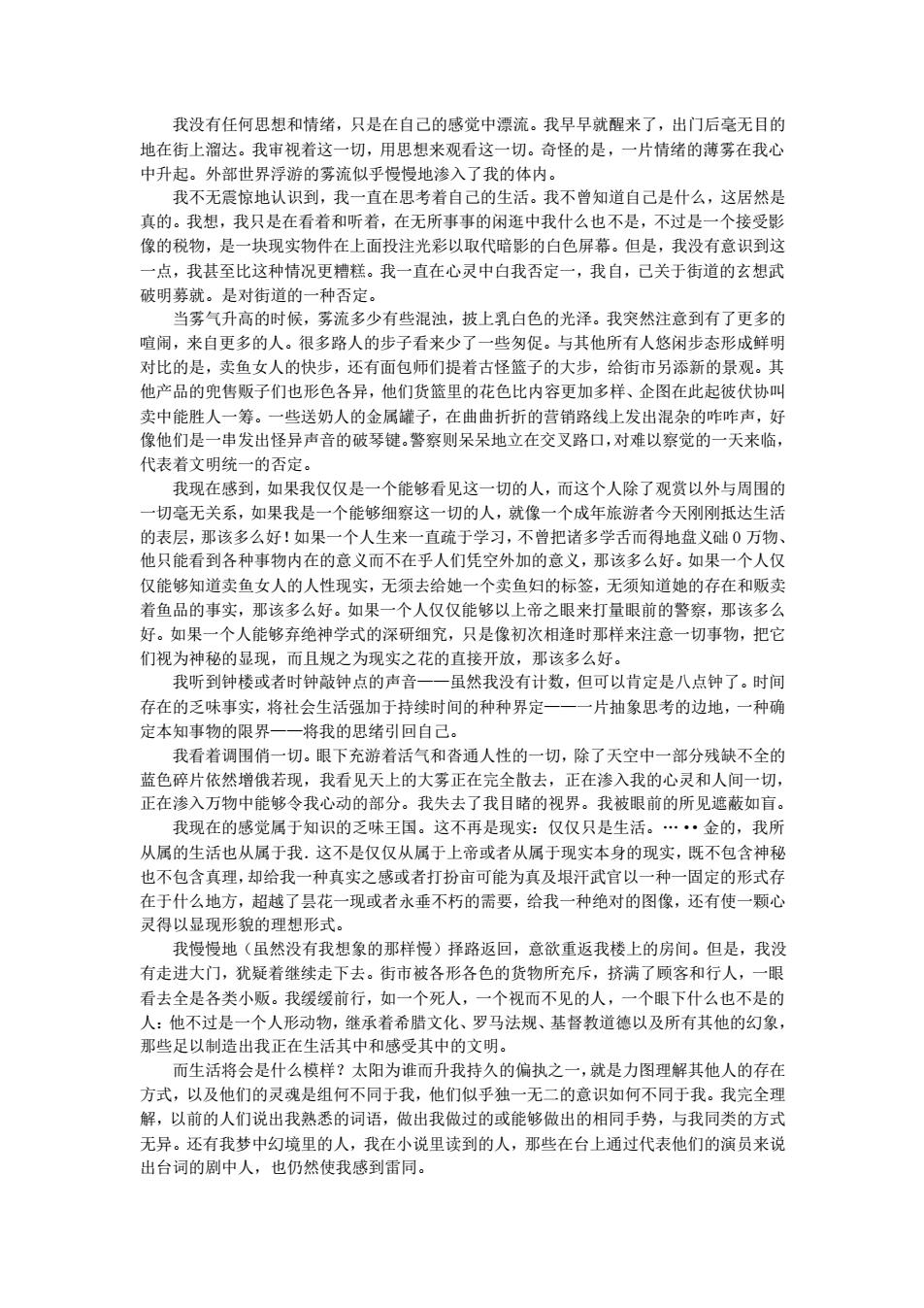
我沿右任何思想和桔烤。只是在自己的成微中趣流。我早早就醒来了,出门后亮无日的 地在街上溜达。我审视着这一切,用思想来观看这一切。奇怪的是,一片情绪的薄雾在我心 中升起。外部世界浮游的雾流似乎慢慢地渗入 了我的体内 我不无震惊地认识到,我一直在思考着自己的生活。我不曾知道自己是什么,这居然 真的。我想,我只是在看着和听者,在无所事事的闲逛中我什么也不是,不过是一个接受影 像的税物,是一块现实物件在上面投注光影以取代暗影的白色屏幕。但是,我没有意识到这 一点,我其至出这种情况更槽鞋。我一直在心,灵中白我否定一,我自,已关千街道的玄想武 破明募就。是对街道的 种香 当雾气升高的时候,雾流多少有些混浊,技上乳白色的光泽。我突然注意到有了更多的 喧闹,来自更多的人。很多路人的步子看来少了一些匆促。与其他所有人悠闲步态形成鲜明 对比的是,卖角女人的快步,还有面包师们提若古怪旅子的大步,给街市另添新的景观。其 他产品的兜售贩子们也形色各异,他们货篮里的花色比内容更加多样、企图在此起彼伏协 中能胜人第 一些送奶人的金属罐子,在曲曲折折的 营销路线上发出混杂的咋咋声,好 像他们是一串发出怪异声音的破琴键。警察则呆呆地立在交叉路口,对难以察觉 天来临 代表者文明统一的否定。 我现在感到,如果我仅仅是一个能够看见这一切的人,而这个人除了观赏以外与周围的 一切毫无关系,如果我是一个能够细察这一切的人,就像一个成年旅游者今天刚刚抵达生活 的表层,那该多么好!如果一个人生来一直疏干学习,不曾把诸多学舌而得地盘义础0万物 他只能看到各种事物内在的意义而不在平人们凭空外加的意义,那该多么好。如果一个人仅 仅能够知道卖鱼女人的人性现实,无须去给她一个实鱼妇的标签,无须知道她的存在和贩卖 着鱼品的事实,那该多么好。如果一个人仅仅能够以上帝之眼来打量眼前的警察,那该多么 好。如果一个人能够弃绝神学式的深研细究,只是像初次相逢时那样来注意一切事物,把它 们视为神秘的显现,而且规之为现实之花的直接开放,那该多么好。 我听到钟楼或者时钟敲钟点的声音 虽然我沿有计数,但可以背定是八点钟了。时间 存在的乏味事实 ,将社会生活强加 持续时间的种种界定 片抽象思考的边地 种碗 定木知事物的限界 将我的思绪引回自己。 我看若调围俏一切。眼下充游若活气和沓通人性的一切,除了天空中一部分残缺不全的 蓝色碎片依然增俄若现,我看见天上的大雾正在完全散去,正在渗入我的心灵和人间一切, 正在渗入万物中能够令我心动的部分。我失去了我目睹的视界。我被眼前的所见遮蔽如直。 我现在的感觉属于知识的乏味王国。 这不再是现实:仅仅只是生活 .金的,我所 从属的生活也从属于我.这不是仅仅从属于上帝或者从属于现实本身的现实,既不包含神秘 也不包含真理,却给我一种真实之感或者打扮亩可能为真及垠汗武官以一种一固定的形式存 在于什么地方,超越了昙花一现或者永垂不朽的需要,给我一种绝对的图像,还有使一颗心 灵得以显现形貌的理想形式 我慢慢地(虽然没有我想象的那样慢)择路返回,意欲重返我棱上的房 ]。但是,我没 有走进大门,犹疑着继续走下去。街市被各形各色的货物所充斥 挤满了顾客和行人, 看去全是各类小贩。我缓缓前行,如一个死人,一个视而不见的人,一个眼下什么也不是的 人:他不过是一个人形动物,继承着希腊文化、罗马法规、基督教道德以及所有其他的幻象, 那些足以制造出我正在生活其中和感受其中的文明 而生活将会是什么模样?太阳为谁而升我持久的偏执之一,就是力图理解其他人的存在 方式,以及他们的灵魂是组何不同于我,他们似乎独一 的意识如何不同于我。我完全理 解,以前的人们说出我熟悉的词语,做出我做过的或能够做出的相同手势,与我同类的方式 无异。还有我梦中幻境里的人,我在小说里读到的人,那些在台上通过代表他们的演员来说 出台词的剧中人,也仍然使我感到雷同
我没有任何思想和情绪,只是在自己的感觉中漂流。我早早就醒来了,出门后毫无目的 地在街上溜达。我审视着这一切,用思想来观看这一切。奇怪的是,一片情绪的薄雾在我心 中升起。外部世界浮游的雾流似乎慢慢地渗入了我的体内。 我不无震惊地认识到,我一直在思考着自己的生活。我不曾知道自己是什么,这居然是 真的。我想,我只是在看着和听着,在无所事事的闲逛中我什么也不是,不过是一个接受影 像的税物,是一块现实物件在上面投注光彩以取代暗影的白色屏幕。但是,我没有意识到这 一点,我甚至比这种情况更糟糕。我一直在心灵中白我否定一,我自,已关于街道的玄想武 破明募就。是对街道的一种否定。 当雾气升高的时候,雾流多少有些混浊,披上乳白色的光泽。我突然注意到有了更多的 喧闹,来自更多的人。很多路人的步子看来少了一些匆促。与其他所有人悠闲步态形成鲜明 对比的是,卖鱼女人的快步,还有面包师们提着古怪篮子的大步,给街市另添新的景观。其 他产品的兜售贩子们也形色各异,他们货篮里的花色比内容更加多样、企图在此起彼伏协叫 卖中能胜人一筹。一些送奶人的金属罐子,在曲曲折折的营销路线上发出混杂的咋咋声,好 像他们是一串发出怪异声音的破琴键。警察则呆呆地立在交叉路口,对难以察觉的一天来临, 代表着文明统一的否定。 我现在感到,如果我仅仅是一个能够看见这一切的人,而这个人除了观赏以外与周围的 一切毫无关系,如果我是一个能够细察这一切的人,就像一个成年旅游者今天刚刚抵达生活 的表层,那该多么好!如果一个人生来一直疏于学习,不曾把诸多学舌而得地盘义础 0 万物、 他只能看到各种事物内在的意义而不在乎人们凭空外加的意义,那该多么好。如果一个人仅 仅能够知道卖鱼女人的人性现实,无须去给她一个卖鱼妇的标签,无须知道她的存在和贩卖 着鱼品的事实,那该多么好。如果一个人仅仅能够以上帝之眼来打量眼前的警察,那该多么 好。如果一个人能够弃绝神学式的深研细究,只是像初次相逢时那样来注意一切事物,把它 们视为神秘的显现,而且规之为现实之花的直接开放,那该多么好。 我听到钟楼或者时钟敲钟点的声音——虽然我没有计数,但可以肯定是八点钟了。时间 存在的乏味事实,将社会生活强加于持续时间的种种界定——一片抽象思考的边地,一种确 定本知事物的限界——将我的思绪引回自己。 我看着调围俏一切。眼下充游着活气和沓通人性的一切,除了天空中一部分残缺不全的 蓝色碎片依然增俄若现,我看见天上的大雾正在完全散去,正在渗入我的心灵和人间一切, 正在渗入万物中能够令我心动的部分。我失去了我目睹的视界。我被眼前的所见遮蔽如盲。 我现在的感觉属于知识的乏味王国。这不再是现实:仅仅只是生活。.··金的,我所 从属的生活也从属于我.这不是仅仅从属于上帝或者从属于现实本身的现实,既不包含神秘 也不包含真理,却给我一种真实之感或者打扮亩可能为真及垠汗武官以一种一固定的形式存 在于什么地方,超越了昙花一现或者永垂不朽的需要,给我一种绝对的图像,还有使一颗心 灵得以显现形貌的理想形式。 我慢慢地(虽然没有我想象的那样慢)择路返回,意欲重返我楼上的房间。但是,我没 有走进大门,犹疑着继续走下去。街市被各形各色的货物所充斥,挤满了顾客和行人,一眼 看去全是各类小贩。我缓缓前行,如一个死人,一个视而不见的人,一个眼下什么也不是的 人:他不过是一个人形动物,继承着希腊文化、罗马法规、基督教道德以及所有其他的幻象, 那些足以制造出我正在生活其中和感受其中的文明。 而生活将会是什么模样?太阳为谁而升我持久的偏执之一,就是力图理解其他人的存在 方式,以及他们的灵魂是组何不同于我,他们似乎独一无二的意识如何不同于我。我完全理 解,以前的人们说出我熟悉的词语,做出我做过的或能够做出的相同手势,与我同类的方式 无异。还有我梦中幻境里的人,我在小说里读到的人,那些在台上通过代表他们的演员来说 出台词的剧中人,也仍然使我感到雷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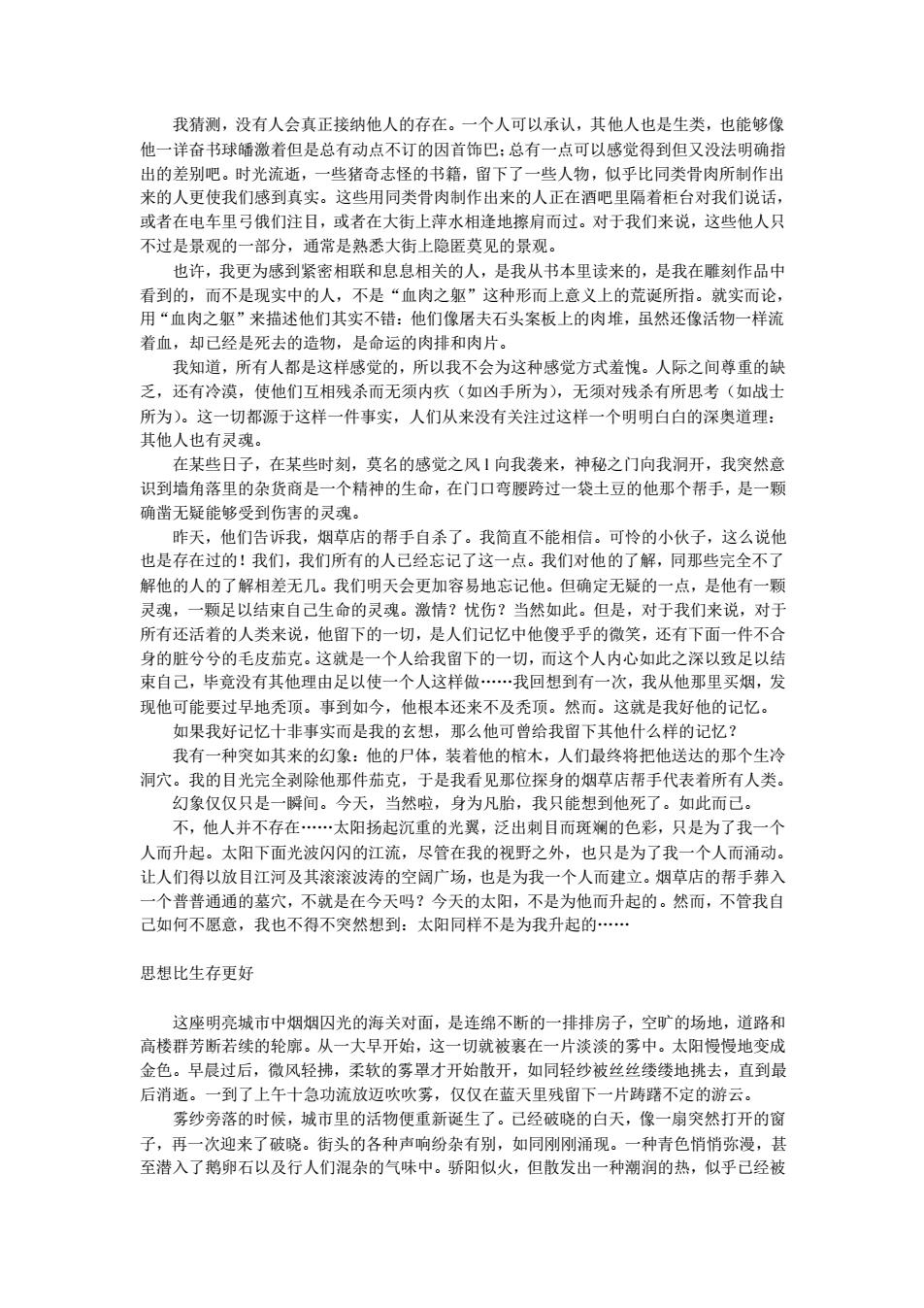
我猜测,没有人会真正接纳他人的存在。一个人可以承认,其他人也是生类,也能够像 他一详奋书球婚激者但是总有动点不订的因首饰巴:总有一点可以感觉得到但又没法明确指 出的差别吧。时光 近 些猪奇志怪的书籍,留下了 些人物,似乎比同类骨肉所制作 来的人更使我们感到真实。这些用同类骨肉制作出来的人正在酒吧里隔着柜台对我们说话, 或者在电车里弓俄们注目,或者在大街上萍水相逢地擦肩而过。对于我们来说,这些他人只 不过是景观的一部分,通常是熟悉大街上隐匿莫见的景观。 也许,我更为感到紧密相联和总息相关的人,是我从书本里读来的,是我在雕刻作品中 看 而不是现实 ”这种形而上意义 的荒诞所指 就实而 用“血肉之躯”来描述他们其实不错:他们像居夫石头案板上的肉堆,虽然还像活物一样流 着血,却已经是死去的造物,是命运的肉排和肉片。 我知道,所有人都是这样感觉的,所以我不会为这种感觉方式羞愧。人际之间尊重的缺 乏,还有冷植,使他们互相残杀而无须内疚(如凶手所为),无须对残杀有所思考(如战士 所为) 切都源于这样一件事实,人们从来没有关注过这样一个明明白白的深奥道理: 其他人也有灵魂 在某些日子,在某些时刻,莫名的感觉之风1向我袭来,神秘之门向我洞开,我突然意 识到墙角落里的杂货商是一个精神的生命,在门口弯腰跨过一袋土豆的他那个帮手,是一颗 确凿无疑能够受到伤害的灵魂」 昨天,他们告诉我,烟草店的帮手自杀了。我简直不能相信。可怜的小伙子,这么说他 也是存在过的 我们,我们所有的人 一点。我们对他的了解 那些完全不 解他的人的了解相差无几。我们明天会更加容易地忘记他。但确定无凝的一点,是他有一颗 灵魂,一题足以结束自己生命的灵魂。激情?忧伤?当然如此。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对于 所有还活着的人类来说,他留下的一切,是人们记忆中他傻乎乎的微笑,还有下面一件不合 身的给公的毛皮描古。这就是一个人给我留下的一切,而这个人内心,如此之深以致足以 束自己,毕竞没有其他理由足以使 一个人这 回想到有一》 我从他那里买烟,发 现他可能要过早地秃顶。事到如今,他根本还来不及秃顶。然而。这就是我好他的记忆 如果我好记忆十非事实而是我的玄想,那么他可曾给我留下其他什么样的记忆? 我有一种突如其来的幻象:他的尸体,装若他的棺木,人们最终将把他送达的那个生冷 洞穴。我的目光完全剥除他邦件茄克,于是我看见那位探身的烟草店帮手代表着所有人类。 幻象仅仅只是一服间 。今天,当然啦,身为凡胎,我只能想到他死了。如此而己 不,他人并不存在 大阳 扬起沉重的光翼,泛出刺目而斑 的色彩,只是为了我 人而升起。太阳下面光波闪闪的江流,尽管在我的视野之外,也只是为了我一个人而涌动 让人们得以放目江河及其滚滚波涛的空阔广场,也是为我一个人而建立。烟草店的帮手莽入 ·个普普通通的墓穴,不就是在今天吗?今天的太阳,不是为他而升起的。然而,不管我自 己如何不愿意,我也不得不突然想到:太阳同样不是为我升起的。 思想比生存更好 这座明亮城市中烟烟囚光的海关对面,是连绵不断的一排排房子,空旷的场地,道路和 高楼群芳断若续的轮廓。从一大早开始,这一切就被裹在一片淡淡的雾中。太阳慢慢地变成 金色。早晨过后,微风轻拂,柔软的雾罩才开始散开,如同轻纱被丝丝缕缕地挑去,直到 后消逝。一到了上午十急功流放迈吹吹雾,仅仅在蓝天里残留下 一片踌躇不定的游云。 雾纱旁落的时候,城市里的活物便重新诞生了。已经破晓的白天,像一扇突然打开的窗 子,再一次迎来了破晓。街头的各种声响纷杂有别,如同刚刚涌现。一种青色悄悄弥漫,甚 至潜入了鹅卵石以及行人们混杂的气味中。骄阳似火,但散发出一种潮润的热,似乎己经被
我猜测,没有人会真正接纳他人的存在。一个人可以承认,其他人也是生类,也能够像 他一详奋书球皤激着但是总有动点不订的因首饰巴;总有一点可以感觉得到但又没法明确指 出的差别吧。时光流逝,一些猪奇志怪的书籍,留下了一些人物,似乎比同类骨肉所制作出 来的人更使我们感到真实。这些用同类骨肉制作出来的人正在酒吧里隔着柜台对我们说话, 或者在电车里弓俄们注目,或者在大街上萍水相逢地擦肩而过。对于我们来说,这些他人只 不过是景观的一部分,通常是熟悉大街上隐匿莫见的景观。 也许,我更为感到紧密相联和息息相关的人,是我从书本里读来的,是我在雕刻作品中 看到的,而不是现实中的人,不是“血肉之躯”这种形而上意义上的荒诞所指。就实而论, 用“血肉之躯”来描述他们其实不错:他们像屠夫石头案板上的肉堆,虽然还像活物一样流 着血,却已经是死去的造物,是命运的肉排和肉片。 我知道,所有人都是这样感觉的,所以我不会为这种感觉方式羞愧。人际之间尊重的缺 乏,还有冷漠,使他们互相残杀而无须内疚(如凶手所为),无须对残杀有所思考(如战士 所为)。这一切都源于这样一件事实,人们从来没有关注过这样一个明明白白的深奥道理: 其他人也有灵魂。 在某些日子,在某些时刻,莫名的感觉之风 l 向我袭来,神秘之门向我洞开,我突然意 识到墙角落里的杂货商是一个精神的生命,在门口弯腰跨过一袋土豆的他那个帮手,是一颗 确凿无疑能够受到伤害的灵魂。 昨天,他们告诉我,烟草店的帮手自杀了。我简直不能相信。可怜的小伙子,这么说他 也是存在过的!我们,我们所有的人已经忘记了这一点。我们对他的了解,同那些完全不了 解他的人的了解相差无几。我们明天会更加容易地忘记他。但确定无疑的一点,是他有一颗 灵魂,一颗足以结束自己生命的灵魂。激情?忧伤?当然如此。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对于 所有还活着的人类来说,他留下的一切,是人们记忆中他傻乎乎的微笑,还有下面一件不合 身的脏兮兮的毛皮茄克。这就是一个人给我留下的一切,而这个人内心如此之深以致足以结 束自己,毕竟没有其他理由足以使一个人这样做.我回想到有一次,我从他那里买烟,发 现他可能要过早地秃顶。事到如今,他根本还来不及秃顶。然而。这就是我好他的记忆。 如果我好记忆十非事实而是我的玄想,那么他可曾给我留下其他什么样的记忆? 我有一种突如其来的幻象:他的尸体,装着他的棺木,人们最终将把他送达的那个生冷 洞穴。我的目光完全剥除他那件茄克,于是我看见那位探身的烟草店帮手代表着所有人类。 幻象仅仅只是一瞬间。今天,当然啦,身为凡胎,我只能想到他死了。如此而已。 不,他人并不存在.太阳扬起沉重的光翼,泛出刺目而斑斓的色彩,只是为了我一个 人而升起。太阳下面光波闪闪的江流,尽管在我的视野之外,也只是为了我一个人而涌动。 让人们得以放目江河及其滚滚波涛的空阔广场,也是为我一个人而建立。烟草店的帮手葬入 一个普普通通的墓穴,不就是在今天吗?今天的太阳,不是为他而升起的。然而,不管我自 己如何不愿意,我也不得不突然想到:太阳同样不是为我升起的. 思想比生存更好 这座明亮城市中烟烟囚光的海关对面,是连绵不断的一排排房子,空旷的场地,道路和 高楼群芳断若续的轮廓。从一大早开始,这一切就被裹在一片淡淡的雾中。太阳慢慢地变成 金色。早晨过后,微风轻拂,柔软的雾罩才开始散开,如同轻纱被丝丝缕缕地挑去,直到最 后消逝。一到了上午十急功流放迈吹吹雾,仅仅在蓝天里残留下一片踌躇不定的游云。 雾纱旁落的时候,城市里的活物便重新诞生了。已经破晓的白天,像一扇突然打开的窗 子,再一次迎来了破晓。街头的各种声响纷杂有别,如同刚刚涌现。一种青色悄悄弥漫,甚 至潜入了鹅卵石以及行人们混杂的气味中。骄阳似火,但散发出一种潮润的热,似乎已经被

刚才消散了的大雾所浸透。 我总是发现,无论零大雾小,一个城市的苏醒比乡村里的日出市今人成动。一种重新再 生的品列成微 ,越往下看就会越强烈。与田野渐人亮色的情形不同,这太阳 树的背影 有树叶展开过程中最初的暗色,接下来光的流移, 直到最后的金光闪耀, 切动人的变传 叠印在窗子里,投照在墙壁和房顶上.在乡村里观看破晓,总给我好的感觉,而在城市里 观看破晓,对于我来说既好也不好,因此使我感到更好。如同所有的希望,一种更大的希望 给我带来谣不可及的非现的杯乡余味。乡村甲的破晓只不时是存在的事实,而城市中的破 晓则充满着许诺。前者使你生存 后者则使你思想。我总是相信,思想比生存更好。这是我 的不幸,与其他所有的大不幸随 我已经身分两处 今天,我们称之为办公室小伙计的那个人走了.人们说。他返回农和。再也不会来了 今天,这个被我视为人类群体中 ·部分的人,进而成为我和我 个世界的 一部分的人,走了 那天在走道上偶然相遇,我没法不对我们的分手吃惊。他不无羞怯地与我拥抱。我的心不由 自主地发酸,限匡不由自主地发热,靠着足够的自制力,才没有哭出来。 所有一切都是我们的,这纯粹是因为:它们曾经一度是我们的,与我们偶然地生活在 起,或者在日常牛活中兽经具光很接,便成为了我们的一部分。今天,不是一个办公室的小 伙子,而是一个生命体 个活生生的人类,我生命物质中千真万确的一部分,离开了我们 去了G省某个我们不知道的地方。今天,我已经身分两处,再也不可能复原。今天,办公 室的小伙子走了。 所右发生在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里的一切,也发生于我们的内心。所有消亡于我们所环不 视的世界里的一切,也消亡于我们的内心。假定我们能够留意,一切事物便得以存在于那里, 它们一旦失去便是从我们心头撕走。今天,办公室的小伙子走了。 当我坐入高高的椅子 重新回到昨天的帐本,我感到沉重,衰老 ,还有意志的虚弱。但 是,今天以拥础断言购悲剧故给我汉尼一种.我,必须奋力压抑的沉思,已经打断了整理帐 目的机械性程式。如果我还得用心工作,我只有靠一种惯性的动作,把自己强制性地拉回来 就范。今天,办公室小伙子走了。 是的,明天或者以后的哪一天,生离死别的钟声在幽静中响起,不再在这里的人将是我, 本陈旧的抄本被整理好以后束之高阁。是的,明天,或者以后的哪 大,命运判决的时候 我也许搞要死党我也会返调微乡的小村分供天知道我将归宿何处。今天,仅仅因为离别还能 引起人的感触,一种缺席者的悲副才变得历历在目真切可触。 呵,办公室的小伙子今天走了。 心灵是生活之累 些感觉像梦,成为弥漫到人们精神任何一个角落的迷雾,让人不能思想,不能行动 甚至怎么样都不是。我们梦幻的一些迹象存留于心,就像我们没有正式睡觉,一种白日的余 温还停留在感觉的迟纯表层。当一个人的意志成为院子里一桶水,而且被笨手笨脚的路人 脚踢翻的时候,这真是一无所有的陶醉之时。 人们送出目光但并无所见。长长的街道挤满人类这种造物,像 瓶倾倒的墨水,污染的 信件上乱糟糟一团,无可辨识。房子仅仅是房子,不论人们看得怎样清清楚楚,也不可能从 这种观察中获得什么意义。 皮箱匠小店里传来的一阵阵的锤击声,给人一种熟悉的陌生之感。每一击在时间里相隔
刚才消散了的大雾所浸透。 我总是发现,无论雾大雾小,一个城市的苏醒比乡村里的日出更令人感动。一种重新再 生的强烈感觉,越往下看就会越强烈。与田野渐人亮色的情形不同,这太阳,树的背影,还 有树叶展开过程中最初的暗色,接下来光的流移,一直到最后的金光闪耀,一切动人的变化 叠印在窗子里,投照在墙壁和房顶上.在乡村里观看破晓,总给我好的感觉,而在城市里 观看破晓,对于我来说既好也不好,因此使我感到更好。如同所有的希望,一种更大的希望 给我带来遥不可及的非现实的怀乡余味。乡村里的破晓只不过是存在的事实,而城市中的破 晓则充满着许诺。前者使你生存,后者则使你思想。我总是相信,思想比生存更好。这是我 的不幸,与其他所有的大不幸随行。 我已经身分两处 今天,我们称之为办公室小伙计的那个人走了.人们说。他返回农和。再也不会来了_ 今天,这个被我视为人类群体中一部分的人,进而成为我和我整个世界的一部分的人,走了。 那天在走道上偶然相遇,我没法不对我们的分手吃惊。他不无羞怯地与我拥抱。我的心不由 自主地发酸,眼眶不由自主地发热,靠着足够的自制力,才没有哭出来。 所有一切都是我们的,这纯粹是因为:它们曾经一度是我们的,与我们偶然地生活在一 起,或者在日常生活中兽经县光很接,便成为了我们的一部分。今天,不是一个办公室的小 伙子,而是一个生命体,一个活生生的人类,我生命物质中千真万确的一部分,离开了我们, 去了 G 省某个我们不知道的地方。今天,我已经身分两处,再也不可能复原。今天,办公 室的小伙子走了。 所有发生在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里的一切,也发生于我们的内心。所有消亡于我们所环 视的世界里的一切,也消亡于我们的内心。假定我们能够留意,一切事物便得以存在于那里, 它们一旦失去便是从我们心头撕走。今天,办公室的小伙子走了。 当我坐入高高的椅子,重新回到昨天的帐本,我感到沉重,衰老,还有意志的虚弱。但 是,今天以拥础断言购悲剧故给我汉尼一种.我.必须奋力压抑的沉思,已经打断了整理帐 目的机械性程式。如果我还得用心工作,我只有靠一种惯性的动作,把自己强制性地拉回来 就范。今天,办公室小伙子走了。 是的,明天或者以后的哪一天,生离死别的钟声在幽静中响起,不再在这里的人将是我, 一本陈旧的抄本被整理好以后束之高阁。是的,明天,或者以后的哪一大,命运判决的时候, 我也许搞要死党我也会返调徽乡的小村分供天知道我将归宿何处。今天,仅仅因为离别还能 引起人的感触,一种缺席者的悲剧才变得历历在目真切可触。 呵,办公室的小伙子今天走了。 心灵是生活之累 一些感觉像梦,成为弥漫到人们精神任何一个角落的迷雾,让人不能思想,不能行动, 甚至怎么样都不是。我们梦幻的一些迹象存留于心,就像我们没有正式睡觉,一种白日的余 温还停留在感觉的迟钝表层。当一个人的意志成为院子里一桶水,而且被笨手笨脚的路人一 脚踢翻的时候,这真是一无所有的陶醉之时。 人们送出目光但并无所见。长长的街道挤满人类这种造物,像一瓶倾倒的墨水,污染的 信件上乱糟糟一团,无可辨识。房子仅仅是房子,不论人们看得怎样清清楚楚,也不可能从 这种观察中获得什么意义。 皮箱匠小店里传来的一阵阵的锤击声,给人一种熟悉的陌生之感。每一击在时间里相隔

每一击都尾随着回声,每一击也都完全空洞。雷声惊魂之时过路的马车照例发出它们惯有的 轰响。人声浮现,不是来自人们的喉头,而是来自空气本身。作为这一切的背景,甚至河水 也疲惫不增 这不是人们感受到的单调。这一切也不是痛苦。这是在另一种不同的个性装束之下昏昏 入睡的欲望,是对增薪以后乏味之感的忘却。你对任何东西也没有感觉,除了你的双腿在不 由自主向前行走时机械地起落,使你意识到自己的脚上穿着鞋子。也许连这一点你也感觉甚 少,因为有些东西密封了你的大脑,遮去了你的双眼,堵住了你的耳朵, 这就像心灵 一次感 ”这 中疾病的文学意象来向往生活,如同身处病床上一个长长 的康复阶段:而康复的意念激发出城郊地带一些大房子的意象,在房子的深处,在靠近壁妍 的地方,你远离街市和交通。不,你什么也听不到。你意识到你经过了一张你必须进人的门, 走过它的时候你好像已经睡着,已不能使自己的身体移向别的任何方向。你途经了一切地方。 你这只沉睡的能,你的铃技现在何处? 种初始的微弱,成腥难闻的海水气味被微风带来,在塔格斯河边盘旋 在贝克萨区 的周边沤积和混杂。 它冷冷地吹着,显示出温暖大海的麻术 在这里,生活成为了我肯里堵塞着的东西,而我的嗅觉藏在眼睛以后的什么地方。在更 高处,完全是辆附于虚空之上,一抹薄藏的浮云从乌云中流出,最终种解在虚幻的白云之中 高空如同怯怯天国中的一座刷场,滚动者听不见的惊雷,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 甚至飞翔着的海似乎也是静静的,比空气本身还要轻盈,好像什么人把它们悬置在那 里。 而黄昏并无沉 重 之 它临阵 我们的不安之中:空气渐渐地冷起来 我可怜的希望,我一直被迫度过着的生活正在诞生!它们就像此时的空气,像消散的务 气,不适当地试图搅起一场虚构的风暴。我想要呐喊,给这样的景观和这样的思虑划上句号。 但是海水的咸涩注入我所有的良好愿望,在远远的低处,只有我的嗅觉能辨出的潮水 混浊而幽暗地在我胸中涌动。 这真 是 通只能满足自己的胡说八道!可笑的洞察居然进入纯属虚假的感情!所有这些 心灵和感觉的混杂,还有思考与空气和河流的混杂,只是说明生活伤害了我的嗅觉和意识 只说明我还没有才智来运用工作手册上简单而又放之四海皆准的话:心灵是生活之累。 夜晚 呵,夜晚,星星在夜色里装点光明。呵,夜晚,大得等同字宙的浩阔天际,造就着我的 肉体和心灵- 一同样是河体的二部分>让我在黑暗中失落自己,使我也拥有夜晚,不再有星 星般的梦幻,不再有对未来太阳之光的向往。生活是伟大的失眠任何人若希望制造一个鬼怪 的概念,只需要在欲眠却又不能入眠的心灵那里,用语言来给事物造馆以这些事物具有梦境 的一切支离破碎,却不会是人睡的非正式人口。它们如编幅盘旋于无力的心灵之上,或者像 吸血鬼吸吮着我们驯从的血液。 它们是衰退和耗竭的幼体,是填注峡谷的暗影,是命运最后的残痕。有时候它们是虫卵 被灵魂宠护和滋养却与灵魂格格不入:有时候它们是鬼除,阴气森森地无事相扰却又挥之不 去:有时候它们则像眼镜蛇,从旧日情感的古怪洞穴里浮现出来\它们使谬误定若磐石,仅 有的目的是使我们变得一无所用。它们是来自内心深处的疑惑,冷冷地据守在那里,在睡眼 中关闭灵魂。它们像烟云一样短命, 又如地上的车撤,所有能留F的东西,是曾经在我们 相关感觉的贫瘠泥土中存在过的事实。它们当中,有一些像是思想的火花,在两个梦境之间 闪亮过一瞬,剩下的一些则不过是我们得以看见的意识的无意识。 像一支没有完成的琴弓,灵魂从来不能存在于它的自身。伟大的景观统统属于我们已经 亲历过的一个明天。而水不间断的交谈己经是一个失敷。谁曾猜出生活就像这个样子?
每一击都尾随着回声,每一击也都完全空洞。雷声惊魂之时过路的马车照例发出它们惯有的 轰响。人声浮现,不是来自人们的喉头,而是来自空气本身。作为这一切的背景,甚至河水 也疲惫不堪。 这不是人们感受到的单调。这一切也不是痛苦。这是在另一种不同的个性装束之下昏昏 入睡的欲望,是对增薪以后乏味之感的忘却。你对任何东西也没有感觉,除了你的双腿在不 由自主向前行走时机械地起落,使你意识到自己的脚上穿着鞋子。也许连这一点你也感觉甚 少,因为有些东西密封了你的大脑,遮去了你的双眼,堵住了你的耳朵。 这就像心灵的一次感冒。以这种疾病的文学意象来向往生活,如同身处病床上一个长长 的康复阶段;而康复的意念激发出城郊地带一些大房子的意象,在房子的深处,在靠近壁炉 的地方,你远离街市和交通。不,你什么也听不到。你意识到你经过了一张你必须进人的门, 走过它的时候你好像已经睡着,已不能使自己的身体移向别的任何方向。你途经了一切地方。 你这只沉睡的熊,你的铃鼓现在何处? 以一种初始的微弱,咸腥难闻的海水气味被微风带来,在塔格斯河边盘旋,在贝克萨区 的周边沤积和混杂。它冷冷地吹着,显示出温暖大海的麻木。 在这里,生活成为了我胃里堵塞着的东西,而我的嗅觉藏在眼睛以后的什么地方。在更 高处,完全是牺附于虚空之上,一抹薄薄的浮云从乌云中流出,最终融解在虚幻的白云之中。 高空如同怯怯天国中的一座剧场,滚动着听不见的惊雷,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 甚至飞翔着的海鸥似乎也是静静的,比空气本身还要轻盈,好像什么人把它们悬置在那 里。而黄昏并无沉重之感,它临阵于我们的不安之中;空气渐渐地冷起来。 我可怜的希望,我一直被迫度过着的生活正在诞生!它们就像此时的空气,像消散的雾 气,不适当地试图搅起一场虚构的风暴。我想要呐喊,给这样的景观和这样的思虑划上句号。 但是海水的咸涩注入我所有的良好愿望,在远远的低处,只有我的嗅觉能辨出的潮水, 混浊而幽暗地在我胸中涌动。 这真是一通只能满足自己的胡说八道!可笑的洞察居然进入纯属虚假的感情!所有这些 心灵和感觉的混杂,还有思考与空气和河流的混杂,只是说明生活伤害了我的嗅觉和意识, 只说明我还没有才智来运用工作手册上简单而又放之四海皆准的话:心灵是生活之累。 夜晚 呵,夜晚,星星在夜色里装点光明。呵,夜晚,大得等同宇宙的浩阔天际,造就着我的 肉体和心灵——同样是河体的二部分>让我在黑暗中失落自己,使我也拥有夜晚,不再有星 星般的梦幻,不再有对未来太阳之光的向往。生活是伟大的失眠任何人若希望制造一个鬼怪 的概念,只需要在欲眠却又不能入眠的心灵那里,用语言来给事物造馆以这些事物具有梦境 的一切支离破碎,却不会是人睡的非正式人口。它们如编幅盘旋于无力的心灵之上,或者像 吸血鬼吸吮着我们驯从的血液。 它们是衰退和耗竭的幼体,是填注峡谷的暗影,是命运最后的残痕。有时候它们是虫卵, 被灵魂宠护和滋养却与灵魂格格不入;有时候它们是鬼除,阴气森森地无事相扰却又挥之不 去;有时候它们则像眼镜蛇,从旧日情感的古怪洞穴里浮现出来\它们使谬误定若磐石,仅 有的目的是使我们变得一无所用。它们是来自内心深处的疑惑,冷冷地据守在那里,在睡眠 中关闭灵魂。它们像烟云一样短命,又如地上的车撤,所有能留 F 的东西,是曾经在我们 相关感觉的贫瘠泥土中存在过的事实。它们当中,有一些像是思想的火花,在两个梦境之间 闪亮过一瞬,剩下的一些则不过是我们得以看见的意识的无意识。 像一支没有完成的琴弓,灵魂从来不能存在于它的自身。伟大的景观统统属于我们已经 亲历过的一个明天。而永不间断的交谈已经是一个失败。谁曾猜出生活就像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