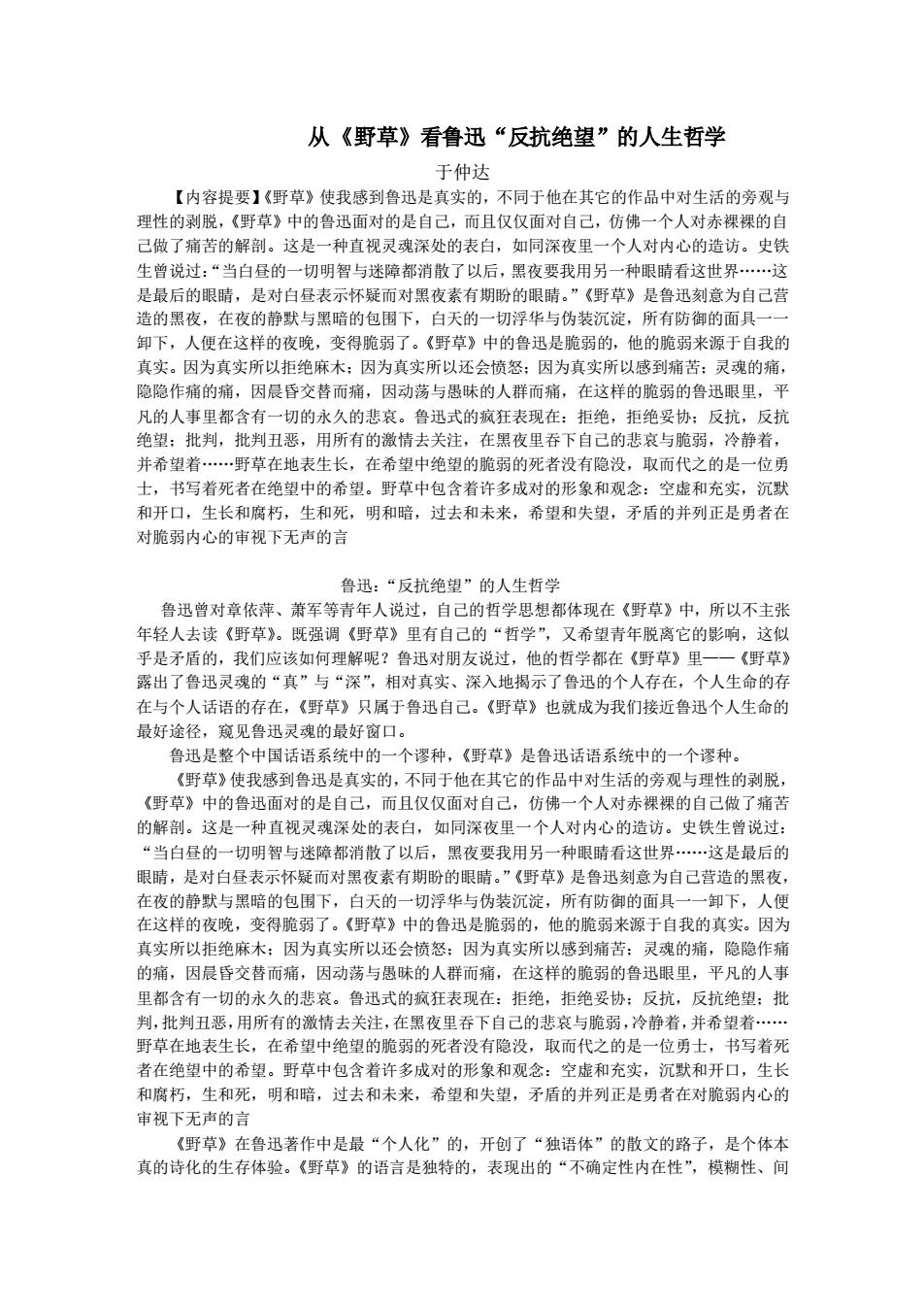
从《野草》看鲁迅“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 【内容提要】《野草》使我感到鲁迅是真实的,不同于他在其它的作品中对生活的旁观与 理性的剥脱,《野草》中的鲁迅面对的是自己,而且仅仅面对自己,仿佛一个人对赤裸裸的自 己做了痛苦的解剖。这是一种直视灵魂深处的表白,如同深夜里一个人对内心的造访。史铁 生曾说讨,“当白昼的一切明智与迷随都消散了以后,里夜要我用另一种眼睹看这世界议 总后的明睛 是对白昼表示怀疑而对黑夜素有期盼的眼睛。 ”《野草》是鲁迅刻意为自己营 造的黑夜 在夜的静 可黑暗的包围下,白天的一切浮华与伪装沉淀, 所有防的面 卸下,人便在这样的夜晚,变得脆弱了。《野草》中的鲁迅是脆弱的,他的脆弱来源于自我的 真实。因为真实所以拒绝麻木:因为真实所以还会愤怒:因为真实所以感到痛苦:灵魂的痛, 隐隐作痛的痛,因晨昏交替而痛,因动荡与愚味的人群而痛,在这样的脆弱的鲁迅眼里,平 凡的人事里都含有一切的永久的悲哀。鲁迅式的疯狂表现在:拒绝,拒绝妥协:反抗,反抗 绝望:批判,批判丑恶 用所有的激情去关注 在黑夜里吞下自己的 哀与脆 静者 并希望着· ,野草在地表生长,在希望中绝望的脆弱的死者没有隐没,取而代之的是一位勇 士,书写着死者在绝望中的希望。野草中包含着许多成对的形象和观念:空虚和充实,沉默 和开口,生长和腐朽,生和死,明和暗,过去和未来,希望和失望,矛盾的并列正是勇者在 对脆弱内心的审视下无声的言 鲁迅:“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 鲁迅曾对章依萍、萧军等青年人说过,自己的哲学思想都体现在《野草》中,所以不主张 年轻人去读《野草》。既强调《野草》里有自己的“哲学”,又希望青年脱离它的影响,这似 乎是矛话的,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呢?鲁讯对朋友说过,他的哲学都在《野草》甲 一《野草。 霞出了色讯灵魂的“直”与“深”,相对直实、深入地揭示了色讯的个人存在,个人生命的存 在与个人话语的存在, 《野草》只属于鲁迅自己。《野草》也就成为我们接近鲁迅个人生命的 最好途径,窥见鲁迅灵魂的最好窗口。 鲁迅是整个中国话语系统中的一个谬种,《野草》是鲁迅话语系统中的一个琴种 《野草》使我感到鲁迅是真实的,不同于他在其它的作品中对生活的旁观与理性的剥脱, 《野草》中的鲁迅面对的是自己,而且仅仅面对自己,仿佛一个人对赤裸裸的自己做了痛苦 的解剖。这是一种直祝灵魂深处的表白 如同深夜里 人对内心的造访。史铁生曾说过 “当白昼的一切明智与迷障都消散了以后,黑夜要我用另一种眼睛看这世界. .这是最后的 眼睛,是对白昼表示怀疑而对黑夜素有期盼的眼睛。”《野草》是鲁迅刻意为自己营造的黑夜 在夜的静默与黑暗的包围下,白天的一切浮华与伪装沉淀,所有防御的面只一一卸下,人便 在这样的夜晚,变得脆弱了。《野草》中的鲁迅是脆弱的,他的脆弱来源于自我的真实。因为 真实所以拒绝麻木。 因为真实所以还会愤怒:因为真实所以感到痛苦:灵魂的痛 隐隐作 的痛,因晨昏交替而痛,因动荡与愚味的人群而痛,在这样的脆弱的鲁迅眼里, 平凡的人 里都含有一切的永久的悲哀。鲁迅式的疯狂表现在:拒绝,拒绝妥协:反抗,反抗绝望:批 判,批判丑恶,用所有的激情去关注,在黑夜里吞下自己的悲哀与脆弱,冷静着,并希望者· 野草在地表生长,在希望中绝望的脆弱的死者没有隐没,取而代之的是一位勇士,书写若死 者在绝望中的希望。野草中包含若许多成对的形象和观念:空虚和充实,沉默和开口,生长 和腐朽,生和死 明和暗,过去和未来,希望和失望, 矛盾的并列正是勇者在对脆弱内心的 审视下无声的言 《野草》在鲁迅著作中是最“个人化”的,开创了“独语体”的散文的路子,是个体本 真的诗化的生存体验。《野草》的语言是独特的,表现出的“不确定性内在性”,模糊性、间
从《野草》看鲁迅“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 于仲达 【内容提要】《野草》使我感到鲁迅是真实的,不同于他在其它的作品中对生活的旁观与 理性的剥脱,《野草》中的鲁迅面对的是自己,而且仅仅面对自己,仿佛一个人对赤裸裸的自 己做了痛苦的解剖。这是一种直视灵魂深处的表白,如同深夜里一个人对内心的造访。史铁 生曾说过:“当白昼的一切明智与迷障都消散了以后,黑夜要我用另一种眼睛看这世界.这 是最后的眼睛,是对白昼表示怀疑而对黑夜素有期盼的眼睛。”《野草》是鲁迅刻意为自己营 造的黑夜,在夜的静默与黑暗的包围下,白天的一切浮华与伪装沉淀,所有防御的面具一一 卸下,人便在这样的夜晚,变得脆弱了。《野草》中的鲁迅是脆弱的,他的脆弱来源于自我的 真实。因为真实所以拒绝麻木;因为真实所以还会愤怒;因为真实所以感到痛苦;灵魂的痛, 隐隐作痛的痛,因晨昏交替而痛,因动荡与愚昧的人群而痛,在这样的脆弱的鲁迅眼里,平 凡的人事里都含有一切的永久的悲哀。鲁迅式的疯狂表现在:拒绝,拒绝妥协;反抗,反抗 绝望;批判,批判丑恶,用所有的激情去关注,在黑夜里吞下自己的悲哀与脆弱,冷静着, 并希望着.野草在地表生长,在希望中绝望的脆弱的死者没有隐没,取而代之的是一位勇 士,书写着死者在绝望中的希望。野草中包含着许多成对的形象和观念:空虚和充实,沉默 和开口,生长和腐朽,生和死,明和暗,过去和未来,希望和失望,矛盾的并列正是勇者在 对脆弱内心的审视下无声的言 鲁迅:“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 鲁迅曾对章依萍、萧军等青年人说过,自己的哲学思想都体现在《野草》中,所以不主张 年轻人去读《野草》。既强调《野草》里有自己的“哲学”,又希望青年脱离它的影响,这似 乎是矛盾的,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呢?鲁迅对朋友说过,他的哲学都在《野草》里——《野草》 露出了鲁迅灵魂的“真”与“深”,相对真实、深入地揭示了鲁迅的个人存在,个人生命的存 在与个人话语的存在,《野草》只属于鲁迅自己。《野草》也就成为我们接近鲁迅个人生命的 最好途径,窥见鲁迅灵魂的最好窗口。 鲁迅是整个中国话语系统中的一个谬种,《野草》是鲁迅话语系统中的一个谬种。 《野草》使我感到鲁迅是真实的,不同于他在其它的作品中对生活的旁观与理性的剥脱, 《野草》中的鲁迅面对的是自己,而且仅仅面对自己,仿佛一个人对赤裸裸的自己做了痛苦 的解剖。这是一种直视灵魂深处的表白,如同深夜里一个人对内心的造访。史铁生曾说过: “当白昼的一切明智与迷障都消散了以后,黑夜要我用另一种眼睛看这世界.这是最后的 眼睛,是对白昼表示怀疑而对黑夜素有期盼的眼睛。”《野草》是鲁迅刻意为自己营造的黑夜, 在夜的静默与黑暗的包围下,白天的一切浮华与伪装沉淀,所有防御的面具一一卸下,人便 在这样的夜晚,变得脆弱了。《野草》中的鲁迅是脆弱的,他的脆弱来源于自我的真实。因为 真实所以拒绝麻木;因为真实所以还会愤怒;因为真实所以感到痛苦;灵魂的痛,隐隐作痛 的痛,因晨昏交替而痛,因动荡与愚昧的人群而痛,在这样的脆弱的鲁迅眼里,平凡的人事 里都含有一切的永久的悲哀。鲁迅式的疯狂表现在:拒绝,拒绝妥协;反抗,反抗绝望;批 判,批判丑恶,用所有的激情去关注,在黑夜里吞下自己的悲哀与脆弱,冷静着,并希望着. 野草在地表生长,在希望中绝望的脆弱的死者没有隐没,取而代之的是一位勇士,书写着死 者在绝望中的希望。野草中包含着许多成对的形象和观念:空虚和充实,沉默和开口,生长 和腐朽,生和死,明和暗,过去和未来,希望和失望,矛盾的并列正是勇者在对脆弱内心的 审视下无声的言 《野草》在鲁迅著作中是最“个人化”的,开创了“独语体”的散文的路子,是个体本 真的诗化的生存体验。《野草》的语言是独特的,表现出的“不确定性内在性”,模糊性、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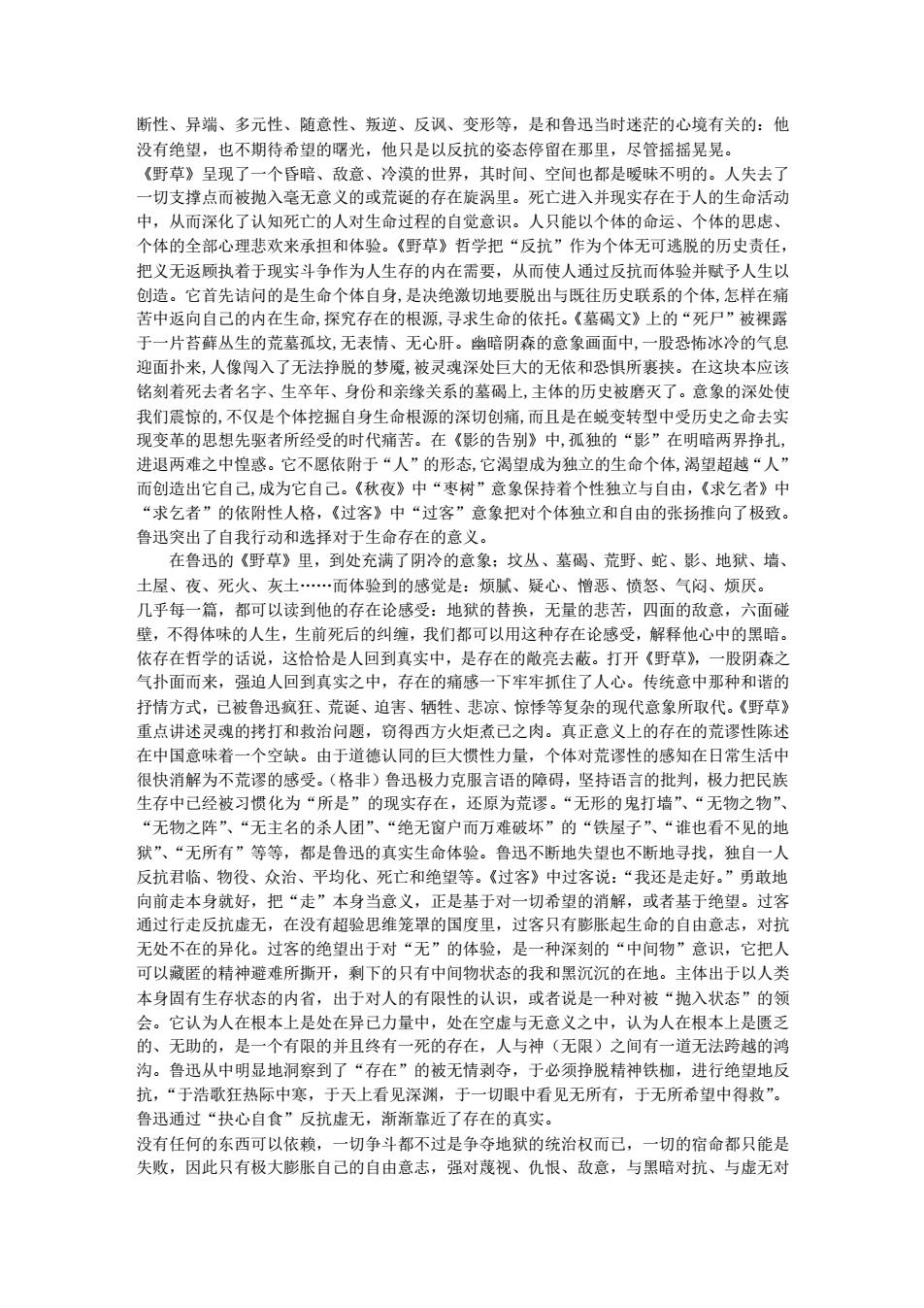
断性、异端、多元性、随意性、叛逆、反讽、变形等,是和鲁迅当时迷茫的心境有关的:他 没有绝望,也不期待希望的曙光,他只是以反抗的姿态停留在那里,尽管摇摇晃晃 《哥草》呈现了 个暗 敌意、冷漠的世界,其时间、空间也都是暖味不明的 人失去了 一切支撑点而被抛入毫无意义的或荒诞的存在旋涡里。死亡进入并现实存在于人的生命活动 中,从而深化了认知死亡的人对生命过程的自觉意识。人只能以个体的命运、个体的思虑、 个体的全部心理悲欢来承担和体验。《野草》哲学把“反抗”作为个体无可逃脱的历史责任, 把义无返顾执于现实斗争作为人生存的内在需要,从而使人通过反抗而体验并赋予人生以 创造 它首先 诘问的是生命个体自身,是决绝 激切 地要脱出与既往历史联系的个体,怎样在痛 苦中返向自己的内在生命,探究存在的根源,寻求生命的依托。《慕码文》上的“死厂 被裸 于一片苔裤丛生的荒墓孤坟,无表情、无心肝。幽暗阴森的意象画面中,一股恐怖冰冷的气息 迎面扑来,人像闯入了无法挣脱的梦魇,被灵魂深处巨大的无依和恐惧所裹挟。在这块本应该 铭刻着死去者名字、生卒年、身份和亲缘关系的莫碣上,主体的历史被磨灭了。意象的深处使 我们震惊的,不仅是个体挖掘自身生命根源的深切创痛,而且是在蜕变转型中受历史之命去实 现变革的思想先驱者所经受的时代痛苦。在《影的告别》中,孤独的“影”在明暗两界挣力 进退两难之中惶惑。它不愿依附于“人”的形态,它渴望成为独立的生命个体,渴望超越“人 而创造出它自己,成为它自己。《秋夜》中“枣树”意象保持着个性独立与自由,《求乞者》中 “求乞者”的依附性人格,《过客》中“过客”意象把对个体独立和自由的张扬推向了极致」 鲁迅突出了自我行动和选择对于生命存在的意义 在鲁迅的《野草》里,到处充满 阴冷的意象:坟丛、墓、荒野、蛇、影、地狱、墙 土屋、夜、死火、灰士.而体验到的感觉是:烦腻、疑心、憎恶、愤怒、气闷、烦厌。 几乎每一篇,都可以读到他的存在论感受:地狱的替换,无量的悲苦,四面的敌意,六面碰 壁,不得体味的人生,生前死后的纠蕴,我们都可以用这种存在论感受,解释他心中的黑暗。 依存在哲学的话说,这恰恰是人回到直实中,是存在的亮去被。打开《草》,一股阴森 气扑面而来,强迫人回到真实之中 存在的痛感 人心 传统意中那种和诺白 抒情方式,已被鲁迅疯狂、荒诞、迫害、牺牲、悲凉、惊悸等复杂的现代意象所取代。《野草》 重点讲述灵魂的拷打和救治问题,窃得西方火炬煮已之肉。真正意义上的存在的荒谬性陈述 在中国意味者一个空缺。由于道德认同的巨大惯性力量,个体对荒谬性的感知在日常生活中 很快消解为不荒溪的成受。(格非)鲁讯极力克服言语的赔碍。坚持语言的批判,极力把民湖 生存中已经被习惯化为“所是”的现实存在 环原为荒零。“无形的 鬼打培”、“无物之物” “无物之阵 无主名的杀人团 “绝无 户而万难破坏”的“铁屋子”、 “谁也看不见的地 狱”、“无所有”等等,都是鲁迅的真实生命体验。鲁迅不断地失望也不断地寻找,独自一人 反抗君临、物役、众治、平均化、死亡和绝望等。《过客》中过客说:“我还是走好。”勇敢地 向前走本身就好,把“走”本身当意义,正是基于对一切希望的消解,或者基于绝望。过容 通过行走反抗虚无,在没有超验思维笼罩的国度里,过客只有膨胀起生命的自由意志,对抗 无处不在的异化。过客 的绝望出于对“无”的体验 种深刻的“中间物 意识 它抑 可以藏匿的精神避难所撕开,剩下的只有中间物状态的我和黑沉沉的在地。主体出于以人类 本身固有生存状态的内省,出于对人的有限性的认识,或者说是一种对被“抛入状态”的领 会。它认为人在根本上是处在异已力量中,处在空虚与无意义之中,认为人在根本上是匮习 的、无助的,是一个有限的并且终有一死的存在,人与神(无限)之间有一道无法跨越的鸿 沟。鲁迅从中明显地洞察到了“存在”的被无情剥夺。 于必须挣脱精神铁枷,进行绝望地 “于浩歌狂热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 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鲁迅通过“抉心自食”反抗虚无,渐渐靠近了存在的真实。 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依赖,一切争斗都不过是争夺地狱的统治权而己,一切的宿命都只能是 失败,因此只有极大膨胀自己的自由意志,强对蔑视、仇恨、敌意,与黑暗对抗、与虚无对
断性、异端、多元性、随意性、叛逆、反讽、变形等,是和鲁迅当时迷茫的心境有关的:他 没有绝望,也不期待希望的曙光,他只是以反抗的姿态停留在那里,尽管摇摇晃晃。 《野草》呈现了一个昏暗、敌意、冷漠的世界,其时间、空间也都是暧昧不明的。人失去了 一切支撑点而被抛入毫无意义的或荒诞的存在旋涡里。死亡进入并现实存在于人的生命活动 中,从而深化了认知死亡的人对生命过程的自觉意识。人只能以个体的命运、个体的思虑、 个体的全部心理悲欢来承担和体验。《野草》哲学把“反抗”作为个体无可逃脱的历史责任, 把义无返顾执着于现实斗争作为人生存的内在需要,从而使人通过反抗而体验并赋予人生以 创造。它首先诘问的是生命个体自身,是决绝激切地要脱出与既往历史联系的个体,怎样在痛 苦中返向自己的内在生命,探究存在的根源,寻求生命的依托。《墓碣文》上的“死尸”被裸露 于一片苔藓丛生的荒墓孤坟,无表情、无心肝。幽暗阴森的意象画面中,一股恐怖冰冷的气息 迎面扑来,人像闯入了无法挣脱的梦魇,被灵魂深处巨大的无依和恐惧所裹挟。在这块本应该 铭刻着死去者名字、生卒年、身份和亲缘关系的墓碣上,主体的历史被磨灭了。意象的深处使 我们震惊的,不仅是个体挖掘自身生命根源的深切创痛,而且是在蜕变转型中受历史之命去实 现变革的思想先驱者所经受的时代痛苦。在《影的告别》中,孤独的“影”在明暗两界挣扎, 进退两难之中惶惑。它不愿依附于“人”的形态,它渴望成为独立的生命个体,渴望超越“人” 而创造出它自己,成为它自己。《秋夜》中“枣树”意象保持着个性独立与自由,《求乞者》中 “求乞者”的依附性人格,《过客》中“过客”意象把对个体独立和自由的张扬推向了极致。 鲁迅突出了自我行动和选择对于生命存在的意义。 在鲁迅的《野草》里,到处充满了阴冷的意象;坟丛、墓碣、荒野、蛇、影、地狱、墙、 土屋、夜、死火、灰土.而体验到的感觉是:烦腻、疑心、憎恶、愤怒、气闷、烦厌。 几乎每一篇,都可以读到他的存在论感受:地狱的替换,无量的悲苦,四面的敌意,六面碰 壁,不得体味的人生,生前死后的纠缠,我们都可以用这种存在论感受,解释他心中的黑暗。 依存在哲学的话说,这恰恰是人回到真实中,是存在的敞亮去蔽。打开《野草》,一股阴森之 气扑面而来,强迫人回到真实之中,存在的痛感一下牢牢抓住了人心。传统意中那种和谐的 抒情方式,已被鲁迅疯狂、荒诞、迫害、牺牲、悲凉、惊悸等复杂的现代意象所取代。《野草》 重点讲述灵魂的拷打和救治问题,窃得西方火炬煮已之肉。真正意义上的存在的荒谬性陈述 在中国意味着一个空缺。由于道德认同的巨大惯性力量,个体对荒谬性的感知在日常生活中 很快消解为不荒谬的感受。(格非)鲁迅极力克服言语的障碍,坚持语言的批判,极力把民族 生存中已经被习惯化为“所是”的现实存在,还原为荒谬。“无形的鬼打墙”、“无物之物”、 “无物之阵”、“无主名的杀人团”、“绝无窗户而万难破坏”的“铁屋子”、“谁也看不见的地 狱”、“无所有”等等,都是鲁迅的真实生命体验。鲁迅不断地失望也不断地寻找,独自一人 反抗君临、物役、众治、平均化、死亡和绝望等。《过客》中过客说:“我还是走好。”勇敢地 向前走本身就好,把“走”本身当意义,正是基于对一切希望的消解,或者基于绝望。过客 通过行走反抗虚无,在没有超验思维笼罩的国度里,过客只有膨胀起生命的自由意志,对抗 无处不在的异化。过客的绝望出于对“无”的体验,是一种深刻的“中间物”意识,它把人 可以藏匿的精神避难所撕开,剩下的只有中间物状态的我和黑沉沉的在地。主体出于以人类 本身固有生存状态的内省,出于对人的有限性的认识,或者说是一种对被“抛入状态”的领 会。它认为人在根本上是处在异已力量中,处在空虚与无意义之中,认为人在根本上是匮乏 的、无助的,是一个有限的并且终有一死的存在,人与神(无限)之间有一道无法跨越的鸿 沟。鲁迅从中明显地洞察到了“存在”的被无情剥夺,于必须挣脱精神铁枷,进行绝望地反 抗,“于浩歌狂热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鲁迅通过“抉心自食”反抗虚无,渐渐靠近了存在的真实。 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依赖,一切争斗都不过是争夺地狱的统治权而已,一切的宿命都只能是 失败,因此只有极大膨胀自己的自由意志,强对蔑视、仇恨、敌意,与黑暗对抗、与虚无对

抗,温煦、悲悯没有了,只剩下敌意、荒寒、冷漠。鲁迅说:“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 白和奥气,我懒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于是,西然不能再在传统的流戏出界中清谣,又 没有 个更高的彼岸世界值得去周守 块石 玩玩、走走、以及“对于呻吟、叹息、哭泣、哀求无须吃惊” 血、阴毒 辣、烈,都堪称在0世纪中国中独一无二,道理在此。鲁迅极力克服言语的障碍,坚持语言 的批判,极力把民族生存中己经被习惯化为“所是”的现实存在,还原为荒谬。“无形的鬼打 墙”、“无物之物”、“无物之阵”、“无主名的杀人团”、“绝无脑户而万难被坏”的“铁层子” “谁也看不见的地狱”、“无所有”等等, 都是 的真实生命 鲁迅先生在看到启蒙发展的艰难及种种社会 暗的同时 更越来越发现了自己内心的 分裂: 方面是对新世界的向往和呐城,另一方面却义无力挣脱某些阴暗意识的自我料绊。 (《鲁迅个性心理研究·引言》),而这种“阴暗意识”一部分来自上述已分析过的由孤独、失 败继而幻灭、虚无的宿命式的绝望,另部分则来自先生对自身封建传统意识的剪不新、除不 残留的深刻认识,野草》是鲁迅转向自己内心世界进行激烈搏斗的产生的精神产物, 包 含了鲁迅自辛亥革命以 ,所经 历所积 的最痛苦 哲学的思考 先生先认识到自己还没有自外于不觉悟者行列的资格,自己的内心仍旧不可避免地积存 着许多旧的意识,那病态的国民“坏根性”就不可能只弥漫于身外而不渗进自己的灵魂,自 己骨子里还是一个未能摆脱传统影响的文人。(参《刺从里的求索·刺从里的求索·知识者的 “入世”与魏连母的悲到 一答陈保平问》、《鲁迅传·第二十章》)从这些对自己所住位置的 清晰而深刻的认识中,先生否定了自己原先的地位 而伴随着对自我否定而来的 一种强列日 “负罪感”却使先生产生了极度的不安、惶惑和孤独,这促使了先生对自身的激烈甚至几过 乎残酷的自店的抨击、剖析(《彷徨》、《野草》中部分作品),但更甚的是这种对于自我的过 于苛刻的否定和剖析,却一点也没有减轻心中那负罪的阴郁感:“吃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吃人 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依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 狱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 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 明白, 难见真的人:”(《狂人日记》)先生跌入了毁灭自身、牺牲自我仍不能拯救的痛苦而 望的深渊之中:“我只觉得‘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鲁迅家书全编·致许广平 内心中的失败感、绝望感和无意义感,引先生进入了虚无的心境。这时先生心中“人道主义 和“个人无治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显然大在偏向于后者,“憎人”、“为自己玩玩” (《鲁迅家书全编·致许广平十一》)的虚无情绪紧紧地纠缠着先生的内心。自“五四”以 知识分子内心的这种矛后、虚无是普遍存在的 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己 面对这种虚无感 不少知识分子选择了追求 “十字街头的塔”式的“艺术化的个性生活”(《无词的言语·两利 个性主义.》)。先生堪称是“中围现代最苦痛的灵魂”,但在痛苦、绝望的重重包围中,先 生始终选择了一条承担痛苦、反抗虚无的道路。这一方面基于他那对国家、对民族最真诚、 无私、深沉的爱和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感,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先生是一个现实主 义者。对于痛苦,先生看出了它的不可莲免性:“我想, 苦痛是总与人生联带的”。(《鲁迅家 书全编·致许 》),先生对痛苦不逃避,而是以自己的生命独个承担了所感受到的 切,先生的痛苦是深沉的,但先生始终都竭力自己去担受而不把它传给别人:“我对人说话时 却总拣择光明些的说出,.我为自己和为别人的设想,是两样的。所以者何,就因为我的 思想太思暗,但是究竞是否真确,不得而知,所以只能在自身试验,不能邀请别人。”(《鲁迅 家书全编致许广平十一》)先生的这句话正是先生甘于承担黑暗现实的痛苦的决心的体现 鲁迅先生虽然处身于黑暗的深渊 但依旧有着 竭力看透现实的愿望”,而且又“有意 王音 将每个强烈刺激他的新现象,与他对人生的整体认识联系起米看”,现实表象和个体(过去的) 体验互相参照,加上先生对病态人心、人生阴暗面的敏感,就使先生在当时那黑暗的社会中 得到了异于常人的深刻的现实认识。基于此,先生否定了所谓的“黄金世界”,对之,先生公
抗,温煦、悲悯没有了,只剩下敌意、荒寒、冷漠。鲁迅说:“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 气和鬼气,我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于是,既然不能再在传统的游戏世界中逍遥,又 没有一个更高的彼岸世界值得去固守,鲁迅就干脆让自己变为一块石头:冷眼、铁血、阴毒、 玩玩、走走、以及“对于呻吟、叹息、哭泣、哀求无须吃惊”,鲁迅的阴、冷、黑、沉、尖、 辣、烈,都堪称在 20 世纪中国中独一无二,道理在此。鲁迅极力克服言语的障碍,坚持语言 的批判,极力把民族生存中已经被习惯化为“所是”的现实存在,还原为荒谬。“无形的鬼打 墙”、“无物之物”、“无物之阵”、“无主名的杀人团”、“绝无窗户而万难破坏”的“铁屋子”、 “谁也看不见的地狱”、“无所有”等等,都是鲁迅的真实生命体验。 鲁迅先生在看到启蒙发展的艰难及种种社会黑暗的同时,更越来越发现了自己内心的 分裂:“一方面是对新世界的向往和呐喊,另一方面却又无力挣脱某些阴暗意识的自我羁绊。” (《鲁迅个性心理研究·引言》),而这种“阴暗意识”一部分来自上述已分析过的由孤独、失 败继而幻灭、虚无的宿命式的绝望,另部分则来自先生对自身封建传统意识的剪不断、除不 尽的残留的深刻认识。《野草》是鲁迅转向自己内心世界进行激烈搏斗的产生的精神产物,包 含了鲁迅自辛亥革命以来,所经历所积蓄的最痛苦、也最冷峻的人生哲学的思考。 先生先认识到自己还没有自外于不觉悟者行列的资格,自己的内心仍旧不可避免地积存 着许多旧的意识,那病态的国民“坏根性”就不可能只弥漫于身外而不渗进自己的灵魂,自 己骨子里还是一个未能摆脱传统影响的文人。(参《刺丛里的求索·刺丛里的求索·知识者的 “入世”与魏连殳的悲剧——答陈保平问》、《鲁迅传·第二十章》)从这些对自己所住位置的 清晰而深刻的认识中,先生否定了自己原先的地位,而伴随着对自我否定而来的一种强烈的 “负罪感”却使先生产生了极度的不安、惶惑和孤独,这促使了先生对自身的激烈甚至几近 乎残酷的自虐的抨击、剖析(《彷徨》、《野草》中部分作品),但更甚的是这种对于自我的过 于苛刻的否定和剖析,却一点也没有减轻心中那负罪的阴郁感:“吃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吃人 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依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 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 明白,难见真的人!”(《狂人日记》)先生跌入了毁灭自身、牺牲自我仍不能拯救的痛苦而绝 望的深渊之中:“我只觉得‘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鲁迅家书全编·致许广平·二》) 内心中的失败感、绝望感和无意义感,引先生进入了虚无的心境。这时先生心中“人道主义” 和“个人无治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显然大在偏向于后者,“憎人”、“为自己玩玩” (《鲁迅家书全编·致许广平·十一》)的虚无情绪紧紧地纠缠着先生的内心。自“五四”以 来,知识分子内心的这种矛盾、虚无是普遍存在的,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面对这种虚无感, 不少知识分子选择了追求“十字街头的塔”式的“艺术化的个性生活”(《无词的言语·两种 个性主义.》)。先生堪称是“中国现代最苦痛的灵魂”,但在痛苦、绝望的重重包围中,先 生始终选择了一条承担痛苦、反抗虚无的道路。这一方面基于他那对国家、对民族最真诚、 无私、深沉的爱和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感,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先生是一个现实主 义者。对于痛苦,先生看出了它的不可避免性:“我想,苦痛是总与人生联带的”。(《鲁迅家 书全编·致许广平·一》),先生对痛苦不逃避,而是以自己的生命独个承担了所感受到的一 切,先生的痛苦是深沉的,但先生始终都竭力自己去担受而不把它传给别人:“我对人说话时, 却总拣择光明些的说出,.我为自己和为别人的设想,是两样的。所以者何,就因为我的 思想太黑暗,但是究竟是否真确,不得而知,所以只能在自身试验,不能邀请别人。”(《鲁迅 家书全编·致许广平·十一》)先生的这句话正是先生甘于承担黑暗现实的痛苦的决心的体现。 鲁迅先生虽然处身于黑暗的深渊,但依旧有着“竭力看透现实的愿望”,而且又“有意无意地 将每个强烈刺激他的新现象,与他对人生的整体认识联系起来看”,现实表象和个体(过去的) 体验互相参照,加上先生对病态人心、人生阴暗面的敏感,就使先生在当时那黑暗的社会中 得到了异于常人的深刻的现实认识。基于此,先生否定了所谓的“黄金世界”,对之,先生公

开提出质疑:“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叛徒处死刑。”(《鲁迅家书全编·致许 平·二》)“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预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自己呢?” (《头发的故事》 基于先生无法定位、 无路可走的惶惑心理和对黑暗的深刻体验, 对未来能对、全面、衣恒的托邦式的阿,杜维一送现实的道路,先先作拒 选择是:“正视(直面)现实、人生的不完美、不圆满、缺陷、偏领、有弊及短暂速朽,并从 这种正视(直面)中,杀出一条生路。”(《鲁迅语萃·编序》)基于“中间物”的人生观念, 鲁迅先生以一种“把他自己自觉地贡献在了由他所开创而为后人所践踏的联结现实与未来的 万史桥梁上”的姿 态重新 了脚,肩起了历史的责任。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 屹立着,润见一切己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 切重登访 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戏:他将要起来,使人类 苏生,或者使人类灭尽,这些造物主的良民们。(《淡淡的血痕中 -记念几人个死者和生者 和未生者》)鲁迅一再强调了“韧”的结神,在其《这个与那个》中写道:“中国一向就少右 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 少有单身鏖战的武人 见胜兆则纷 纷聚集, 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的明,冷、里,论、尖布玻抚吴抚徒的品膏家中理 的。他对中国的绝望是骨子里无余地的,他看到了中国人骨髓中的腐烂。鲁迅是中国文化中 独立无二的奇迹,他是中国知识人中悟性最高的智者,而他的悟性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对中国 国民性的批判,对中国民族奴隶根性的剖析 《野苴,过》中也期告 了“明知前面是坟却猛走”的过客形象, 可以说,中国知识分 子要反抗黑暗,除了进行韧性的反抗之外还别有何途呢?没有。 不反抗黑暗 成为黑暗 的囚徒,成为介于白与黑之间的“灰色人种”。加缪的小说《西绪弗斯神话》,也正是表彰了 这种“坚韧”的结神,西绪弗斯是在抗争的过程中取得胜利和幸福感的,反抗黑暗的结果不 论如何,不与黑暗妥协的良知都会在反抗过程中闪光。苦难是一种噬骨的的药,鲁迅是一个 有若苦避经历的人。他的灵速是建立在痛苦之上的 十年代中期,色讯一面提到耳有浓写 佛家色彩的“人生苦”的命愿,“人生多苦辛”、 人生苦痛的事太多 ,尤其是在中国”、“人 们的苦痛是不容易相通的”、“苦痛是总与人生联带的”(注:参见鲁迅《坟·写在(坟)后面》 《华盖集·导师》、《华盖集续编·“死地”》、《两地书·二》。)等,写于这一时期的《野草》 也因出带上了浓厚的佛家色影。“人生即苦”、“一切皆苦”是佛数的基本数义,佛数所言之苦 除了生老病死之外,还有求不得苦、爱别离苦、架会苦以及五取苦。意识到社会改革 艰难和个人力量的有限,在无可摆脱的孤独和绝望 鲁迅自觉地承担起扶植青年和培养新 生代的工作。以自我的牺牲和毁灭换来众生的幸福是他为自己设定的人生方式,“自己背着因 袋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但是他这种自我牺牲的立身之道,在二十年代的社会、家庭生活中却遭到一系列毁灭性地打 击,先是兄弟失和,他被无情地逐出家门,接若是一些青年在接受了他的无私帮助后,转而 攻击诬蔑他,对他施行围测,“这实在使我愤怒、怨根了,有时简直想报复”(《两地书·九五》) 这种牺牲的悲剧之所以激起他巨大的愤怒和心灵的痛苦 不仅仅因为它进一步动摇了他的过 化论思想,而且在于它直接触及到鲁迅所难以解决的“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矛盾 使他对先觉者牺牲的价值和意义感到怀疑。《野草》中最具情感震慑力的《颓败线的颤动》描 写的即是这种晒牲之苦,在老妇人“无词言语”的诅咒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鲁迅的愤 架与悲苦。《野草》所展示的正是鲁讯从苦到空,又由空到有的自我滑明的精神之旅。林毓生 说:“在世界文学中很难发现像鲁迅这样的作家 对意义作个人的 探素,同时承担唤醒他人的义务 (注:林毓生《鲁迅关于知识分子的思考》, 见乐黛云主编 《当代英语世界鲁迅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只有从“信念”这一角度契入 我们才能窥探到鲁迅精神深处的这一奥秘。鲁迅曾高度称赞唐代僧人玄奘舍身求法,忠于信 仰的殉道精神,也曾多次以称赞的口吻提及释迦牟尼“投身饲虎”坚毅品格。在鲁迅的人格
开提出质疑:“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叛徒处死刑。”(《鲁迅家书全编·致许广 平·二》)“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预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自己呢?” (《头发的故事》)基于先生无法定位、无路可走的惶惑心理和对黑暗的深刻体验,先生拒绝 了一切对未来绝对、全面、永恒的乌托邦式的幻想,杜绝一切逃避现实的道路,先生唯一的 选择是:“正视(直面)现实、人生的不完美、不圆满、缺陷、偏颇、有弊及短暂速朽,并从 这种正视(直面)中,杀出一条生路。”(《鲁迅语萃·编序》)基于“中间物”的人生观念, 鲁迅先生以一种“把他自己自觉地贡献在了由他所开创而为后人所践踏的联结现实与未来的 历史桥梁上”的姿态重新在心理上站稳了脚,肩起了历史的责任。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 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 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戏;他将要起来,使人类 苏生,或者使人类灭尽,这些造物主的良民们。(《淡淡的血痕中——记念几人个死者和生者 和未生者》)鲁迅一再强调了“韧”的精神,在其《这个与那个》中写道:“中国一向就少有 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 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鲁迅的阴、冷、黑、沦、尖、辣、烈都是中国作家中独一无二 的。他对中国的绝望是骨子里无余地的,他看到了中国人骨髓中的腐烂。鲁迅是中国文化中 独立无二的奇迹,他是中国知识人中悟性最高的智者,而他的悟性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对中国 国民性的批判,对中国民族奴隶根性的剖析。 《野草·过客》中也塑造了“明知前面是坟却猛走”的过客形象,可以说,中国知识分 子要反抗黑暗,除了进行韧性的反抗之外还别有何途呢?没有。不反抗黑暗,就会成为黑暗 的囚徒,成为介于白与黑之间的“灰色人种”。加缪的小说《西绪弗斯神话》,也正是表彰了 这种“坚韧”的精神,西绪弗斯是在抗争的过程中取得胜利和幸福感的,反抗黑暗的结果不 论如何,不与黑暗妥协的良知都会在反抗过程中闪光。苦难是一种噬骨的的药,鲁迅是一个 有着苦难经历的人。他的灵魂是建立在痛苦之上的。二十年代中期,鲁迅一再提到具有浓厚 佛家色彩的“人生苦”的命题,“人生多苦辛”、“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人 们的苦痛是不容易相通的”、“苦痛是总与人生联带的”(注:参见鲁迅《坟·写在〈坟〉后面》、 《华盖集·导师》、《华盖集续编·“死地”》、《两地书·二》。)等,写于这一时期的《野草》 也因此带上了浓厚的佛家色彩。“人生即苦”、“一切皆苦”是佛教的基本教义,佛教所言之苦, 除了生老病死之外,还有求不得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以及五取蕴苦。意识到社会改革的 艰难和个人力量的有限,在无可摆脱的孤独和绝望中,鲁迅自觉地承担起扶植青年和培养新 生代的工作。以自我的牺牲和毁灭换来众生的幸福是他为自己设定的人生方式,“自己背着因 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但是他这种自我牺牲的立身之道,在二十年代的社会、家庭生活中却遭到一系列毁灭性地打 击,先是兄弟失和,他被无情地逐出家门,接着是一些青年在接受了他的无私帮助后,转而 攻击诬蔑他,对他施行围剿,“这实在使我愤怒、怨恨了,有时简直想报复”(《两地书·九五》)。 这种牺牲的悲剧之所以激起他巨大的愤怒和心灵的痛苦,不仅仅因为它进一步动摇了他的进 化论思想,而且在于它直接触及到鲁迅所难以解决的“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矛盾, 使他对先觉者牺牲的价值和意义感到怀疑。《野草》中最具情感震慑力的《颓败线的颤动》描 写的即是这种牺牲之苦,在老妇人“无词言语”的诅咒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鲁迅的愤 怒与悲苦。《野草》所展示的正是鲁迅从苦到空,又由空到有的自我澄明的精神之旅。林毓生 说:“在世界文学中很难发现像鲁迅这样的作家——对世界持虚无主义观念,对意义作个人的 探索,同时承担唤醒他人的义务”(注:林毓生《鲁迅关于知识分子的思考》,见乐黛云主编 《当代英语世界鲁迅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只有从“信念”这一角度契入, 我们才能窥探到鲁迅精神深处的这一奥秘。鲁迅曾高度称赞唐代僧人玄奘舍身求法,忠于信 仰的殉道精神,也曾多次以称赞的口吻提及释迦牟尼“投身饲虎”坚毅品格。在鲁迅的人格

中,对信仰的忠贞,对名利的淡薄,对理想的执着以及不怕牺牲,甘于寂寞等,都显现出佛 数对他的积极影响。而他之所以始终对那纸深杯数意,称赫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 一个重题 的原因也在于耶穌的情愿以自己被钉十字架的大痛苦来实现上帝的召唤的栖牲精神 表现 出强烈的宗教激情和庄严的殉道精神,而这正是中国历史上所少有的。鲁迅认为, 人心必有 所冯依,非信无以立”(《破恶声论》),虽然他后来放弃了宗教救国的主张,但是对信仰的强 调和重视使他其至认为“伪士当去,迷信可存”(《破恶声论》).这是他与围作人极不相同的 一面(注:参见拙作《从种业论到闭户读书论 一周作人与佛教文化关系论之一》,《鲁讯研 究月刊》2000年第2期。 鲁迅之所以在为信仰而奋斗的过程中能够既保持道德激情 又不 丧失应有的理性的 在很大程度 也得力于佛家的修养和智慧 信仰是人所特 有的 种精神机制,作为价值,它的特质是给人们提供知识以外的关于未来的信念,以此构成人们 向历史深处延伸和未来极限处挺讲的精神支柱。对绝对的追求和对终极的关切是形成信仰的 驱动力,而宗教就其最广泛和最根本的意义而言也是指向一种形而上的终极关杯的,所以 “五四”作家常常是一面在科学的层面抨击宗教蒙味主义, ·面又在价值层面留恋宗教, 如庐隐所说: 我并不是信宗教的人, 但是我在精神仿徨无若的时候, 我 能 寻出信仰的对 象来”《或人的悲哀》)。 鲁迅的《野草》把笔触直逼人的内在的灵魂,指涉了逃亡、绝地、死亡以及存在的意义, 鲁迅所拥有的苦痛和绝望是罕见的,它的凄丽追问逼近了人的生存的最后底线。他的人生希 望无数次碰碎在现实的悬岸峭壁上而后进发出绝望的精神火花,这种绝望里包含了无数希望 的尸骸残片,进而使绝望也被消解掉,于是进入了 个新的自由的人生境界。《野草》流溢着 深沉的情思和对灵魂的自我拷问。黑色,是鲁迅所偏爱的颜色。黑,是一种阴郁、孤独、沉 寂和绝望的色调,具有异类的精神、悲剧的性质,象征者反抗、挑战、破坏、拒绝和复仇: 它还是百折不挠、决不妥协的生存意志和同归于尽的气概隐喻,散发出虚无的、死亡的气息, 给人一种简洁而强劲有力的美感。在他的笔下,有“眼光阴沉,黑须,乱发,黑色短衣裤楼 破碎”的“过客”:有“蓬松的头发和浓黑的须眉占了一险的小彪,只见两眼在夜气里发光 的魏连殳也有“面貌黑瘦”的禹: 又有“衣服却是青的, 须眉头发都是黑”的“黑色人 侠客:就连羿拉弓射月的雄姿,也像是“黑色火”:还有那个比别的一切鬼魂都更美、更 强的“女吊”,披散者头发,漆黑的浓眉,乌黑的眼眶,穿若黑色的长背心?先生能够能够“自 在暗中,看一切暗”。在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的昏暗中,鲁迅的呐减恰是“猫头鹰的不祥 之言”。他把这叫做“与黑暗捣乱”,借以打破“天下太平”的死哀,给黑暗的制造者 一占 舒服,使黑暗的世界有 点不圆满。散文《颓败线的颤动》,木屋内 个瘦弱渺小的、苦痛 惊异、羞辱的生命在颤动中醒来。饥饿占据了一切,母亲说到烧饼,而燃起了些许的希望 不一会却被更大的灾难淹没。场景之二,上次梦的残续,过了几十年,亦即一间小屋内,不 过己整齐。此时占据的不是饥饿,而是屈辱、卑劣。妇人抛弃一切冷驾、毒笑,走入无边荒 甲解里 一刹那间照过了一切,为亲人牺牲,却被放逐。作为“形散而神不散”的经典文章, 作家思绪飞驰万里,恐怖的梦魇带给我们奇幻、荒诞的场景,但经由特殊的艺术生命升华的 画面已不是 般的状态,更具咀嚼意蕴。我们看到鲁迅希望破灭后那痛苦的心 绝望的泪 亦有挣扎的务力。“老女人”以颓废身躯的颜动,两手举上天,口唇漏出非人间所有的无词的 言语发出了抗挣。不论是小女孩亦或是“老女人”都是作家自身命运的写照。作家在自言自 语,也许我们不应该去惊扰这颗心,但我们既已进入,终可听出一二,那炼狱般心灵发出的 声音。“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这就是鲁迅的“反抗绝望”,也是“独语体”的哲学 内漏」 鲁迅认为人只有在无所希望中才能得救,他依靠个体意志不断反抗着黑暗,自觉地承担绝 望把握人生。面对个体的生存困境,鲁迅既不选择走向宗教拯救,也不选择道家的审美逍遥, 而是拿肉体去搏斗存在的暗夜,在对绝望及对绝望的抗争中。·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
中,对信仰的忠贞,对名利的淡薄,对理想的执着以及不怕牺牲,甘于寂寞等,都显现出佛 教对他的积极影响。而他之所以始终对耶稣深怀敬意,称赞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一个重要 的原因也在于耶稣的情愿以自己被钉十字架的大痛苦来实现上帝的召唤的牺牲精神中,表现 出强烈的宗教激情和庄严的殉道精神,而这正是中国历史上所少有的。鲁迅认为,“人心必有 所冯依,非信无以立”(《破恶声论》),虽然他后来放弃了宗教救国的主张,但是对信仰的强 调和重视使他甚至认为“伪士当去,迷信可存”(《破恶声论》),这是他与周作人极不相同的 一面(注:参见拙作《从种业论到闭户读书论——周作人与佛教文化关系论之一》,《鲁迅研 究月刊》2000 年第 2 期。)。鲁迅之所以在为信仰而奋斗的过程中能够既保持道德激情,又不 丧失应有的理性的清明,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力于佛家的修养和智慧。信仰是人所特有的一 种精神机制,作为价值,它的特质是给人们提供知识以外的关于未来的信念,以此构成人们 向历史深处延伸和未来极限处挺进的精神支柱。对绝对的追求和对终极的关切是形成信仰的 驱动力,而宗教就其最广泛和最根本的意义而言也是指向一种形而上的终极关怀的,所以, “五四”作家常常是一面在科学的层面抨击宗教蒙昧主义,一面又在价值层面留恋宗教,正 如庐隐所说:“我并不是信宗教的人,但是我在精神仿徨无着的时候,我不能不寻出信仰的对 象来”《或人的悲哀》)。 鲁迅的《野草》把笔触直逼人的内在的灵魂,指涉了逃亡、绝地、死亡以及存在的意义, 鲁迅所拥有的苦痛和绝望是罕见的,它的凄丽追问逼近了人的生存的最后底线。他的人生希 望无数次碰碎在现实的悬崖峭壁上而后迸发出绝望的精神火花,这种绝望里包含了无数希望 的尸骸残片,进而使绝望也被消解掉,于是进入了一个新的自由的人生境界。《野草》流溢着 深沉的情思和对灵魂的自我拷问。黑色,是鲁迅所偏爱的颜色。黑,是一种阴郁、孤独、沉 寂和绝望的色调,具有异类的精神、悲剧的性质,象征着反抗、挑战、破坏、拒绝和复仇; 它还是百折不挠、决不妥协的生存意志和同归于尽的气概隐喻,散发出虚无的、死亡的气息, 给人一种简洁而强劲有力的美感。在他的笔下,有“眼光阴沉,黑须,乱发,黑色短衣裤皆 破碎”的“过客”;有“蓬松的头发和浓黑的须眉占了一脸的小彪,只见两眼在夜气里发光” 的魏连殳 ;也有“面貌黑瘦”的禹;又有“衣服却是青的,须眉头发都是黑”的“黑色人” ——侠客;就连羿拉弓射月的雄姿,也像是“黑色火”;还有那个比别的一切鬼魂都更美、更 强的“女吊”,披散着头发,漆黑的浓眉,乌黑的眼眶,穿着黑色的长背心?先生能够能够“自 在暗中,看一切暗”。在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的昏暗中,鲁迅的呐喊恰是“猫头鹰的不祥 之言”。他把这叫做“与黑暗捣乱”,借以打破“天下太平”的死寂,给黑暗的制造者一点不 舒服,使黑暗的世界有一点不圆满。散文《颓败线的颤动》,木屋内,一个瘦弱渺小的、苦痛、 惊异、羞辱的生命在颤动中醒来。饥饿占据了一切,母亲说到烧饼,而燃起了些许的希望, 不一会却被更大的灾难淹没。场景之二,上次梦的残续,过了几十年,亦即一间小屋内,不 过已整齐。此时占据的不是饥饿,而是屈辱、卑劣。妇人抛弃一切冷骂、毒笑,走入无边荒 野里。一刹那间照过了一切,为亲人牺牲,却被放逐。作为“形散而神不散”的经典文章, 作家思绪飞驰万里,恐怖的梦魇带给我们奇幻、荒诞的场景,但经由特殊的艺术生命升华的 画面已不是一般的状态,更具咀嚼意蕴。我们看到鲁迅希望破灭后那痛苦的心、绝望的泪, 亦有挣扎的努力。“老女人”以颓废身躯的颤动,两手举上天,口唇漏出非人间所有的无词的 言语发出了抗挣。不论是小女孩亦或是“老女人”都是作家自身命运的写照。作家在自言自 语,也许我们不应该去惊扰这颗心,但我们既已进入,终可听出一二,那炼狱般心灵发出的 声音。“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这就是鲁迅的“反抗绝望”,也是“独语体”的哲学 内涵。 鲁迅认为人只有在无所希望中才能得救,他依靠个体意志不断反抗着黑暗,自觉地承担绝 望把握人生。面对个体的生存困境,鲁迅既不选择走向宗教拯救,也不选择道家的审美逍遥, 而是拿肉体去搏斗存在的暗夜,在对绝望及对绝望的抗争中。.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