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功”,就连用了两个“的”字如在第二个“的”字前面加上“取得”二字,就好一点。现在把 这一部分译成一个分句就更好了。) 19英语在一个句子里往往先说个人的感受,再说与感受有关的动作,最后才说最初发生的 事情。汉语则相反,往往按照事情发生的顺序来叙述,最后才说个人的感受。 The most important day I remember in all my life is the one on which my teacher,Anne Mansfield Sullivan,came to me.I am filled with wonder when I consider the immeasurable contrast between the two lives which it connects. 在我的记忆里,安妮·曼斯菲尔德·沙利文老师来的那一天,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 从这一天开始,我的生活和以前迥然不同,一想到这一点,我就感到非常兴奋。 20.表达同样的意思,英语的结构比较紧,汉语的结构比较松。 A gang of men,under the direction of their energetic and likeable foreman,25-year-old Phineas P. Gage,was working on a new line of the Rutland and Burlington railroad. 一伙工人正跟着他们的领班在拉特兰一伯灵顿铁路的新线路上干活。这位领班名叫菲尼 斯·P·盖奇,二十五岁,他精力充沛,待人和气。(原文是一简单句,有一个主语,一个谓语 动词,却包含了这么多内容,结构显得比较紧。译文分为两句,第二句还包含两个并列分句, 结构显得比较松。) 21.拆句的情况多,合句的情况少。 Poets as we know have always a made great use of alliteration.They are persuaded that the repetition of a sound gives an effect of beauty. 我们知道,诗人一般总喜欢押头韵,觉得重复一个声音会产生美的效果。(原文两句都比较 短,译文合成一句,语气较顺。) 22.注意文体,应该用口语的地方,选用适合口语的词句。 "I remember thinking,'No.No.It's not Jackson,it's not my husband,it's not my Jackson,'" she said."But it was.He was lying in the street,right across from our house.The police said a man shot him over a parking space." “记得我当时就想:‘不,不。不是杰克逊,不是我丈夫,不是我的杰克逊’”她说。“可是, 那不是别人,正是他。他躺在大街上,就在我们的房子对面。警察说,为了争一块停车的地方, 人家把他打死了。” 23.一段文章的最后一句,特别是全文最后一段的最后一句,要比较有力,否则文章煞不住。 中英文都是这样。翻译时就要把这最后一句的分量表达出来,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Words have weight,sound and appearance;it is only by considering these that you can write a sentence that is good to look at and good to listen to. 词具有一定的分量、声音和形状,只有考虑到这些因素,写出来的句子才能既好听,又好 看。(若把“好听”放在最后,就压不住了。) 24题目可以照原文译,也可以根据文章的内容拟定。 A Valentine to One Who Cared Too Much. 衷肠曲(这个题目是参照文章的内容拟定的。原题的意思是:在情人节写给一个人的信, 这个人关心的事情太多了。) 25遇到中国读者可能不熟悉的典故、人名、地名等,除了加注以外,还可以在译文中加几 个字,略加说明。 I learned a great many new words that day.I do not remember what they all were;but I do know that mother,father,sister,teacher were among them -words that were to make the world blossom for me,"like Aaron's rod,with flowers. 那一天我学了许多新词,也记不清都有哪些词了。但是其中肯定有“母亲”、“父亲”、“姐 姐”、“老师”一一后来就是这些词把一个美好的世界展现在我的面前,就像《圣经》上说的“亚 16
16 成功”,就连用了两个“的”字.如在第二个“的”字前面加上“取得”二字,就好一点。现在把 这一部分译成一个分句就更好了。) 19.英语在一个句子里往往先说个人的感受,再说与感受有关的动作,最后才说最初发生的 事情。汉语则相反,往往按照事情发生的顺序来叙述,最后才说个人的感受。 The most important day I remember in all my life is the one on which my teacher,Anne Mansfield Sullivan, came to me. I am filled with wonder when I consider the immeasurable contrast between the two lives which it connects. 在我的记忆里,安妮·曼斯菲尔德·沙利文老师来的那一天,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 从这一天开始,我的生活和以前迥然不同,一想到这一点,我就感到非常兴奋。 20.表达同样的意思,英语的结构比较紧,汉语的结构比较松。 A gang of men, under the direction of their energetic and likeable foreman, 25-year-old Phineas P. Gage, was working on a new line of the Rutland and Burlington railroad. 一伙工人正跟着他们的领班在拉特兰-伯灵顿铁路的新线路上干活。这位领班名叫菲尼 斯·P·盖奇,二十五岁,他精力充沛,待人和气。(原文是一简单句,有一个主语,一个谓语 动词,却包含了这么多内容,结构显得比较紧。译文分为两句,第二句还包含两个并列分句, 结构显得比较松。) 21.拆句的情况多,合句的情况少。 Poets as we know have always a made great use of alliteration. They are persuaded that the repetition of a sound gives an effect of beauty. 我们知道,诗人一般总喜欢押头韵,觉得重复一个声音会产生美的效果。(原文两句都比较 短,译文合成一句,语气较顺。) 22.注意文体,应该用口语的地方,选用适合口语的词句。 “I remember thinking, ‘No. No. It’s not Jackson, it’s not my husband, it’s not my Jackson,’” she said. “But it was. He was lying in the street, right across from our house. The police said a man shot him over a parking space.” “记得我当时就想:‘不,不。不是杰克逊,不是我丈夫,不是我的杰克逊’”她说。“可是, 那不是别人,正是他。他躺在大街上,就在我们的房子对面。警察说,为了争一块停车的地方, 人家把他打死了。” 23.一段文章的最后一句,特别是全文最后一段的最后一句,要比较有力,否则文章煞不住。 中英文都是这样。翻译时就要把这最后一句的分量表达出来,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Words have weight, sound and appearance; it is only by considering these that you can write a sentence that is good to look at and good to listen to. 词具有一定的分量、声音和形状,只有考虑到这些因素,写出来的句子才能既好听,又好 看。(若把“好听”放在最后,就压不住了。) 24.题目可以照原文译,也可以根据文章的内容拟定。 A Valentine to One Who Cared Too Much. 衷肠曲(这个题目是参照文章的内容拟定的。原题的意思是:在情人节写给一个人的信, 这个人关心的事情太多了。) 25.遇到中国读者可能不熟悉的典故、人名、地名等,除了加注以外,还可以在译文中加几 个字,略加说明。 I learned a great many new words that day. I do not remember what they all were; but I do know that mother, father,sister, teacher were among them — words that were to make the world blossom for me, “like Aaron’s rod, with flowers.” 那一天我学了许多新词,也记不清都有哪些词了。但是其中肯定有“母亲”、“父亲”、“姐 姐”、“老师”——后来就是这些词把一个美好的世界展现在我的面前,就像《圣经》上说的“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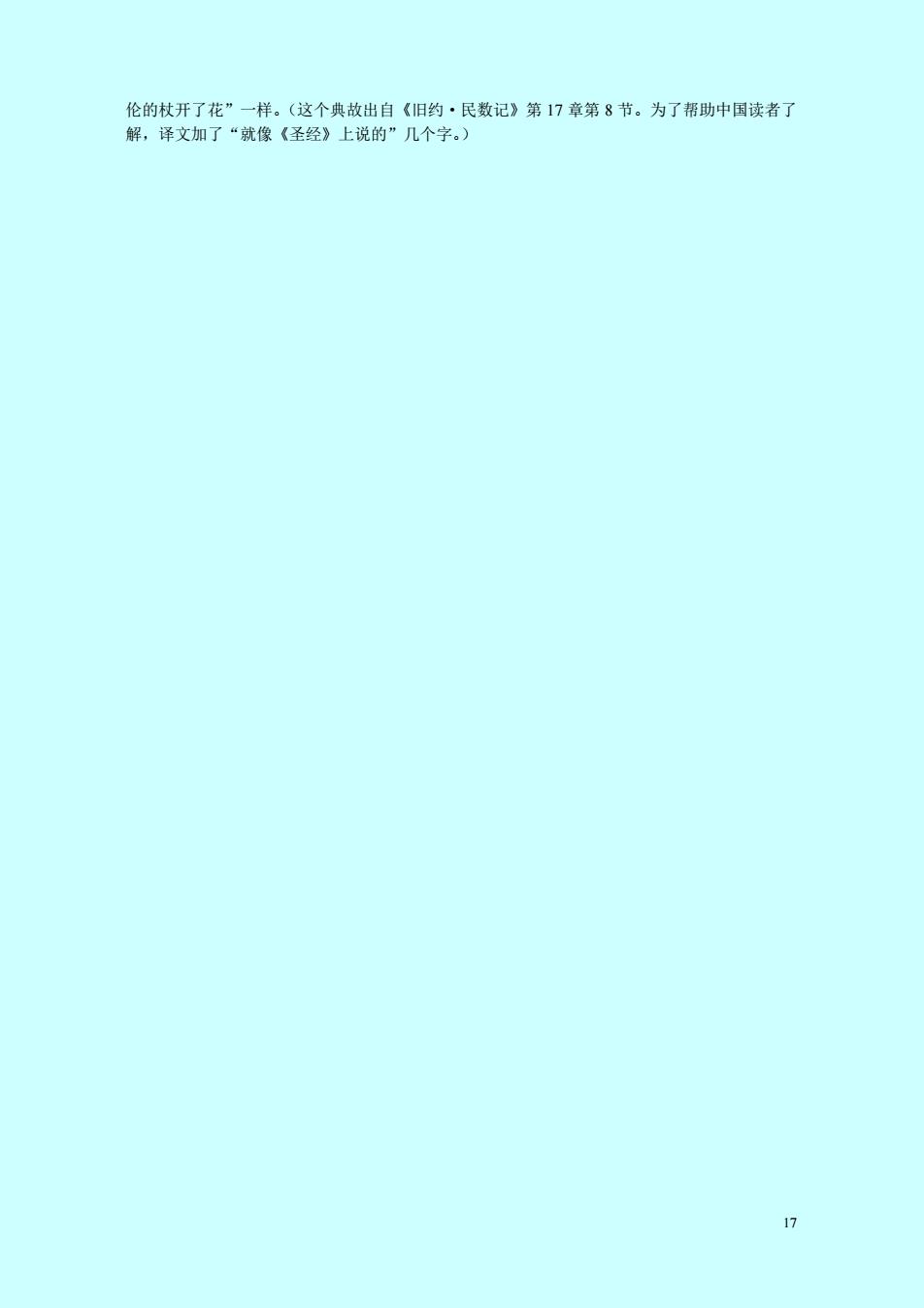
伦的杖开了花”一样。(这个典故出自《旧约·民数记》第17章第8节。为了帮助中国读者了 解,译文加了“就像《圣经》上说的”几个字。) 17
17 伦的杖开了花”一样。(这个典故出自《旧约·民数记》第 17 章第 8 节。为了帮助中国读者了 解,译文加了“就像《圣经》上说的”几个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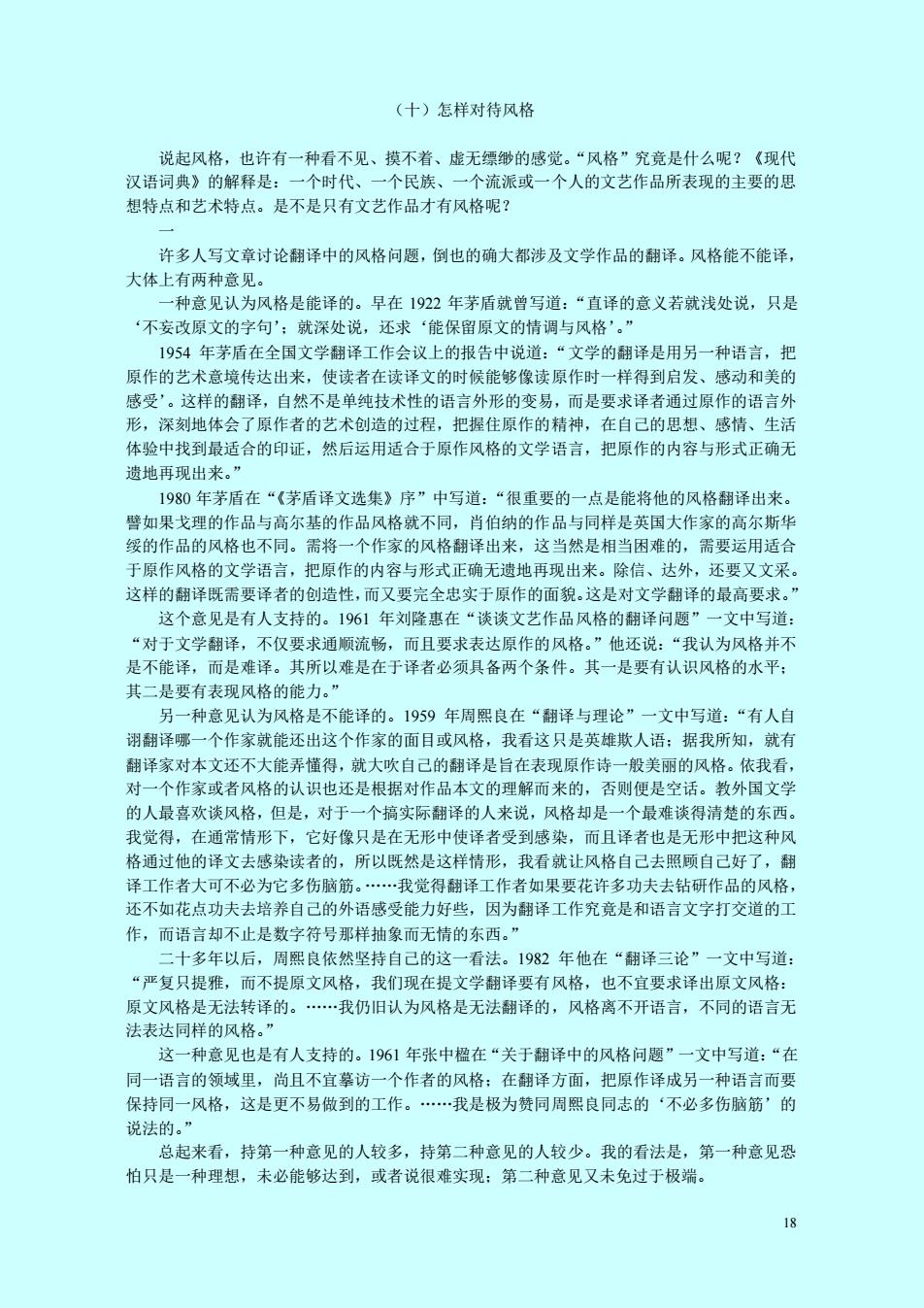
(十)怎样对待风格 说起风格,也许有一种看不见、摸不着、虚无缥缈的感觉。“风格”究竞是什么呢?《现代 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流派或一个人的文艺作品所表现的主要的思 想特点和艺术特点。是不是只有文艺作品才有风格呢? 许多人写文章讨论翻译中的风格问题,倒也的确大都涉及文学作品的翻译。风格能不能译, 大体上有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风格是能译的。早在1922年茅盾就曾写道:“直译的意义若就浅处说,只是 ‘不妄改原文的字句':就深处说,还求‘能保留原文的情调与风格’。” 1954年茅盾在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说道:“文学的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 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 感受'。这样的翻译,自然不是单纯技术性的语言外形的变易,而是要求译者通过原作的语言外 形,深刻地体会了原作者的艺术创造的过程,把握住原作的精神,在自己的思想、感情、生活 体验中找到最适合的印证,然后运用适合于原作风格的文学语言,把原作的内容与形式正确无 遗地再现出来。” 1980年茅盾在“《茅盾译文选集》序”中写道:“很重要的一点是能将他的风格翻译出来。 譬如果戈理的作品与高尔基的作品风格就不同,肖伯纳的作品与同样是英国大作家的高尔斯华 绥的作品的风格也不同。需将一个作家的风格翻译出来,这当然是相当困难的,需要运用适合 于原作风格的文学语言,把原作的内容与形式正确无遗地再现出来。除信、达外,还要又文采。 这样的翻译既需要译者的创造性,而又要完全忠实于原作的面貌。这是对文学翻译的最高要求。” 这个意见是有人支持的。1961年刘隆惠在“谈谈文艺作品风格的翻译问题”一文中写道: “对于文学翻译,不仅要求通顺流畅,而且要求表达原作的风格。”他还说:“我认为风格并不 是不能译,而是难译。其所以难是在于译者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是要有认识风格的水平: 其二是要有表现风格的能力。” 另一种意见认为风格是不能译的。1959年周熙良在“翻译与理论”一文中写道:“有人自 诩翻译哪一个作家就能还出这个作家的面目或风格,我看这只是英雄欺人语:据我所知,就有 翻译家对本文还不大能弄懂得,就大吹自己的翻译是旨在表现原作诗一般美丽的风格。依我看, 对一个作家或者风格的认识也还是根据对作品本文的理解而来的,否则便是空话。教外国文学 的人最喜欢谈风格,但是,对于一个搞实际翻译的人来说,风格却是一个最难谈得清楚的东西。 我觉得,在通常情形下,它好像只是在无形中使译者受到感染,而且译者也是无形中把这种风 格通过他的译文去感染读者的,所以既然是这样情形,我看就让风格自己去照顾自己好了,翻 译工作者大可不必为它多伤脑筋。.我觉得翻译工作者如果要花许多功夫去钻研作品的风格, 还不如花点功夫去培养自己的外语感受能力好些,因为翻译工作究竞是和语言文字打交道的工 作,而语言却不止是数字符号那样抽象而无情的东西。” 二十多年以后,周熙良依然坚持自己的这一看法。1982年他在“翻译三论”一文中写道: “严复只提雅,而不提原文风格,我们现在提文学翻译要有风格,也不宜要求译出原文风格: 原文风格是无法转译的。.我仍旧认为风格是无法翻译的,风格离不开语言,不同的语言无 法表达同样的风格。” 这一种意见也是有人支持的。1961年张中楹在“关于翻译中的风格问题”一文中写道:“在 同一语言的领域里,尚且不宜墓访一个作者的风格;在翻译方面,把原作译成另一种语言而要 保持同一风格,这是更不易做到的工作。.我是极为赞同周熙良同志的‘不必多伤脑筋’的 说法的。” 总起来看,持第一种意见的人较多,持第二种意见的人较少。我的看法是,第一种意见恐 怕只是一种理想,未必能够达到,或者说很难实现:第二种意见又未免过于极端。 18
18 (十)怎样对待风格 说起风格,也许有一种看不见、摸不着、虚无缥缈的感觉。“风格”究竟是什么呢?《现代 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流派或一个人的文艺作品所表现的主要的思 想特点和艺术特点。是不是只有文艺作品才有风格呢? 一 许多人写文章讨论翻译中的风格问题,倒也的确大都涉及文学作品的翻译。风格能不能译, 大体上有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风格是能译的。早在 1922 年茅盾就曾写道:“直译的意义若就浅处说,只是 ‘不妄改原文的字句’;就深处说,还求‘能保留原文的情调与风格’。” 1954 年茅盾在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说道:“文学的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 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 感受’。这样的翻译,自然不是单纯技术性的语言外形的变易,而是要求译者通过原作的语言外 形,深刻地体会了原作者的艺术创造的过程,把握住原作的精神,在自己的思想、感情、生活 体验中找到最适合的印证,然后运用适合于原作风格的文学语言,把原作的内容与形式正确无 遗地再现出来。” 1980 年茅盾在“《茅盾译文选集》序”中写道:“很重要的一点是能将他的风格翻译出来。 譬如果戈理的作品与高尔基的作品风格就不同,肖伯纳的作品与同样是英国大作家的高尔斯华 绥的作品的风格也不同。需将一个作家的风格翻译出来,这当然是相当困难的,需要运用适合 于原作风格的文学语言,把原作的内容与形式正确无遗地再现出来。除信、达外,还要又文采。 这样的翻译既需要译者的创造性,而又要完全忠实于原作的面貌。这是对文学翻译的最高要求。” 这个意见是有人支持的。1961 年刘隆惠在“谈谈文艺作品风格的翻译问题”一文中写道: “对于文学翻译,不仅要求通顺流畅,而且要求表达原作的风格。”他还说:“我认为风格并不 是不能译,而是难译。其所以难是在于译者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是要有认识风格的水平; 其二是要有表现风格的能力。” 另一种意见认为风格是不能译的。1959 年周熙良在“翻译与理论”一文中写道:“有人自 诩翻译哪一个作家就能还出这个作家的面目或风格,我看这只是英雄欺人语;据我所知,就有 翻译家对本文还不大能弄懂得,就大吹自己的翻译是旨在表现原作诗一般美丽的风格。依我看, 对一个作家或者风格的认识也还是根据对作品本文的理解而来的,否则便是空话。教外国文学 的人最喜欢谈风格,但是,对于一个搞实际翻译的人来说,风格却是一个最难谈得清楚的东西。 我觉得,在通常情形下,它好像只是在无形中使译者受到感染,而且译者也是无形中把这种风 格通过他的译文去感染读者的,所以既然是这样情形,我看就让风格自己去照顾自己好了,翻 译工作者大可不必为它多伤脑筋。.我觉得翻译工作者如果要花许多功夫去钻研作品的风格, 还不如花点功夫去培养自己的外语感受能力好些,因为翻译工作究竟是和语言文字打交道的工 作,而语言却不止是数字符号那样抽象而无情的东西。” 二十多年以后,周熙良依然坚持自己的这一看法。1982 年他在“翻译三论”一文中写道: “严复只提雅,而不提原文风格,我们现在提文学翻译要有风格,也不宜要求译出原文风格: 原文风格是无法转译的。.我仍旧认为风格是无法翻译的,风格离不开语言,不同的语言无 法表达同样的风格。” 这一种意见也是有人支持的。1961 年张中楹在“关于翻译中的风格问题”一文中写道:“在 同一语言的领域里,尚且不宜摹访一个作者的风格;在翻译方面,把原作译成另一种语言而要 保持同一风格,这是更不易做到的工作。.我是极为赞同周熙良同志的‘不必多伤脑筋’的 说法的。” 总起来看,持第一种意见的人较多,持第二种意见的人较少。我的看法是,第一种意见恐 怕只是一种理想,未必能够达到,或者说很难实现;第二种意见又未免过于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