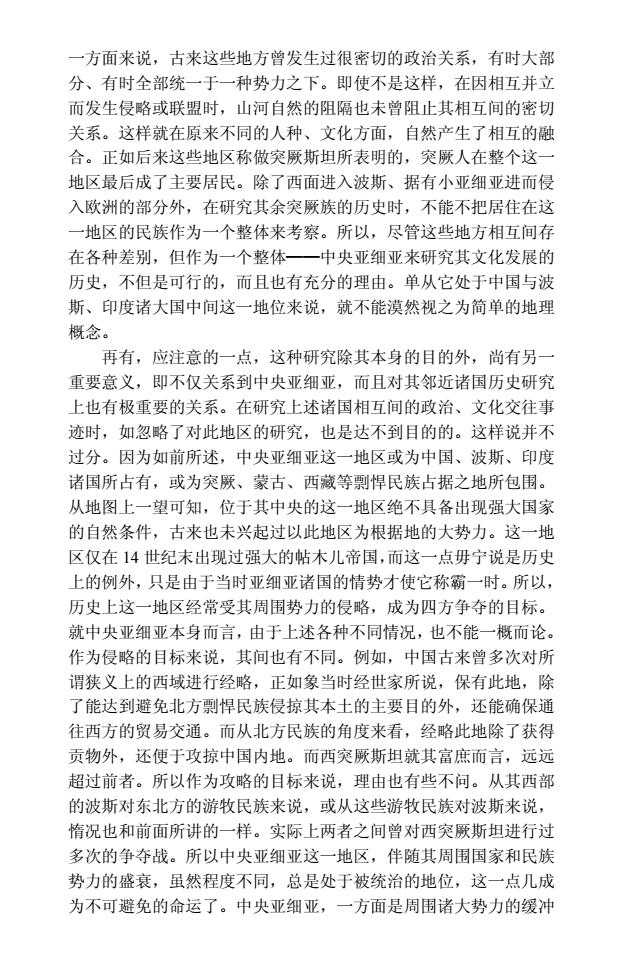
一方面来说,古来这些地方曾发生过很密切的政治关系,有时大部 分、有时全部统一于一种势力之下。即使不是这样,在因相互并立 而发生侵略或联盟时,山河自然的阻隔也未曾阻止其相互间的密切 关系。这样就在原来不同的人种、文化方面,自然产生了相互的融 合。正如后来这些地区称做突厥斯坦所表明的,突厥人在整个这 地区最后成了主要居民。除了西面进入波斯、据有小亚细亚进而侵 入欧洲的部分外,在研究其余突厥族的历史时,不能不把居住在这 一地区的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所以,尽管这些地方相互间存 在各种差别,但作为一个整体 一中央亚细亚来研究其文化发展的 历史,不但是可行的,而且也有充分的理由。单从它处于中国与波 斯、印度诸大国中间这一地位来说,就不能漠然视之为简单的地理 概念。 再有,应注意的一点,这种研究除其本身的目的外,尚有另 重要意义,即不仅关系到中央亚细亚,而且对其邻近诸国历史研究 上也有极重要的关系。在研究上述诸国相互间的政治、文化交往事 迹时,如忽略了对此地区的研究,也是达不到目的的。这样说并不 过分。因为如前所述,中央亚细亚这一地区或为中国、波斯、印度 诸国所占有,或为突厥、蒙古、西藏等剽悍民族占据之地所包围。 从地图上一望可知,位于其中央的这一地区绝不具备出现强大国家 的自然条件,古来也未兴起过以此地区为根据地的大势力。这一地 区仅在14世纪末出现过强大的帖木儿帝国,而这一点毋宁说是历史 上的例外,只是由于当时亚细亚诸国的情势才使它称霸一时。所以, 历史上这一地区经常受其周围势力的侵略,成为四方争夺的目标。 就中央亚细亚本身而言,由于上述各种不同情况,也不能一概而论。 作为侵略的目标来说,其间也有不同。例如,中国古来曾多次对所 谓狭义上的西域进行经略,正如象当时经世家所说,保有此地,除 了能达到避免北方剽悍民族侵掠其本土的主要目的外,还能确保通 往西方的贸易交通。而从北方民族的角度来看,经略此地除了获得 贡物外,还便于攻掠中国内地。而西突厥斯坦就其富庶而言,远远 超过前者。所以作为攻略的目标来说,理由也有些不问。从其西部 的波斯对东北方的游牧民族来说,或从这些游牧民族对波斯来说, 惰况也和前面所讲的一样。实际上两者之间曾对西突厥斯坦进行过 多次的争夺战。所以中央亚细亚这一地区,伴随其周围国家和民族 势力的盛衰,虽然程度不同,总是处于被统治的地位,这一点几成 为不可避免的命运了。中央亚细亚,一方面是周围诸大势力的缓冲
一方面来说,古来这些地方曾发生过很密切的政治关系,有时大部 分、有时全部统一于一种势力之下。即使不是这样,在因相互并立 而发生侵略或联盟时,山河自然的阻隔也未曾阻止其相互间的密切 关系。这样就在原来不同的人种、文化方面,自然产生了相互的融 合。正如后来这些地区称做突厥斯坦所表明的,突厥人在整个这一 地区最后成了主要居民。除了西面进入波斯、据有小亚细亚进而侵 入欧洲的部分外,在研究其余突厥族的历史时,不能不把居住在这 一地区的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所以,尽管这些地方相互间存 在各种差别,但作为一个整体——中央亚细亚来研究其文化发展的 历史,不但是可行的,而且也有充分的理由。单从它处于中国与波 斯、印度诸大国中间这一地位来说,就不能漠然视之为简单的地理 概念。 再有,应注意的一点,这种研究除其本身的目的外,尚有另一 重要意义,即不仅关系到中央亚细亚,而且对其邻近诸国历史研究 上也有极重要的关系。在研究上述诸国相互间的政治、文化交往事 迹时,如忽略了对此地区的研究,也是达不到目的的。这样说并不 过分。因为如前所述,中央亚细亚这一地区或为中国、波斯、印度 诸国所占有,或为突厥、蒙古、西藏等剽悍民族占据之地所包围。 从地图上一望可知,位于其中央的这一地区绝不具备出现强大国家 的自然条件,古来也未兴起过以此地区为根据地的大势力。这一地 区仅在 14 世纪末出现过强大的帖木儿帝国,而这一点毋宁说是历史 上的例外,只是由于当时亚细亚诸国的情势才使它称霸一时。所以, 历史上这一地区经常受其周围势力的侵略,成为四方争夺的目标。 就中央亚细亚本身而言,由于上述各种不同情况,也不能一概而论。 作为侵略的目标来说,其间也有不同。例如,中国古来曾多次对所 谓狭义上的西域进行经略,正如象当时经世家所说,保有此地,除 了能达到避免北方剽悍民族侵掠其本土的主要目的外,还能确保通 往西方的贸易交通。而从北方民族的角度来看,经略此地除了获得 贡物外,还便于攻掠中国内地。而西突厥斯坦就其富庶而言,远远 超过前者。所以作为攻略的目标来说,理由也有些不问。从其西部 的波斯对东北方的游牧民族来说,或从这些游牧民族对波斯来说, 惰况也和前面所讲的一样。实际上两者之间曾对西突厥斯坦进行过 多次的争夺战。所以中央亚细亚这一地区,伴随其周围国家和民族 势力的盛衰,虽然程度不同,总是处于被统治的地位,这一点几成 为不可避免的命运了。中央亚细亚,一方面是周围诸大势力的缓冲

地带,另一方面相互远隔的亚细亚各大强国又通过此处连结起来, 建立了不可分离的相互关系。 中亚同其周围诸国的密切关系不仅表现在政治上,也极其明显 地表现在文化历史上。东方中国、南方印度、西方波斯、阿拉伯、 希腊、罗马等诸方文明的交流传播情况,是历史上最有兴趣的现象, 也是重要的研究课题。而这种文明的交流传播,不言而喻,是以相 互间的直接或间接交通的存在为前提的。东西交通在海路交通发达 以前,中央亚细亚是最普通的通道。就是在海路发达之后,如取陆 路也必须经过此处。不仅从波斯、阿拉伯、欧洲东来,就是从南方 印度来中国,通常也是先北上进入中亚,然后再折向东方。对当中 西交通之初、和前后开拓的蒙古地方与西方交通而言,无疑也是经 过这一地区的一部分。所以在东西交通史上或东西文明传播史上, 此地区的历史也具有很大的意义。但应强调指出,从来在这一点上 认识到西域史意义的人,只是注意到东西交通通过此处,东西文明 经过这里相互传播,而进一步对它如何行于此地,如何发展等方面, 则未太注意。这是西域史研究尚处于开创时期不可避免的情况。凡 如文明的传播等现象,在过去主要靠陆路交通的情况下,从甲地传 到乙地,原则上一般都是渐次波及相互邻近的地区,然后才间接地 传到远方(飞越中间地方是极少的特殊情况。海路交通只经过比较 少的港口,与陆路不同)。例如西方诸宗教的东传,在其传入中国以 前,必须经过地当通道的西域地方,也即经过富有宗教热情和思想 的伊兰人种或与其类似的人种居住的地方。这些宗教先传入此地, 然后再从这里传入中国内地,这应是很自然的事。艺术和学术的传 播也是如此。要之,在东西文明相互传播上,此地区起一种纽带作 用。这一点也与上面所谈这一地区对周围诸国政治方面的位置相当。 作为其间的纽带,诸方文明在这里或因相互融合,或因当地民族加 进了自己的东西而产生一些变化,甚至出现与本来面貌很不相同的 东西,但仍以本来名称更向东西传播。在这种情况下,如不研究此 纽带地区的文明,而径直研究处于两端的东西,那是不能得其正鹄 的。所以,对于此地文化史的研究,除有其自身的重要意义外,对 周围诸国文化史的研究也具有重大意义。 以上我们规定了所谓西域一词的含义,说明了西域史成立之所 以,也简述了其在范围广大的东、西方历史上的意义。以下所论述 的当然是以此地为中心。但由于历史上的复杂现象,常常要求在地 理上超出这一范围,况且西域史的一半意义尚在于其与周围诸国的
地带,另一方面相互远隔的亚细亚各大强国又通过此处连结起来, 建立了不可分离的相互关系。 中亚同其周围诸国的密切关系不仅表现在政治上,也极其明显 地表现在文化历史上。东方中国、南方印度、西方波斯、阿拉伯、 希腊、罗马等诸方文明的交流传播情况,是历史上最有兴趣的现象, 也是重要的研究课题。而这种文明的交流传播,不言而喻,是以相 互间的直接或间接交通的存在为前提的。东西交通在海路交通发达 以前,中央亚细亚是最普通的通道。就是在海路发达之后,如取陆 路也必须经过此处。不仅从波斯、阿拉伯、欧洲东来,就是从南方 印度来中国,通常也是先北上进入中亚,然后再折向东方。对当中 西交通之初、和前后开拓的蒙古地方与西方交通而言,无疑也是经 过这一地区的一部分。所以在东西交通史上或东西文明传播史上, 此地区的历史也具有很大的意义。但应强调指出,从来在这一点上 认识到西域史意义的人,只是注意到东西交通通过此处,东西文明 经过这里相互传播,而进一步对它如何行于此地,如何发展等方面, 则未太注意。这是西域史研究尚处于开创时期不可避免的情况。凡 如文明的传播等现象,在过去主要靠陆路交通的情况下,从甲地传 到乙地,原则上一般都是渐次波及相互邻近的地区,然后才间接地 传到远方(飞越中间地方是极少的特殊情况。海路交通只经过比较 少的港口,与陆路不同)。例如西方诸宗教的东传,在其传入中国以 前,必须经过地当通道的西域地方,也即经过富有宗教热情和思想 的伊兰人种或与其类似的人种居住的地方。这些宗教先传入此地, 然后再从这里传入中国内地,这应是很自然的事。艺术和学术的传 播也是如此。要之,在东西文明相互传播上,此地区起一种纽带作 用。这一点也与上面所谈这一地区对周围诸国政治方面的位置相当。 作为其间的纽带,诸方文明在这里或因相互融合,或因当地民族加 进了自己的东西而产生一些变化,甚至出现与本来面貌很不相同的 东西,但仍以本来名称更向东西传播。在这种情况下,如不研究此 纽带地区的文明,而径直研究处于两端的东西,那是不能得其正鹄 的。所以,对于此地文化史的研究,除有其自身的重要意义外,对 周围诸国文化史的研究也具有重大意义。 以上我们规定了所谓西域一词的含义,说明了西域史成立之所 以,也简述了其在范围广大的东、西方历史上的意义。以下所论述 的当然是以此地为中心。但由于历史上的复杂现象,常常要求在地 理上超出这一范围,况且西域史的一半意义尚在于其与周围诸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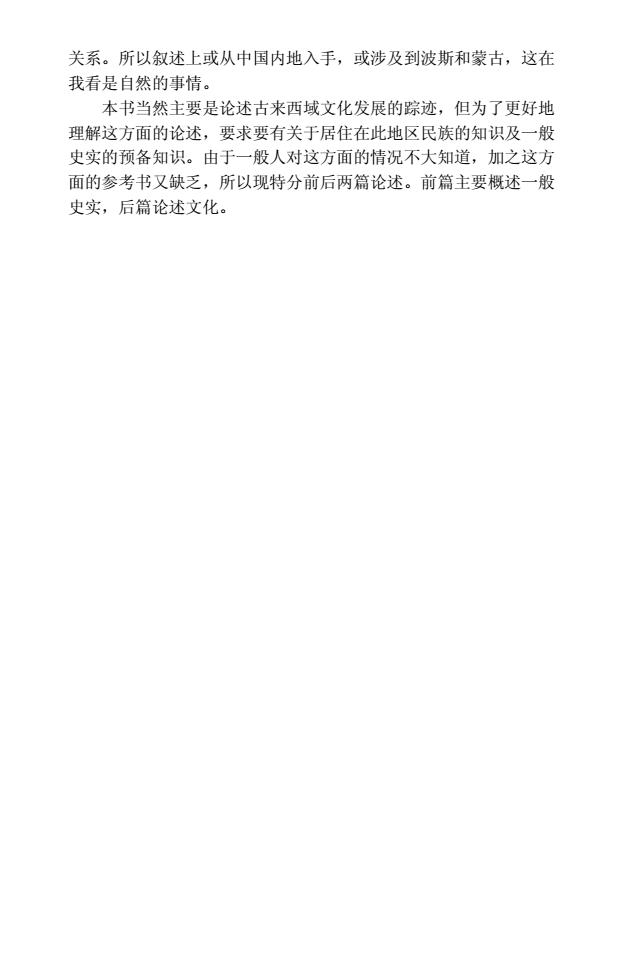
关系。所以叙述上或从中国内地入手,或涉及到波斯和蒙古,这在 我看是自然的事情。 本书当然主要是论述古来西域文化发展的踪迹,但为了更好地 理解这方面的论述,要求要有关于居住在此地区民族的知识及一般 史实的预备知识。由于一般人对这方面的情况不大知道,加之这方 面的参考书又缺乏,所以现特分前后两篇论述。前篇主要概述一般 史实,后篇论述文化
关系。所以叙述上或从中国内地入手,或涉及到波斯和蒙古,这在 我看是自然的事情。 本书当然主要是论述古来西域文化发展的踪迹,但为了更好地 理解这方面的论述,要求要有关于居住在此地区民族的知识及一般 史实的预备知识。由于一般人对这方面的情况不大知道,加之这方 面的参考书又缺乏,所以现特分前后两篇论述。前篇主要概述一般 史实,后篇论述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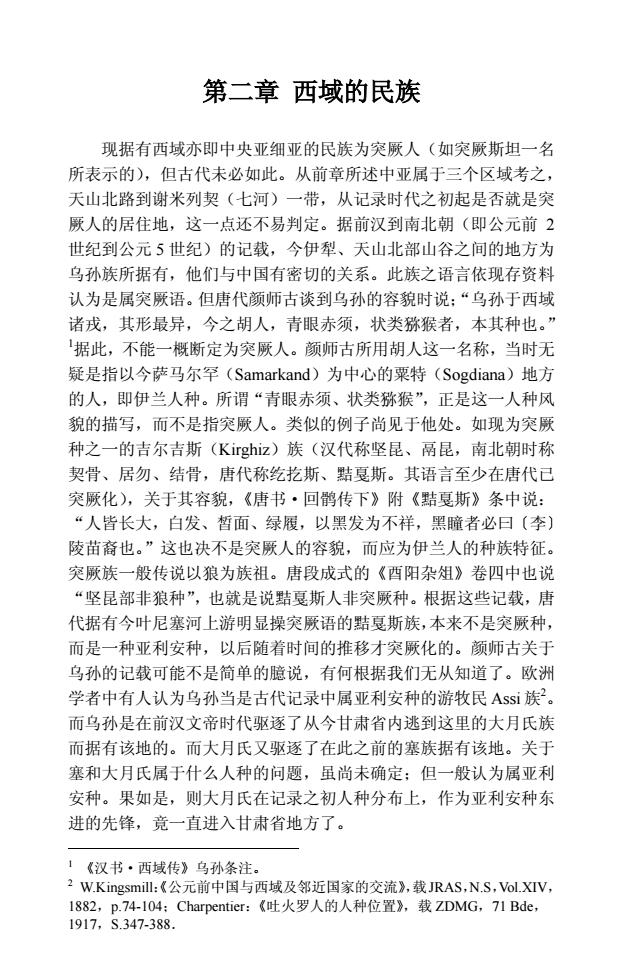
第二章西域的民族 现据有西域亦即中央亚细亚的民族为突厥人(如突厥斯坦一名 所表示的),但古代未必如此。从前章所述中亚属于三个区域考之, 天山北路到谢米列契(七河)一带,从记录时代之初起是否就是突 厥人的居住地,这一点还不易判定。据前汉到南北朝(即公元前2 世纪到公元5世纪)的记载,今伊犁、天山北部山谷之间的地方为 乌孙族所据有,他们与中国有密切的关系。此族之语言依现存资料 认为是属突厥语。但唐代颜师古谈到乌孙的容貌时说:“乌孙于西域 诸戎,其形最异,今之胡人,青眼赤须,状类猕猴者,本其种也。” '据此,不能一概断定为突厥人。颜师古所用胡人这一名称,当时无 疑是指以今萨马尔罕(Samarkand)为中心的粟特(Sogdiana)地方 的人,即伊兰人种。所谓“青眼赤须、状类猕猴”,正是这一人种风 貌的描写,而不是指突厥人。类似的例子尚见于他处。如现为突厥 种之一的吉尔吉斯(Kirghiz)族(汉代称坚昆、鬲昆,南北朝时称 契骨、居勿、结骨,唐代称纥扢斯、黠戛斯。其语言至少在唐代已 突厥化),关于其容貌,《唐书·回鹘传下》附《黠戛斯》条中说: “人皆长大,白发、皙面、绿履,以黑发为不祥,黑瞳者必日(李) 陵苗裔也。”这也决不是突厥人的容貌,而应为伊兰人的种族特征 突厥族一般传说以狼为族祖。唐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卷四中也说 “坚昆部非狼种”,也就是说黠戛斯人非突厥种。根据这些记载,唐 代据有今叶尼塞河上游明显操突厥语的黠戛斯族,本来不是突厥种, 而是一种亚利安种,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才突厥化的。颜师古关于 乌孙的记载可能不是简单的臆说,有何根据我们无从知道了。欧洲 学者中有人认为乌孙当是古代记录中属亚利安种的游牧民Assi族。 而乌孙是在前汉文帝时代驱逐了从今甘肃省内逃到这里的大月氏族 而据有该地的。而大月氏又驱逐了在此之前的塞族据有该地。关于 塞和大月氏属于什么人种的问题,虽尚未确定:但一般认为属亚利 安种。果如是,则大月氏在记录之初人种分布上,作为亚利安种东 进的先锋,竞一直进入甘肃省地方了。 1《汉书·西域传》乌孙条注。 2 W.Kingsmill:《公元前中国与西域及邻近国家的交流》,载RAS,N.S,Vol.XTV, 1882,p.74-104:Charpentier:《吐火罗人的人种位置》,载ZDMG,71Bde, 1917,S.347-388
第二章 西域的民族 现据有西域亦即中央亚细亚的民族为突厥人(如突厥斯坦一名 所表示的),但古代未必如此。从前章所述中亚属于三个区域考之, 天山北路到谢米列契(七河)一带,从记录时代之初起是否就是突 厥人的居住地,这一点还不易判定。据前汉到南北朝(即公元前 2 世纪到公元 5 世纪)的记载,今伊犁、天山北部山谷之间的地方为 乌孙族所据有,他们与中国有密切的关系。此族之语言依现存资料 认为是属突厥语。但唐代颜师古谈到乌孙的容貌时说;“乌孙于西域 诸戎,其形最异,今之胡人,青眼赤须,状类猕猴者,本其种也。” 1据此,不能一概断定为突厥人。颜师古所用胡人这一名称,当时无 疑是指以今萨马尔罕(Samarkand)为中心的粟特(Sogdiana)地方 的人,即伊兰人种。所谓“青眼赤须、状类猕猴”,正是这一人种风 貌的描写,而不是指突厥人。类似的例子尚见于他处。如现为突厥 种之一的吉尔吉斯(Kirghiz)族(汉代称坚昆、鬲昆,南北朝时称 契骨、居勿、结骨,唐代称纥扢斯、黠戛斯。其语言至少在唐代已 突厥化),关于其容貌,《唐书·回鹘传下》附《黠戛斯》条中说: “人皆长大,白发、皙面、绿履,以黑发为不祥,黑瞳者必曰〔李〕 陵苗裔也。”这也决不是突厥人的容貌,而应为伊兰人的种族特征。 突厥族一般传说以狼为族祖。唐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卷四中也说 “坚昆部非狼种”,也就是说黠戛斯人非突厥种。根据这些记载,唐 代据有今叶尼塞河上游明显操突厥语的黠戛斯族,本来不是突厥种, 而是一种亚利安种,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才突厥化的。颜师古关于 乌孙的记载可能不是简单的臆说,有何根据我们无从知道了。欧洲 学者中有人认为乌孙当是古代记录中属亚利安种的游牧民 Assi 族2。 而乌孙是在前汉文帝时代驱逐了从今甘肃省内逃到这里的大月氏族 而据有该地的。而大月氏又驱逐了在此之前的塞族据有该地。关于 塞和大月氏属于什么人种的问题,虽尚未确定;但一般认为属亚利 安种。果如是,则大月氏在记录之初人种分布上,作为亚利安种东 进的先锋,竟一直进入甘肃省地方了。 1 《汉书·西域传》乌孙条注。 2 W.Kingsmill:《公元前中国与西域及邻近国家的交流》,载JRAS,N.S,Vol.XIV, 1882,p.74-104;Charpentier:《吐火罗人的人种位置》,载 ZDMG,71 Bde, 1917,S.347-388.

谢米列契(七河)省南部一带从汉代起就住有称做康居的部族, 其势力及于粟特地方。依其生活状态和语言,也认为是属突厥种。 关于此族没有象乌孙和黠戛斯那样有关于容貌特征的记载。把它说 成是属突厥族于记录上不是什么不合适的。但语言、风俗、生活情 态的相同或近似,并不是说人种也完全相同(如前述黠戛斯人的情 况)。时代越在后,人种混合的程度越厉害,一般已不存在纯粹的种 族类型,也不能以今日世界人种知识来细致区分古代民族。康居何 时据有该地也不清楚。再有,是否当这一带住有如康居族时发生了 亚利安系种族的入侵,反之,或当亚利安种族扩张时发生了如康居 的突厥种族的侵人,这些都属于史前的范围,现在难以判定。总之, 当此地有记录之初,从天山北路到谢米列契一带,就住有可认为是 属于亚利安系和突厥系的游牧种族。之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到前 汉武帝时代(约公元前130年左右)大月氏又往西南方向迁移。代 之而起的是突厥语族的乌孙据有该地,直到南北朝时期,无疑地, 纯粹突厥种族占有此地应是以后的事。 其次,关于天山南路的民族,由于对该地进行发掘所得语言、 绘画、骨骼、头盖骨等材料的研究,至迟在公元前后主要是为亚利 安种族所居住,这是没有疑问的。 最后,关于锡尔、阿姆两河之间的地方,即其中央有名的索格 底亚那沃地的居民,这里有必要略微深入地谈一谈。上一世纪中叶 学术界曾风行一种认为该地的某一地域是亚利安种族原住地的学说 '。现在尚有一部分人坚持此说。现简述该学说何时、基于何种理由、 由何人所提倡的过程。 由于欧洲比较语言学的发达,当18世纪末,欧洲学者热心研究 梵语(印度古语)、赞德语(波斯古语)等,从而发现它们与希腊语 拉丁语、日耳曼语、凯尔特语之间在词汇和语法方而有许多相同点 1786年琼斯(William Jones)提出这种相同点出自共同根源的学说, 实为此学说奠下不可动摇的基石。1833年后,德国语言学家鲍朴 (Framz Bopp)刊行了梵语、赞德语、希腊语、拉丁语、立陶宛语 哥特语、古代斯拉夫语、德语等比较语法,建立了印欧比较语言学 Asiatic Researches《亚细亚研究)Tl,P42以及Benfey,Geschichte der Sprachwissenschaft,《语言学史》,1869,p.348. 2 Vergleichend Grammatik des Sanskrit,Zent,Griechischen,Lateinischen, Lathanischen,Gothischen und Deutschen(梵语、赞德语、希腊语、拉丁语、立 陶宛语、哥特语及德语比较语法)
谢米列契(七河)省南部一带从汉代起就住有称做康居的部族, 其势力及于粟特地方。依其生活状态和语言,也认为是属突厥种。 关于此族没有象乌孙和黠戛斯那样有关于容貌特征的记载。把它说 成是属突厥族于记录上不是什么不合适的。但语言、风俗、生活情 态的相同或近似,并不是说人种也完全相同(如前述黠戛斯人的情 况)。时代越在后,人种混合的程度越厉害,一般已不存在纯粹的种 族类型,也不能以今日世界人种知识来细致区分古代民族。康居何 时据有该地也不清楚。再有,是否当这一带住有如康居族时发生了 亚利安系种族的入侵,反之,或当亚利安种族扩张时发生了如康居 的突厥种族的侵人,这些都属于史前的范围,现在难以判定。总之, 当此地有记录之初,从天山北路到谢米列契一带,就住有可认为是 属于亚利安系和突厥系的游牧种族。之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到前 汉武帝时代(约公元前 130 年左右)大月氏又往西南方向迁移。代 之而起的是突厥语族的乌孙据有该地,直到南北朝时期,无疑地, 纯粹突厥种族占有此地应是以后的事。 其次,关于天山南路的民族,由于对该地进行发掘所得语言、 绘画、骨骼、头盖骨等材料的研究,至迟在公元前后主要是为亚利 安种族所居住,这是没有疑问的。 最后,关于锡尔、阿姆两河之间的地方,即其中央有名的索格 底亚那沃地的居民,这里有必要略微深入地谈一谈。上一世纪中叶 学术界曾风行一种认为该地的某一地域是亚利安种族原住地的学说 1。现在尚有一部分人坚持此说。现简述该学说何时、基于何种理由、 由何人所提倡的过程。 由于欧洲比较语言学的发达,当 18 世纪末,欧洲学者热心研究 梵语(印度古语)、赞德语(波斯古语)等,从而发现它们与希腊语、 拉丁语、日耳曼语、凯尔特语之间在词汇和语法方而有许多相同点。 1786 年琼斯(William Jones)提出这种相同点出自共同根源的学说, 实为此学说奠下不可动摇的基石。1833 年后,德国语言学家鲍朴 (Framz Bopp)刊行了梵语、赞德语、希腊语、拉丁语、立陶宛语、 哥特语、古代斯拉夫语、德语等比较语法2,建立了印欧比较语言学 1 Asiatic Researches《亚细亚研究》T.1,P.422 以及 Benfey,Geschichte der Sprachwissenschaft,《语言学史》,1869,p.348. 2 Vergleichend Grammatik des Sanskrit,Zent,Griechischen,Lateinischen, Lathanischen,Gothischen und Deutschen(梵语、赞德语、希腊语、拉丁语、立 陶宛语、哥特语及德语比较语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