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 中国传统的图书目录,例分经史子集四部,以经部居首,而十三经为其 冠冕。晚清以来大家可读的(书目答问》,开端为经部“正经正注”,第一部 书就是《十三经注疏》,并特别标明:“此为诵读定本,程试功令,说经根柢” 足见其地位的重要。由于《十三经注疏》本身的价值,以及其在历史上所有 的巨大彩响,这部书运今仍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典籍。 十三经的产生形成,有着非常长远的源流历程。《诗》、《书》等经的渊 源,可以追溯到上古。周代尚文,当时教育已包括(诗)、《书)、(礼)、《乐) 如《国语·楚语》记戴,春秋中叶楚庄王定太子傅,大夫中叔时回答王问,提 到“教之春秋”、“教之诗”、“教之礼”、“教之乐”、“教之训典”等等,即涵有 《诗》、《书》、(礼)、《乐》及《春秋》等方面的内容。春秋晚年,孔子立私学,以 《诗》《书)、〈礼)、《乐》教弟子,经的体系进一步莫定。 史籍传述孔子曹修纂六经,对此学者顿有争论,但六经之称在战国时 确已存在。《庄子·天运篇》我:“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 《乐》、《易》、(春秋》六经”,语属寓言,很多人不相信。不久前湖北荆门郭店 楚萋出土竹简(六德),篇中说:“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请(礼》 《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所讲六经次第与《庄子》全 同,证明战国中叶实有这种说法。参看〈苟子·劝学篇》所论:“学恶乎始? 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满经,终乎读礼”,不难如道经在社会教育中具有 明显的作用。 《汉书·艺文志》称周衰而(乐》亡,后来应劲、沈约等则将(乐经》之亡归 罪于暴泰。无论怎样,汉代只有五经立于学官。到唐代,《礼》有《周礼》 (仪礼)、(礼记》,《春秋》有《左传、(公羊》、《谷梁》,这样是十二经:宋明又 增加《孟子》,于是定型为十三经。宋代曹经有人主张把(大戴礼记》也收进 来,合为十四经,但没有得到公认。 《十三经注疏》的注绝大多数是汉晋古注,而且一散说都是现在我们能 看到的最早的完整注本,疏也皆成于唐宋,因此特珠宝黄。不过在科举八 股时代,(注疏》实际没有得到普遮的重视。明代永乐时修成以宋元理学家 言为本的(五经大全》,试士经义全用宋元人注,使是所谓明监本五经,(易》 用朱子(本义》,(书)用蔡沈(集传),《诗》用朱子(《集传),(春秋)用胡安国 传,(礼记》用陈游(集说》,以致多数文人对《注琉》束而不观,甚至在个别人 引用《注疏)时群起惊讶。直到清代汉学之风兴起,《十三经注疏)才为学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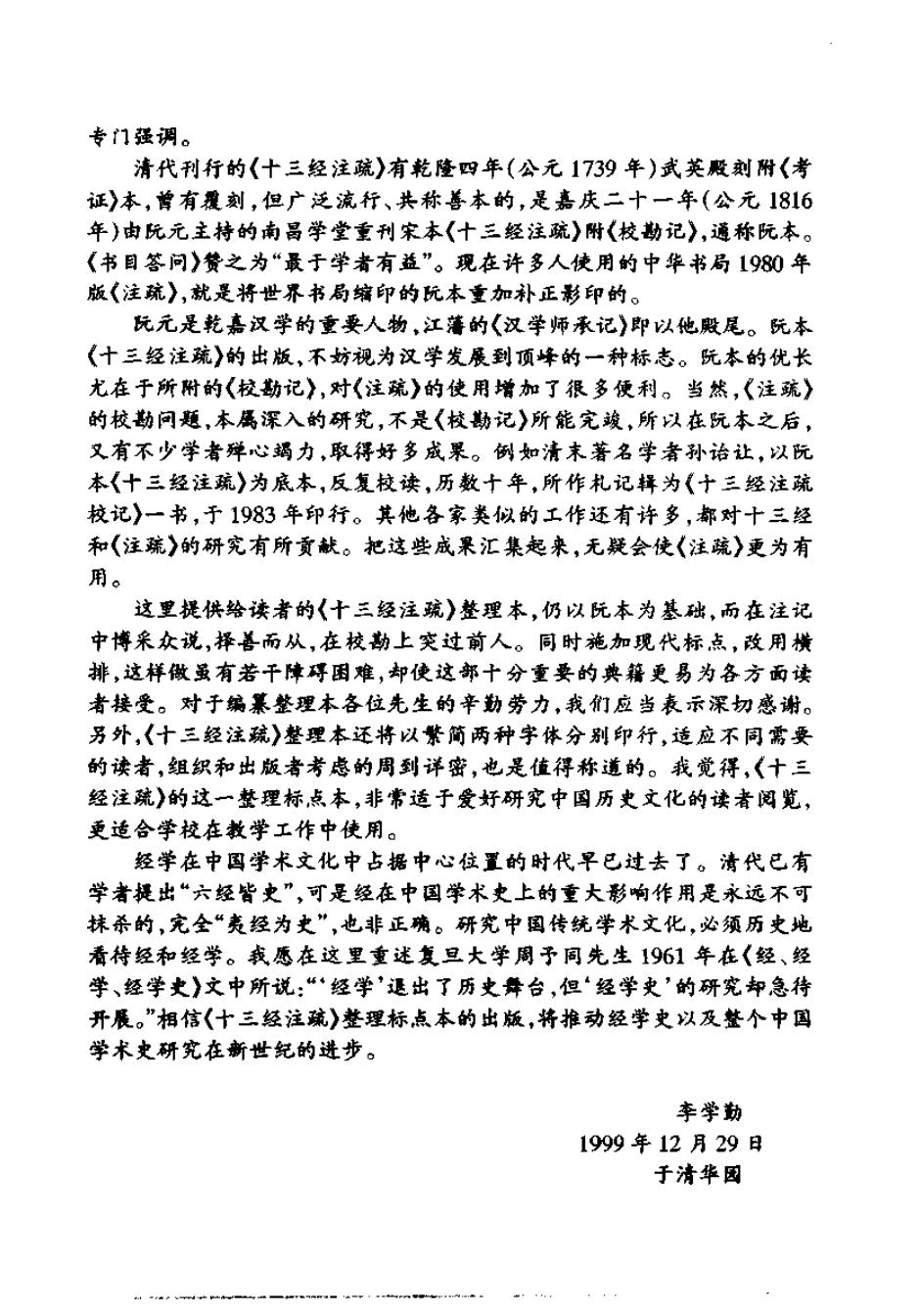
专1强调。 清代刊行的(十三经注疏)有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武英殿刘附(考 证)本,曾有覆刻,但广泛流行、共称善本的,是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 年)由阮元主持的南昌学堂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道称阮本。 (书目答问》赞之为“最于学者有益”。现在许多人使用的中华书局1980年 版《注疏》,就是将世界书局缩印的阮本重加补正影印的。 阮元是乾嘉汉学的重要人物,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即以他殿尾。阮本 《十三经注疏》的出版,不妨视为汉学发展到顶峰的一种标志。阮本的优长 尤在于所附的(校勘记》,对(注疏》的使用增加了很多便利。当然,《注疏》 的校勘问题,本属深入的研究,不是《校勘记》所能完竣,所以在阮本之后, 又有不少学者弹心竭力,取得好多成果。例如清末著名学者孙诒让,以阮 本《十三经注疏》为底本,反复校读,历数十年,所作札记择为《十三经注疏 校记》一书,于1983年印行。其他各家类似的工作还有许多,都对十三经 和(注疏》的研究有所贡献。把这些成果汇集起来,无疑会使《注疏》更为有 用。 这里提供给读者的《十三经注琉)整理本,仍以阮本为基础,而在注记 中博采众说,择善而从,在校劫上突过前人。同时施加现代标点,改用横 排,这样做虽有若干障碍困难,却使这部十分重要的典籍更易为各方而读 者接受。对于编慕整理本各位先生的辛勤劳力,我们应当表示深切感谢。 另外,〈十三经注疏》整理本还将以繁简两种宇体分别印行,适应不同需要 的读者,组织和出版者考总的周到详密,也是值得称道的。我觉得,〈十三 经注疏》的这一整理标,点本,非常适于爱好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读者阅览, 更适合学校在教学工作中使用。 经学在中国学术文化中占据中心位里的时代早已过去了。清代已有 学者提出“六经皆史”,可是经在中国学术史上的重大彩响作用是永远不可 株杀的,完全“夷经为史”,也非正隋。研究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必须历史地 看特经和经学。我愿在这里重述复旦大学周予同先生1961年在(经、经 学、经学史》文中所说:“·经学'退出了历史舞台,但·经学史'的研究却急待 开展。”相信(十三经注疏》整理标,点本的出版,将推动经学史以及整个中国 学术史研究在斯世纪的进步。 李学勤 1999年12月29日 于清华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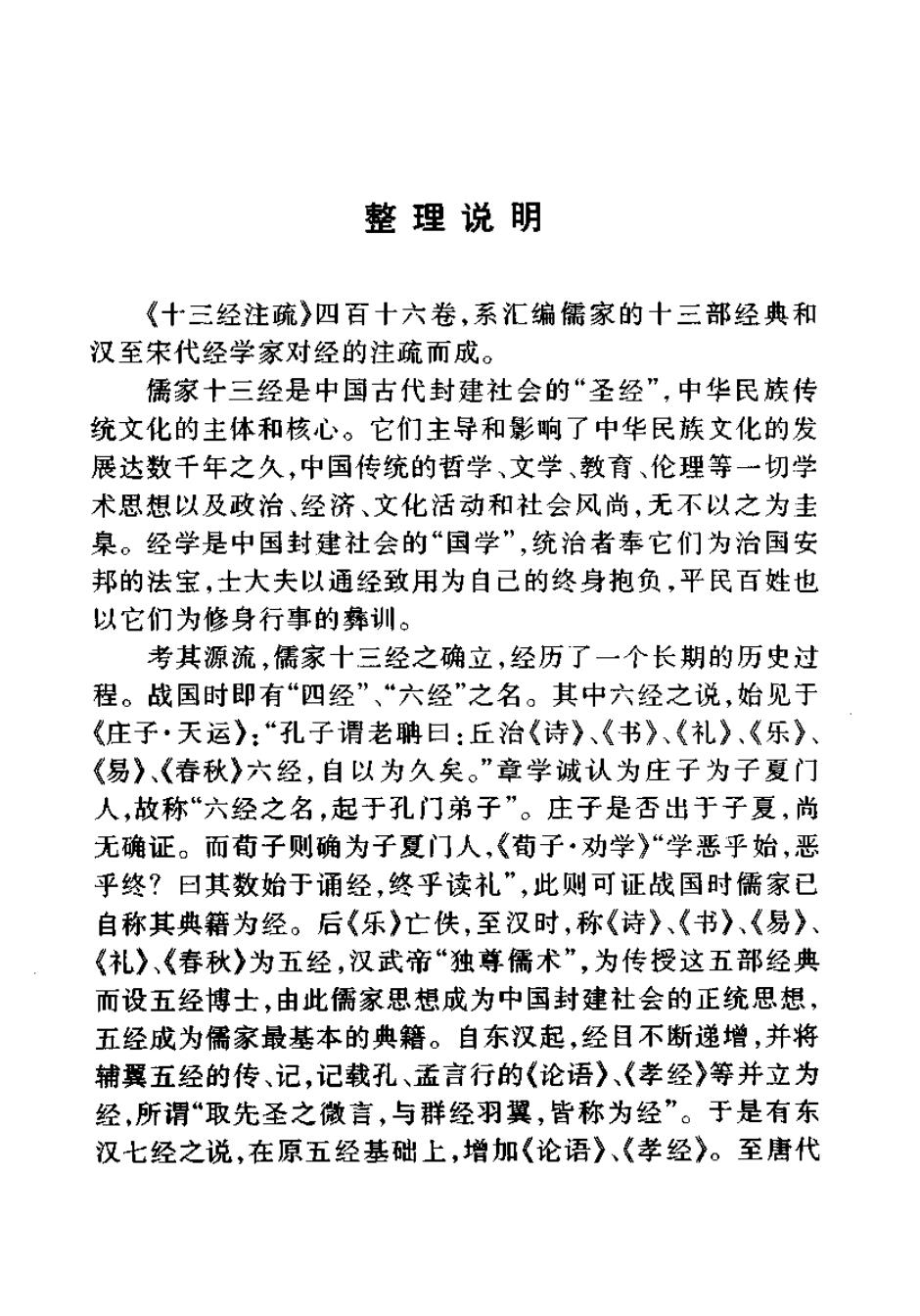
整理说明 《十三经注疏》四百十六卷,系汇编儒家的十三部经典和 汉至宋代经学家对经的注疏而成。 儒家十三经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圣经”,中华民族传 统文化的主体和核心。它们主导和影响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发 展达数千年之久,中国传统的哲学、文学、教育、伦理等一切学 术思想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和社会风尚,无不以之为圭 臬。经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国学”,统治者奉它们为治国安 邦的法宝,士大夫以通经致用为自己的终身抱负,平民百姓也 以它们为修身行事的彝训。 考其源流,儒家十三经之确立,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 程。战国时即有“四经”、“六经”之名。其中六经之说,始见于 《庄子·天运》:“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 《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章学诚认为庄子为子夏门 人,故称“六经之名,起于孔门弟子”。庄子是否出于子夏,尚 无确证。而荀子则确为子夏门人,《荀子·劝学》“学恶乎始,恶 乎终?曰其数始于诵经,终乎读礼”,此则可证战国时儒家已 自称其典籍为经。后《乐》亡佚,至汉时,称《诗》、《书》、《易》 《礼》、《春秋》为五经,汉武帝“独尊儒术”,为传授这五部经典 而设五经博士,由此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五经成为儒家最基本的典籍。自东汉起,经目不断递增,并将 辅翼五经的传、记,记载孔、孟言行的《论语》、《孝经》等并立为 经,所谓“取先圣之微言,与群经羽翼,皆称为经”。于是有东 汉七经之说,在原五经基础上,增加《论语》、《孝经》。至唐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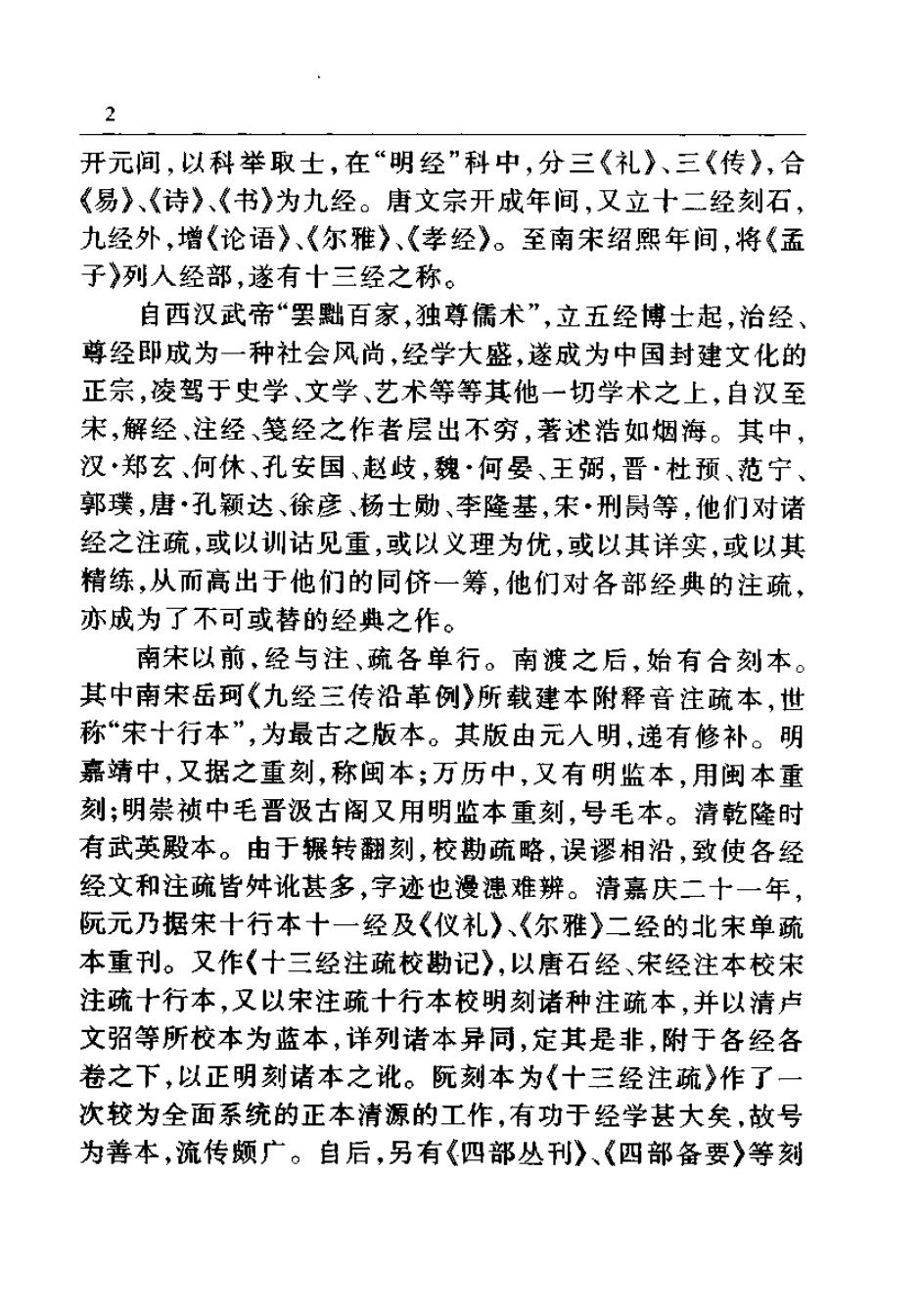
2 开元间,以科举取士,在“明经”科中,分三《礼》、三《传》,合 《易》、《诗》、《书》为九经。唐文宗开成年间,又立十二经刻石, 九经外,增《论语》、《尔雅》、《孝经》。至南宋绍熙年间,将《孟 子》列人经部,遂有十三经之称。 自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起,治经、 尊经即成为一种社会风尚,经学大盛,遂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 正宗,凌驾于史学、文学、艺术等等其他一切学术之上,自汉至 宋,解经、注经、笺经之作者层出不穷,著述浩如烟海。其中 汉·郑玄、何休、孔安国、赵歧,魏·何晏、王弼,晋·杜预、范宁、 郭璞,唐·孔颖达、徐彦、杨士勋、李隆基,宋·刑昺等,他们对诸 经之注疏,或以训诂见重,或以义理为优,或以其详实,或以其 精练,从而高出于他们的同侪一筹,他们对各部经典的注疏, 亦成为了不可或替的经典之作。 南宋以前,经与注、疏各单行。南渡之后,始有合刻本。 其中南宋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所载建本附释音注疏本,世 称“宋十行本”,为最古之版本。其版由元人明,递有修补。明 嘉靖中,又据之重刻,称闽本;万历中,又有明监本,用闽本重 刻;明崇祯中毛晋汲古阁又用明监本重刻,号毛本。清乾隆时 有武英殿本。由于辗转翻刻,校勘疏略,误谬相沿,致使各经 经文和注疏皆舛讹甚多,字迹也漫漶难辨。清嘉庆二十一年, 阮元乃据宋十行本十一经及《仪礼》、《尔雅》二经的北宋单疏 本重刊。又作《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以唐石经、宋经注本校宋 注疏十行本,又以宋注疏十行本校明刻诸种注疏本,并以清卢 文弨等所校本为蓝本,详列诸本异同,定其是非,附于各经各 卷之下,以正明刻诸本之讹。阮刻本为《十三经注疏》作了一 次较为全面系统的正本清源的工作,有功于经学甚大矣,故号 为善本,流传颇广。自后,另有《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等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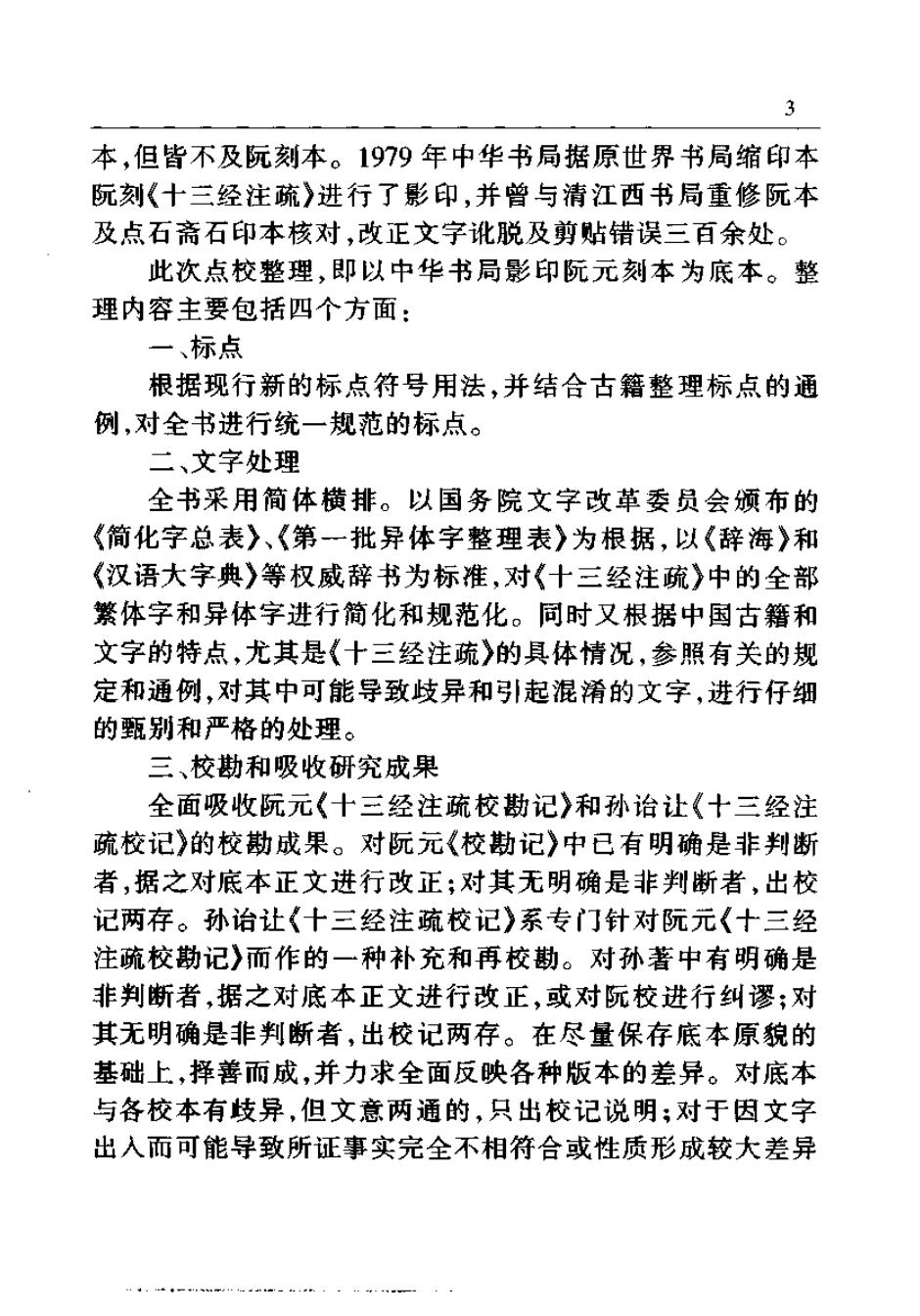
3 本,但皆不及阮刻本。1979年中华书局据原世界书局缩印本 阮刻《十三经注疏》进行了影印,并曾与清江西书局重修阮本 及点石斋石印本核对,改正文字讹脱及剪贴错误三百余处。 此次点校整理,即以中华书局影印阮元刻本为底本。整 理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一、标点 根据现行新的标点符号用法,并结合古籍整理标点的通 例,对全书进行统一规范的标点。 二、文字处理 全书采用简体横排。以国务院文字改革委员会领布的 《简化字总表》、《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为根据,以《辞海》和 《汉语大字典》等权威辞书为标准,对《十三经注疏)中的全部 繁体字和异体字进行简化和规范化。同时又根据中国古籍和 文字的特点,尤其是《十三经注疏》的具体情况,参照有关的规 定和通例,对其中可能导致歧异和引起混淆的文字,进行仔细 的甄别和严格的处理。 三、校勘和吸收研究成果 全面吸收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和孙诒让《十三经注 疏校记》的校勘成果。对阮元《校勘记》中已有明确是非判断 者,据之对底本正文进行改正;对其无明确是非判断者,出校 记两存。孙诒让《十三经注疏校记》系专门针对阮元《十三经 注疏校勘记》而作的一种补充和再校勘。对孙著中有明确是 非判断者,据之对底本正文进行改正,或对阮校进行纠谬;对 其无明确是非判断者,出校记两存。在尽量保存底本原貌的 基础上,择善而成,并力求全面反映各种版本的差异。对底本 与各校本有歧异,但文意两通的,只出校记说明;对于因文字 出入而可能导致所证事实完全不相符合或性质形成较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