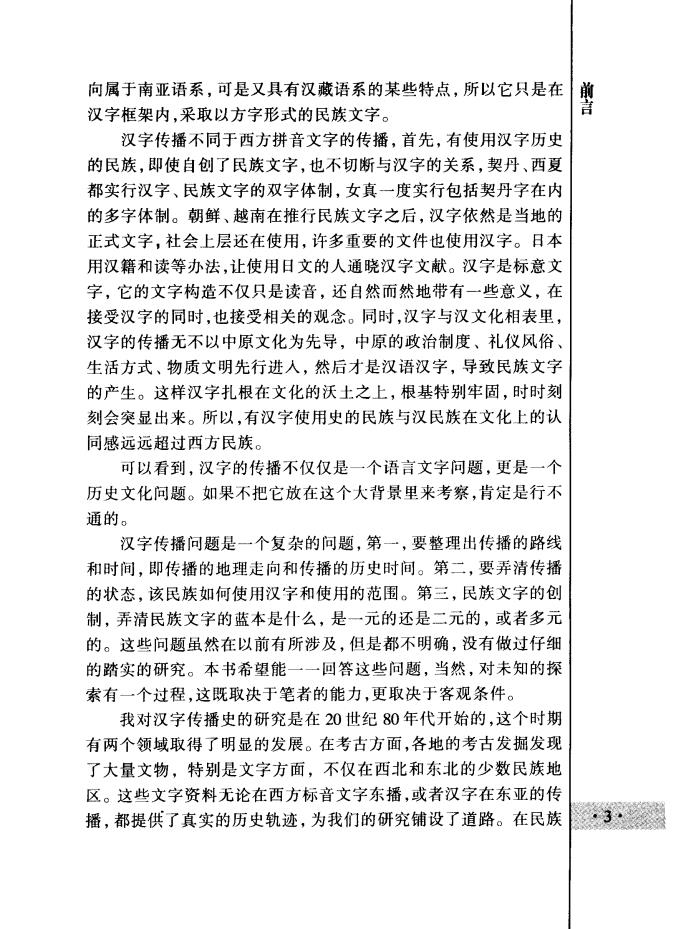
向属于南亚语系,可是又具有汉藏语系的某些特点,所以它只是在 前言 汉字框架内,采取以方字形式的民族文字。 汉字传播不同于西方拼音文字的传播,首先,有使用汉字历史 的民族,即使自创了民族文字,也不切断与汉字的关系,契丹、西夏 都实行汉字、民族文字的双字体制,女真一度实行包括契丹字在内 的多字体制。朝鲜、越南在推行民族文字之后,汉字依然是当地的 正式文字,社会上层还在使用,许多重要的文件也使用汉字。日本 用汉籍和读等办法,让使用日文的人通晓汉字文献。汉字是标意文 字,它的文字构造不仅只是读音,还自然而然地带有一些意义,在 接受汉字的同时,也接受相关的观念。同时,汉字与汉文化相表里, 汉字的传播无不以中原文化为先导,中原的政治制度、礼仪风俗、 生活方式、物质文明先行进人,然后才是汉语汉字,导致民族文字 的产生。这样汉字扎根在文化的沃土之上,根基特别牢固,时时刻 刻会突显出来。所以,有汉字使用史的民族与汉民族在文化上的认 同感远远超过西方民族。 可以看到,汉字的传播不仅仅是一个语言文字问题,更是一个 历史文化问题。如果不把它放在这个大背景里来考察,肯定是行不 通的。 汉字传播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第一,要整理出传播的路线 和时间,即传播的地理走向和传播的历史时间。第二,要弄清传播 的状态,该民族如何使用汉字和使用的范围。第三,民族文字的创 制,弄清民族文字的蓝本是什么,是一元的还是二元的,或者多元 的。这些问题虽然在以前有所涉及,但是都不明确,没有做过仔细 的踏实的研究。本书希望能一一回答这些问题,当然,对未知的探 索有一个过程,这既取决于笔者的能力,更取决于客观条件。 我对汉字传播史的研究是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这个时期 有两个领域取得了明显的发展。在考古方面,各地的考古发掘发现 了大量文物,特别是文字方面,不仅在西北和东北的少数民族地 区。这些文字资料无论在西方标音文字东播,或者汉字在东亚的传 播,都提供了真实的历史轨迹,为我们的研究铺设了道路。在民族
向属于南亚语系,可是又具有汉藏语系的某些特点,所以它只是在 前 公 汉字框架内,采取以方字形式的民族文字。 曰 汉字传播不同于西方拼音文字的传播,首先,有使用汉字历史 的民族,即使 自创了民族文字,也不切断与汉字的关系,契丹、西夏 都实行汉字、民族文字的双字体制,女真一度实行包括契丹字在内 的多字体制。朝鲜、越南在推行民族文字之后,汉字依然是当地的 正式文字,社会上层还在使用,许多重要的文件也使用汉字。日本 用汉籍和读等办法,让使用 日文的人通晓汉字文献。汉字是标意文 字,它的文字构造不仅只是读音,还自然而然地带有一些意义,在 接受汉字的同时,也接受相关的观念。同时,汉字与汉文化相表里, 汉字的传播无不以中原文化为先导,中原的政治制度、礼仪风俗、 生活方式 、物质文明先行进人,然后才是汉语汉字,导致民族文字 的产生。这样汉字扎根在文化的沃土之上,根基特别牢固,时时刻 刻会突显出来。所以,有汉字使用史的民族与汉民族在文化上的认 同感远远超过西方 民族。 可以看到 ,汉字的传播不仅仅是一个语言文字问题 ,更是一个 历史文化问题。如果不把它放在这个大背景里来考察,肯定是行不 通的。 汉字传播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第一,要整理出传播的路线 和时间,即传播的地理走向和传播的历史时间。第二,要弄清传播 的状态,该民族如何使用汉字和使用的范围。第三,民族文字的创 制,弄清民族文字的蓝本是什么,是一元的还是二元的,或者多元 的。这些问题虽然在以前有所涉及,但是都不明确,没有做过仔细 的踏实的研究。本书希望能一一回答这些问题,当然,对未知的探 索有一个过程,这既取决于笔者的能力,更取决于客观条件。 我对汉字传播史的研究是在 20世纪 80年代开始的,这个时期 有两个领域取得了明显的发展。在考古方面,各地的考古发掘发现 了大量文物,特别是文字方面,不仅在西北和东北的少数民族地 霭:4ANkbT39CT4} AW19}- MJGWit}AY9L.A)}黯, )VR1f4In} .TOf. 9} ,AMiWRaT frMA-}- aAMK*A介熟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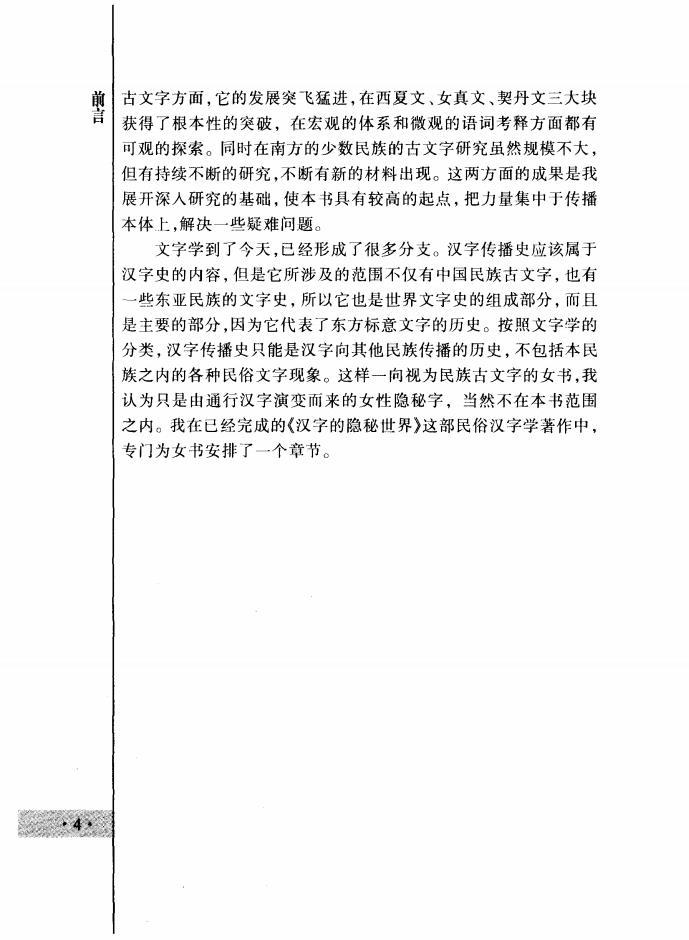
曾 古文字方面,它的发展突飞猛进,在西夏文、女真文、契丹文三大块 获得了根本性的突破,在宏观的体系和微观的语词考释方面都有 可观的探索。同时在南方的少数民族的古文字研究虽然规模不大, 但有持续不断的研究,不断有新的材料出现。这两方面的成果是我 展开深人研究的基础,使本书具有较高的起点,把力量集中于传播 本体上,解决一些疑难问题。 文字学到了今天,已经形成了很多分支。汉字传播史应该属于 汉字史的内容,但是它所涉及的范围不仅有中国民族古文字,也有 一些东亚民族的文字史,所以它也是世界文字史的组成部分,而且 是主要的部分,因为它代表了东方标意文字的历史。按照文字学的 分类,汉字传播史只能是汉字向其他民族传播的历史,不包括本民 族之内的各种民俗文字现象。这样一向视为民族古文字的女书,我 认为只是由通行汉字演变而来的女性隐秘字,当然不在本书范围 之内。我在已经完成的《汉字的隐秘世界》这部民俗汉字学著作中, 专门为女书安排了一个章节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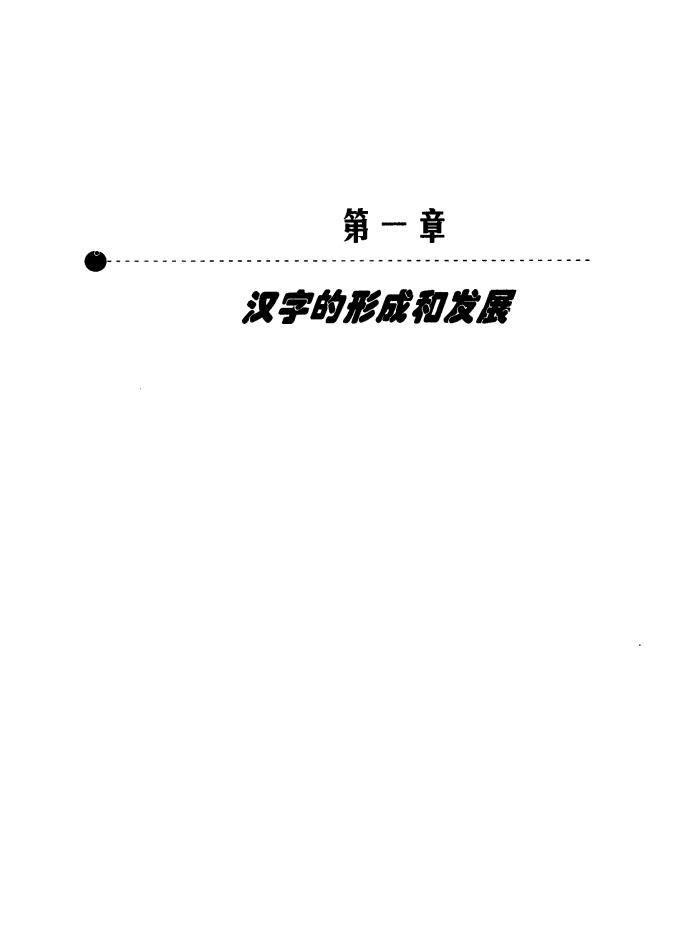
第一章 汉字的形成和发展
第一章 .-----------------------------------------一 娜乒成袱毖藏裁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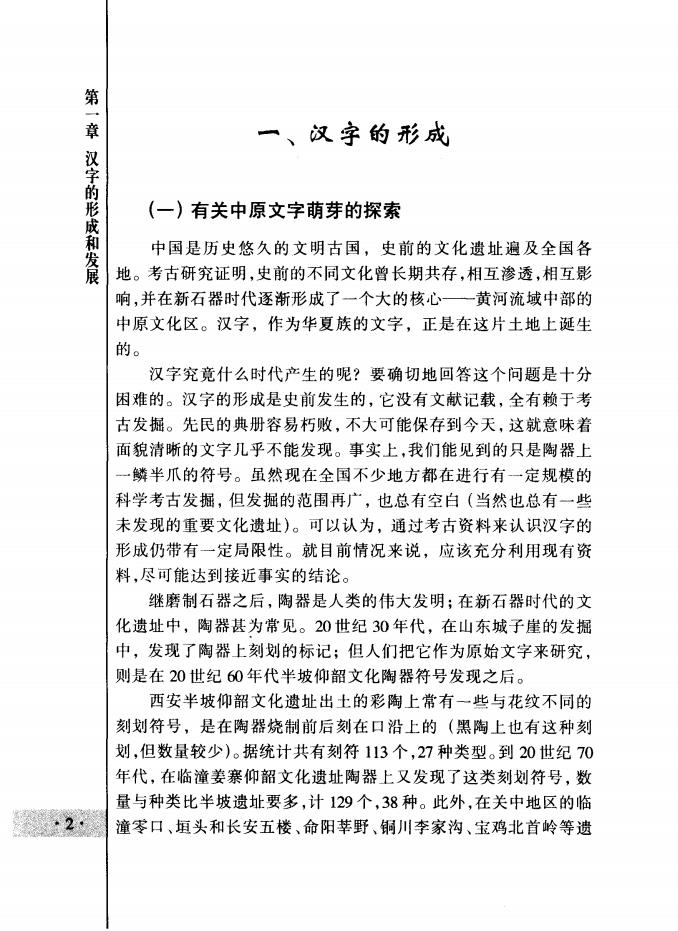
第一章 一、汉字的形成 汉字的形成和发展 (一)有关中原文字萌芽的探索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史前的文化遗址遍及全国各 地。考古研究证明,史前的不同文化曾长期共存,相互渗透,相互影 响,并在新石器时代逐渐形成了一个大的核心一黄河流域中部的 中原文化区。汉字,作为华夏族的文字,正是在这片土地上诞生 的。 汉字究竞什么时代产生的呢?要确切地回答这个问题是十分 困难的。汉字的形成是史前发生的,它没有文献记载,全有赖于考 古发掘。先民的典册容易朽败,不大可能保存到今天,这就意味着 面貌清晰的文字几乎不能发现。事实上,我们能见到的只是陶器上 一鳞半爪的符号。虽然现在全国不少地方都在进行有一定规模的 科学考古发掘,但发掘的范围再广,也总有空白(当然也总有一些 未发现的重要文化遗址)。可以认为,通过考古资料来认识汉字的 形成仍带有一定局限性。就目前情况来说,应该充分利用现有资 料,尽可能达到接近事实的结论。 继磨制石器之后,陶器是人类的伟大发明;在新石器时代的文 化遗址中,陶器甚为常见。20世纪30年代,在山东城子崖的发掘 中,发现了陶器上刻划的标记;但人们把它作为原始文字来研究, 则是在20世纪60年代半坡仰韶文化陶器符号发现之后。 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上常有一些与花纹不同的 刻划符号,是在陶器烧制前后刻在口沿上的(黑陶上也有这种刻 划,但数量较少)。据统计共有刻符113个,27种类型。到20世纪70 年代,在临潼姜寨仰韶文化遗址陶器上又发现了这类刻划符号,数 量与种类比半坡遗址要多,计129个,38种。此外,在关中地区的临 潼零口、垣头和长安五楼、命阳莘野、铜川李家沟、宝鸡北首岭等遗
一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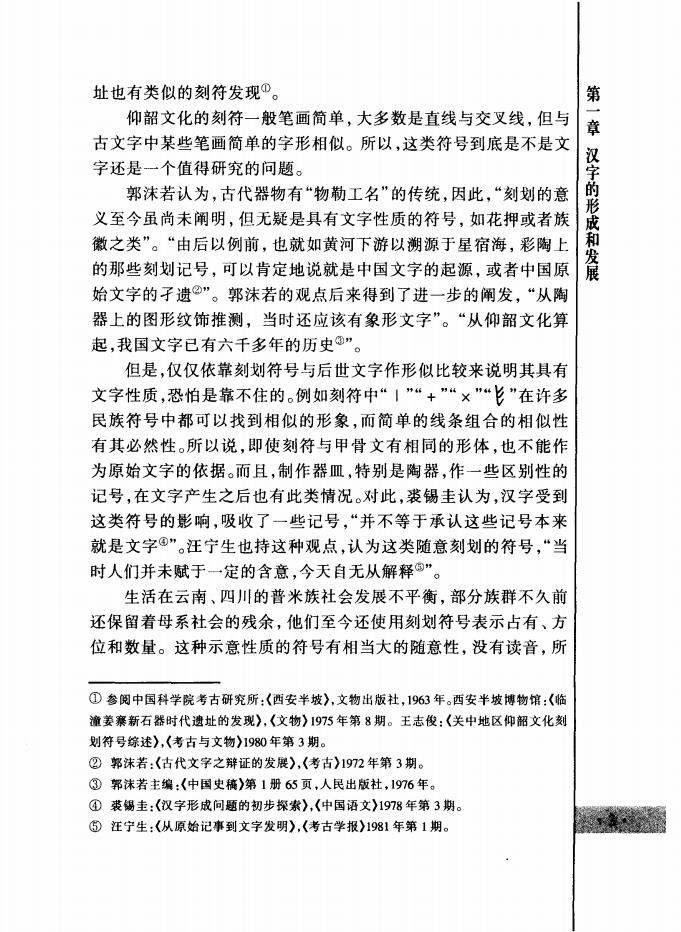
址也有类似的刻符发现①。 第 仰韶文化的刻符一般笔画简单,大多数是直线与交叉线,但与 章 古文字中某些笔画简单的字形相似。所以,这类符号到底是不是文 字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字 郭沫若认为,古代器物有“物勒工名”的传统,因此,“刻划的意 形 义至今虽尚未阐明,但无疑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如花押或者族 成 徽之类”。“由后以例前,也就如黄河下游以溯源于星宿海,彩陶上 和 的那些刻划记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 发展 始文字的子遗”。郭沫若的观点后来得到了进一步的阐发,“从陶 器上的图形纹饰推测,当时还应该有象形文字”。“从仰韶文化算 起,我国文字已有六千多年的历史③”。 但是,仅仅依靠刻划符号与后世文字作形似比较来说明其具有 文字性质,恐怕是靠不住的。例如刻符中“|”“+”“×”“它”在许多 民族符号中都可以找到相似的形象,而简单的线条组合的相似性 有其必然性。所以说,即使刻符与甲骨文有相同的形体,也不能作 为原始文字的依据。而且,制作器皿,特别是陶器,作一些区别性的 记号,在文字产生之后也有此类情况。对此,裘锡圭认为,汉字受到 这类符号的影响,吸收了一些记号,“并不等于承认这些记号本来 就是文字®”。汪宁生也持这种观点,认为这类随意刻划的符号,“当 时人们并未赋于一定的含意,今天自无从解释⑤”。 生活在云南、四川的普米族社会发展不平衡,部分族群不久前 还保留着母系社会的残余,他们至今还使用刻划符号表示占有、方 位和数量。这种示意性质的符号有相当大的随意性,没有读音,所 ①参阅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西安半坡博物馆:《临 潼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文物》1975年第8期。王志俊:《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刻 划符号综述》,(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 ②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考古》1972年第3期。 ③郭袜若主编:《中国史稿)第1册65页,人民出版社,1976年。 ①裘锡圭:(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素》,(中国语文》1978年第3期。 ⑤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
址也有类似的刻符发现①。 第 仰韶文化的刻符一般笔画简单,大多数是直线与交叉线,但与 孟 i"rpwI,- ruHJwiIli 12A-Gmuiw=r-’八少从A=丑ol}一人~;}x ,‘二, 章 吏字还齐舍是中一纂个些值筹得豆研草究兽的丝问炭题形。相似。所以,这类符号到底是不是文汉学 郭沫若认为,古代器物有“物勒工名”的传统,因此,“刻划的意 鲍 义至琴虽高呆雨斌适芜疑是真着夏李社益晶石荀丽花神轰奢蔽装 徽之类”。“由后以例前,也就如黄河下游以溯源于星宿海,彩陶上 和 的那些刻划记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 辰 始文字的孑遗②”。郭沫若的观点后来得到了进一步的阐发,“从陶 器上的图形纹饰推测,当时还应该有象形文字”。“从仰韶文化算 起,我国文字已有六千多年的历史③”。 但是,仅仅依靠刻划符号与后世文字作形似比较来说明其具有 文字性质,恐怕是靠不住的。例如刻符中“I”“+”“xI”在许多 民族符号中都可以找到相似的形象,而简单的线条组合的相似性 有其必然性。所以说,即使刻符与甲骨文有相同的形体 ,也不能作 为原始文字的依据。而且,制作器皿,特别是陶器,作一些区别性的 记号,在文字产生之后也有此类情况。对此 ,裘锡圭认为,汉字受到 这类符号的影响,吸收了一些记号,“并不等于承认这些记号本来 就是文字④”。汪宁生也持这种观点,认为这类随意刻划的符号,“当 时人们并未赋于一定的含意,今天自无从解释⑤”。 生活在云南 、四川的普米族社会发展不平衡,部分族群不久前 还保留着母系社会的残余,他们至今还使用刻划符号表示占有、方 位和数量。这种示意性质的符号有相当大的随意性,没有读音,所 ① 参阅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西安半坡博物馆:(临 渔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文物》1975年第8期。王志俊:《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刻 划符号综述》,(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 ② 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考古)1972年第3期。 ③ 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1册65页,人民出版社,1976年。 ④ 裘锡圭:(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索》.《中国语文))1978年第3期。 一 ⑤ 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考古学报))1981年第 1期。 腹瑟粼覆黝粼瓣翼1襄操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