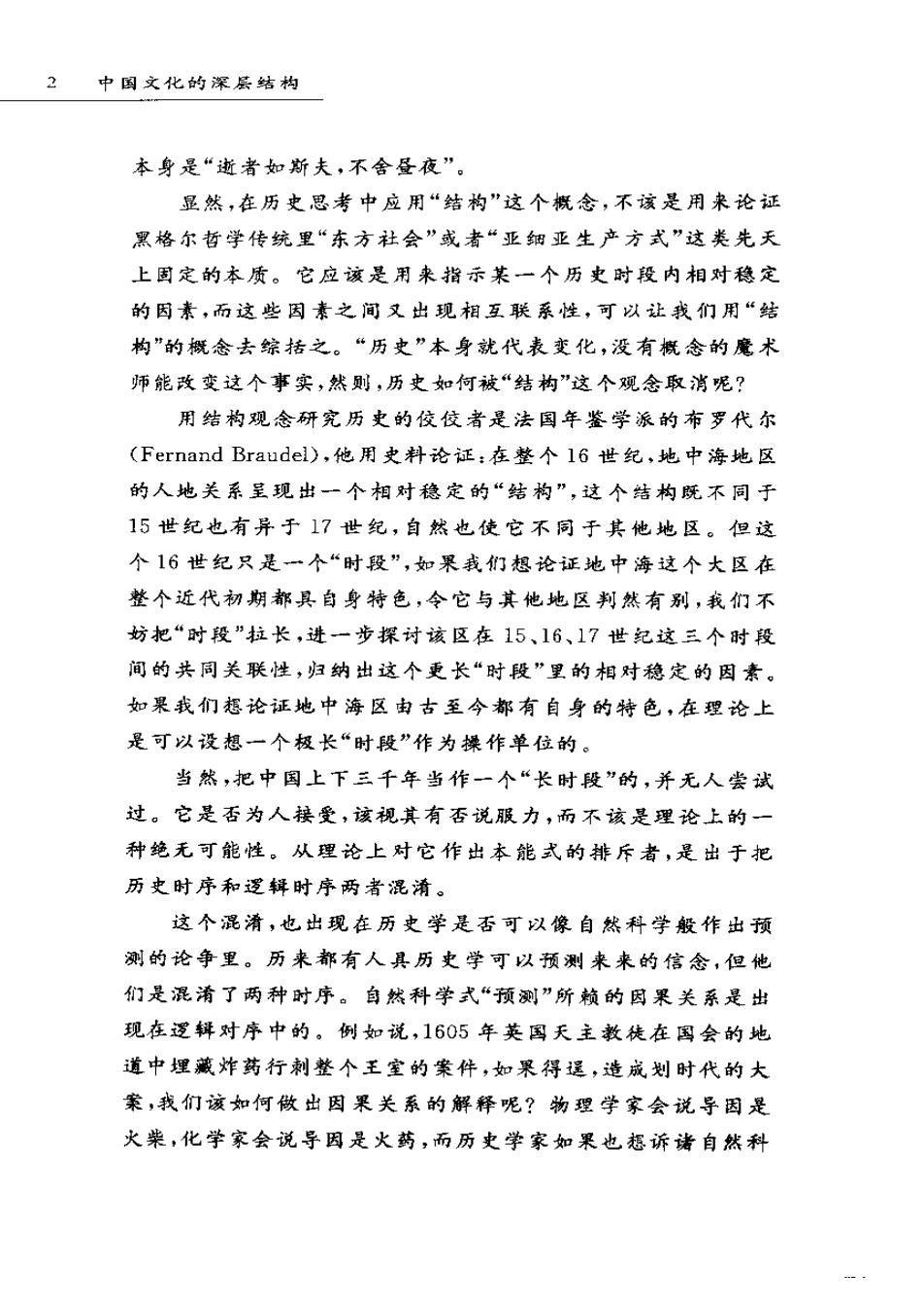
2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本身是“逝者如斯夫,不含昼夜”。 显然,在历史思考中应用“结构”这个概念,不该是用来论证 黑格尔哲学传统里“东方社会”或者“亚细亚生产方式”这类先天 上固定的本质。它应该是用来指示某一个历史时段内相对稳定 的因素,而这些因素之间又出现相互联系性,可以让我们用“结 构”的概念去综括之。“历吏”本身就代表变化,没有概念的魔术 师能改变这个事实,然则,历史如何被“结构”这个观念取消呢? 用结构观念研究历史的佼佼者是法国年鉴学派的布罗代尔 (Fernand Braudel),他用史料论证:在整个l6世纪,地中海地区 的人地关系呈现出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这个结构既不同于 15世纪也有异于17世纪,自然也使它不同于其他地区。但这 个16世纪只是一个“时段”,如果我们想论证地中海这个大区在 整个近代初期都具自身特色,令它与其他地区判然有别,我们不 妨把“时段”拉长,进一步探讨该区在15、16、17世纪这三个时段 间的共同关联性,归纳出这个更长“时段”里的相对稳定的因素 如果我们想论证地中海区由古至今都有自身的特色,在理论上 是可以设想一个极长“时段”作为操作单位的。 当然,把中国上下三千年当作一个“长时段”的,并无人尝试 过。它是否为人接受,该视其有否说服力,而不孩是理论上的一 种绝无可能性。从理论上对它作出本能式的排斥者,是出于把 历史时序和逻辑时序两者混淆。 这个混清,也出现在历史学是否可以像自然科学般作出预 测的论争里。历来都有人具历史学可以预测来来的信念,但他 们是混淆了两种时序。自然科学式“预测”所赖的因果关系是出 现在逻辑对序中的。例如说,1605年英国天主教徒在国会的地 道中埋藏炸药行刺整个王室的案件,如果得遥,造成划时代的大 案,我们该如何做出因果关系的解释呢?物理学家会说导因是 火柴,化学家会说导因是火药,而历史学家如果也想诉诸自然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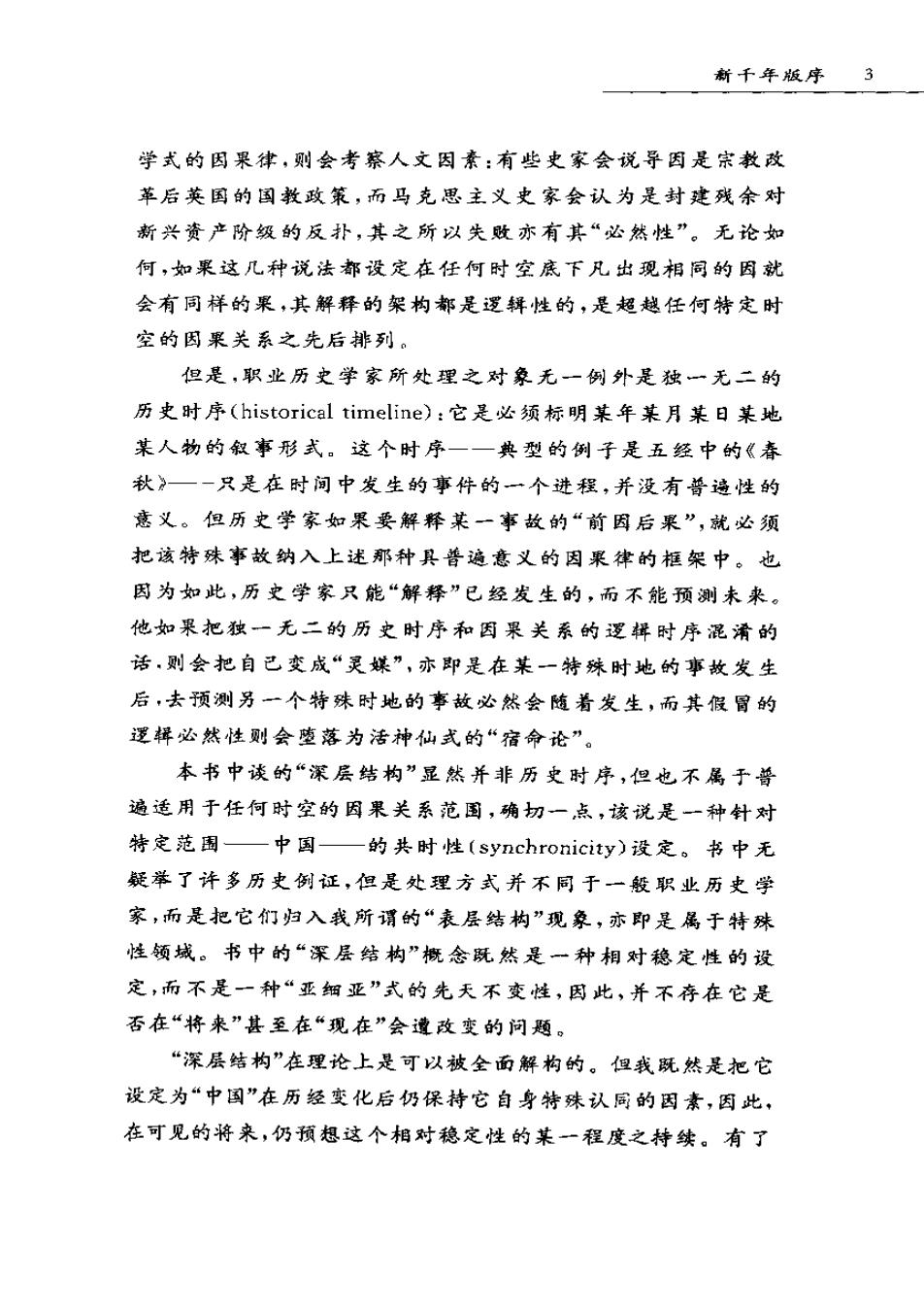
新千年版序 3 学式的因果律,则会考察人文因素:有些史家会说导因是宗教改 革后英国的国教政策,而马克思主义史家会认为是封建残余对 斯兴资产阶级的反扑,其之所以失败亦有其“必然性”。无论如 何,如果这几种说法都设定在任何时空底下凡出现相同的因就 会有同样的果,其解释的架构都是逻辑性的,是超越任何特定时 空的因果关系之先后排列。 但是,职业历史学家所处理之对象无一例外是独一无二的 历史时序(historical timeline):它是必须标明某年某月某日某地 某人物的叙事形式。这个时序一一典型的例子是五经中的《春 秋 一一只是在时间中发生的事件的一个进程,并没有普遍性的 意义。但历史学家如果要解释某一事故的“前因后果”,就必须 把该新殊事故纳入上述那种具普遍意义的因果律的框架中。也 因为如此,历史学家只能“解释”已经发生的,而不能预测未来。 他如果把独一无二的历史时序和因果关系的逻辑时序混淆的 话,则会把自己变成“灵蝶”,亦即是在某一特殊时地的事故发生 后,去预测另一个特殊时地的事故必然会随着发生,而其假冒的 逻样必然性则会堕落为活神仙式的“宿命论”。 本书中谈的“深层结构”显然并非历史时序,但也不属于普 遍适用于任何时空的因果关系范国,确切一,点,该说是一种针对 特定范围一中国—的共时性(synchronicity).设定。书中无 疑举了许多历史例证,但是处理方式并不同于一般职业历吏学 家,而是把它们归入我所谓的“表层结构”现象,亦即是属于特殊 性领域。书中的“深层结构”概念既然是一种相对稳定性的设 定,而不是一种“亚细亚”式的先天不变性,因此,并不存在它是 否在“将来”甚至在“现在”会遵改变的问题。 “深层结构”在理论上是可以被全面解构的。但我既然是把它 设定为“中国”在历经变化后仍保持它自身特殊认同的因素,因此, 在可见的将来,仍预想这个相对稳定性的某一程度之持续。有了

4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这个断的体会,才为新千年版写出如下的新结论: 在本书里,中国文化以十分负面的形象出现,那是因为 它被枚置入一个由他人缔造的“现代”世局中,一切条件对 它来说都是不利的,用来衡量它的所有标准也必然是异化 的。但这个“现代化”该不断被重新定义。中国文化的“文 法”规则能否老新的世局里创造出簇新的佳句妙句,我们将 拭目以待 我充分理会到这个结论与本书的蒸调之间会产生极大的不 协调。 这就牵涉到本书是否已失去“时效”的另一种顾虑。既云作 者“重新打开这本书的时候,恍如再次阅读一部陈年的日记,里 面的思想情愫既曾相识又备感陌生”,那么,它的看法是否充满 偶然性,只反映作者某个时期的思想,而如今已事过境迁? 的确,读者会感到本书的行文是炽热的,但不是炽热的爱国 主义,而是对自身文化的一种接近白热化的反感。这种反感是 如此的强烈,以至由它启发的文化批判远远超出一般的国民性 批判。本书的特点·正在于它不是泛泛地罗列几项或十来项国 民的“劣根性”然后提出老生常谈的补救之道,而是近乎千刀万 刚式的切割。这个浓烈的感觉,是只有身处其中而又想全力地 挣脱出来才有的感觉。如今,作者已经居美三十余年,去国已 久,纵使分祈能力远胜于前,但已经没有了当时的心境,因此无 可能再写出二十年前的东西。 在这里,又回到本书是否已失去“时效”的顾虑。要消弭这 重顾虑,作者提出一个不寻常的解答:具有永久性价值的观点, 往往是由独异的角度出发的。这种独异角度不只是白独异的人 提出,而多半由一个人生中出现某些时刻的独异条件所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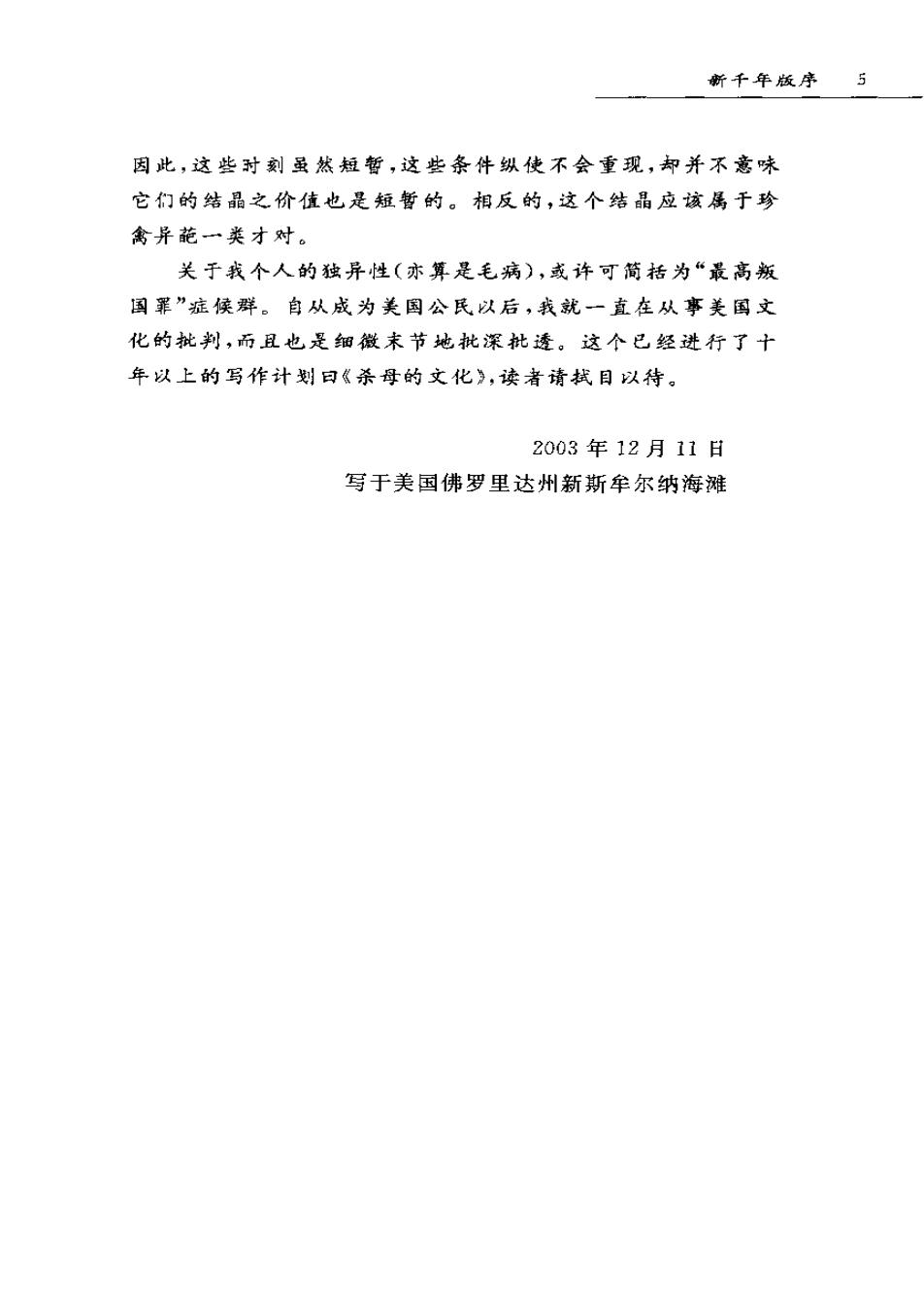
新千年版序5 因此,这些对刻虽然短暂,这些条件纵使不会重现,却并不意味 它们的结晶之价值也是短暂的。相反的,这个结晶应该属于珍 禽异葩一类才对。 关于我个人的独异性(亦算是毛病),或许可简括为“最高叛 国罪”症候群。自从成为美国公民以后,我就一直在从事美国文 化的批判,而且也是细微末节地批深批透。这个已经进行了十 年以上的写作计划曰《杀母的文化》,读者请拭目以待。 2003年12月11日 写于美国佛罗里达州新斯牟尔纳海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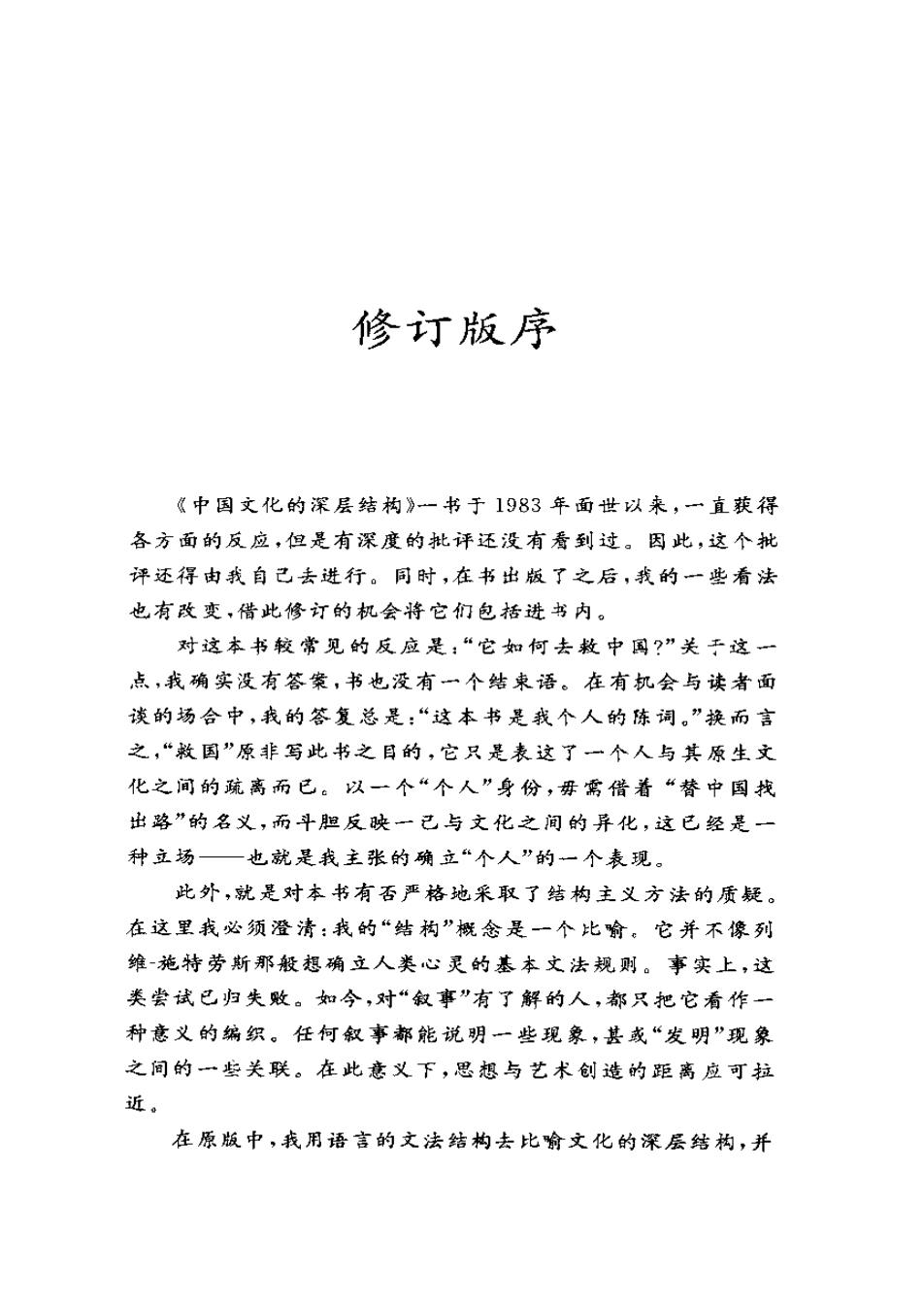
修订版序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于1983年面世以来,一直获得 各方面的反应,但是有深度的批评还没有看到过。因此,这个批 评还得由我自己去进行。同时,在书出版了之后,我的一些看法 也有改变,借此修订的机会将它们包括进书内。 对这本书较常见的反应是:“它如何去救中国?”关于这 点,我确实没有答案,书也没有一个结束语。在有机会与读者面 谈的场合中,我的答复总是:“这本书是我个人的陈词。”换而言 之,“救国”原非写此书之目的,它只是表这了一个人与其原生文 化之间的疏离而已。以一个“个人”身份,毋常借着“替中国找 出路”的名义,而斗胆反映一己与文化之间的异化,这已经是 种立场一也就是我主张的确立“个人”的一个表现。 此外,就是对本书有否严格地采取了结构主义方法的质疑。 在这里我必须澄清:我的“结构”概念是一个比喻。它并不像列 维施特劳斯那般想确立人类心灵的基本文法规则。事实上,这 类尝试已归失败。如今,对“叙事”有了解的人,都只把它看作 种意义的编织。任何叙事都能说明一些现象,甚或“发明”现象 之间的一参关联。在此意义下,思想与艺术创造的距离应可拉 近。 在原版中,我用语言的文法结构去比喻文化的深层结构,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