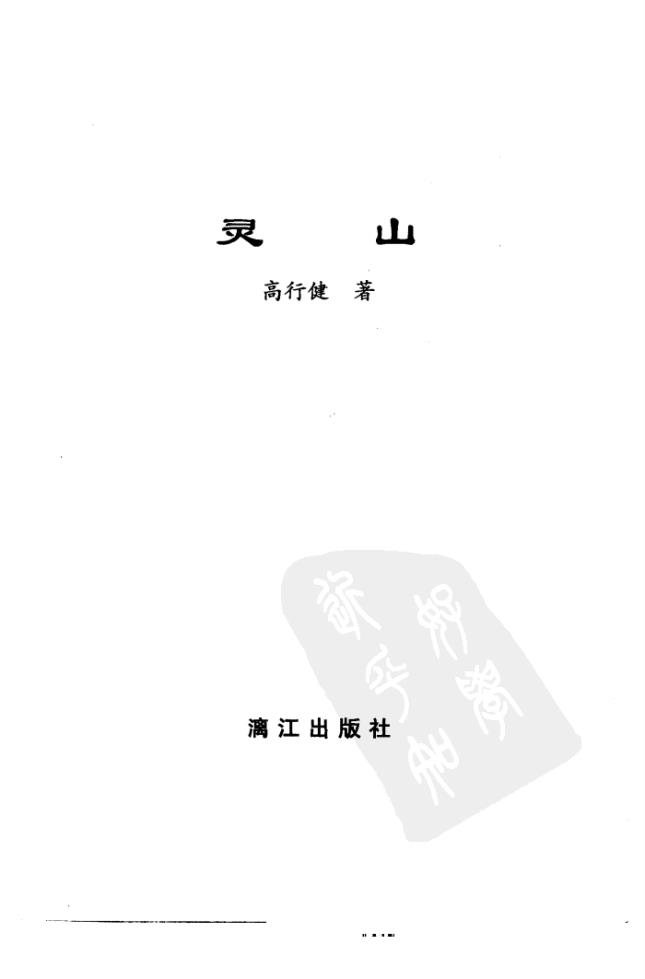
灵 山 高行健著 漓江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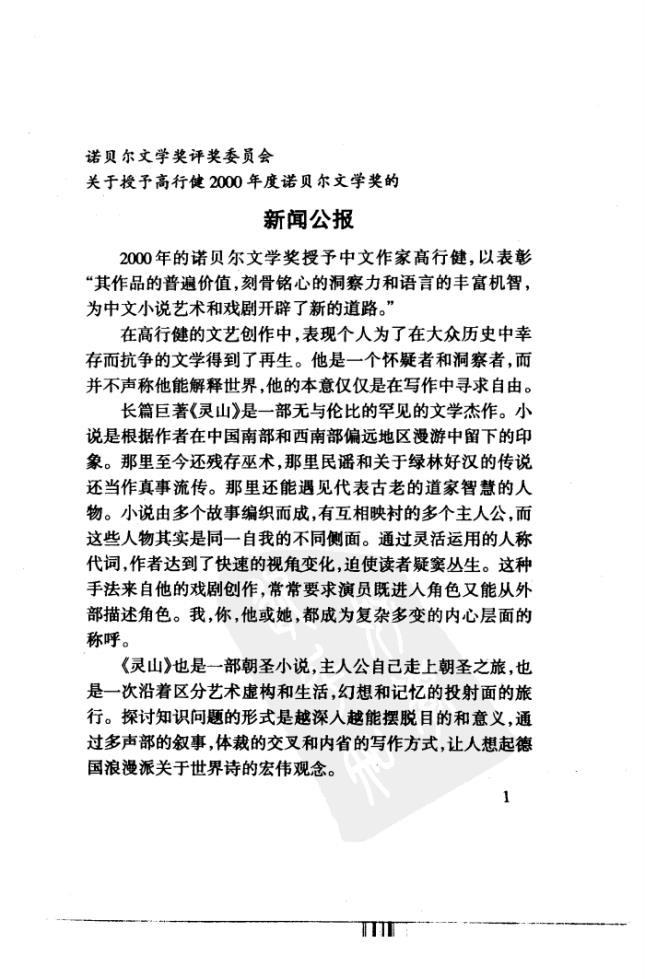
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 关于授予高行健200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 新闻公报 200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文作家高行健,以表彰 “其作品的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 为中文小说艺术和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 在高行健的文艺创作中,表现个人为了在大众历史中幸 存而抗争的文学得到了再生。他是一个怀疑者和洞察者,而 并不声称他能解释世界,他的本意仅仅是在写作中寻求自由。 长篇巨著《灵山》是一部无与伦比的罕见的文学杰作。小 说是根据作者在中国南部和西南部偏远地区漫游中留下的印 象。那里至今还残存巫术,那里民谣和关于绿林好汉的传说 还当作真事流传。那里还能遇见代表古老的道家智慧的人 物。小说由多个故事编织而成,有互相映衬的多个主人公,而 这些人物其实是同一自我的不同侧面。通过灵活运用的人称 代词,作者达到了快速的视角变化,迫使读者疑窦丛生。这种 手法来自他的戏剧创作,常常要求演员既进人角色又能从外 部描述角色。我,你,他或她,都成为复杂多变的内心层面的 称呼。 《灵山》也是一部朝圣小说,主人公自己走上朝圣之旅,也 是一次沿着区分艺术虚构和生活,幻想和记忆的投射面的旅 行。探讨知识问题的形式是越深入越能摆脱目的和意义,通 过多声部的叙事,体裁的交叉和内省的写作方式,让人想起德 国浪漫派关于世界诗的宏伟观念。 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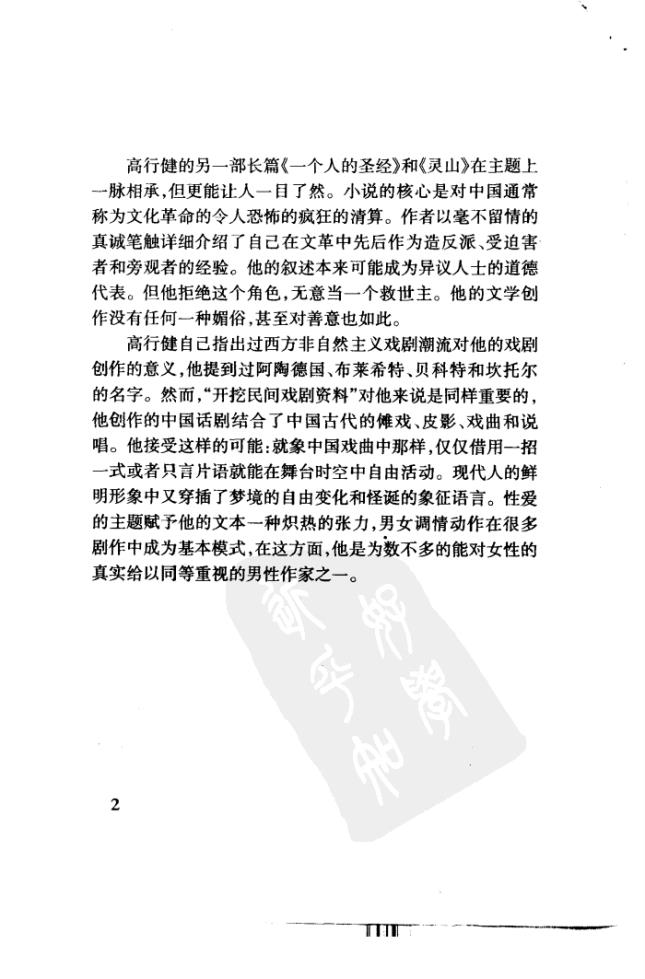
高行健的另一部长篇《一个人的圣经》和《灵山》在主题上 一脉相承,但更能让人一目了然。小说的核心是对中国通常 称为文化革命的令人恐怖的疯狂的清算。作者以毫不留情的 真诚笔触详细介绍了自己在文革中先后作为造反派、受迫害 者和旁观者的经验。他的叙述本来可能成为异议人士的道德 代表。但他拒绝这个角色,无意当一个救世主。他的文学创 作没有任何一种媚俗,甚至对善意也如此。 高行健自己指出过西方非自然主义戏剧潮流对他的戏剧 创作的意义,他提到过阿陶德国、布莱希特、贝科特和坎托尔 的名字。然而,“开挖民间戏剧资料”对他来说是同样重要的, 他创作的中国话剧结合了中国古代的雄戏、皮影、戏曲和说 唱。他接受这样的可能:就象中国戏曲中那样,仅仅借用一招 一式或者只言片语就能在舞台时空中自由活动。现代人的鲜 明形象中又穿插了梦境的自由变化和怪诞的象征语言。性爱 的主题赋予他的文本一种炽热的张力,男女调情动作在很多 剧作中成为基本模式,在这方面,他是为数不多的能对女性的 真实给以同等重视的男性作家之一。 出是 红 2 n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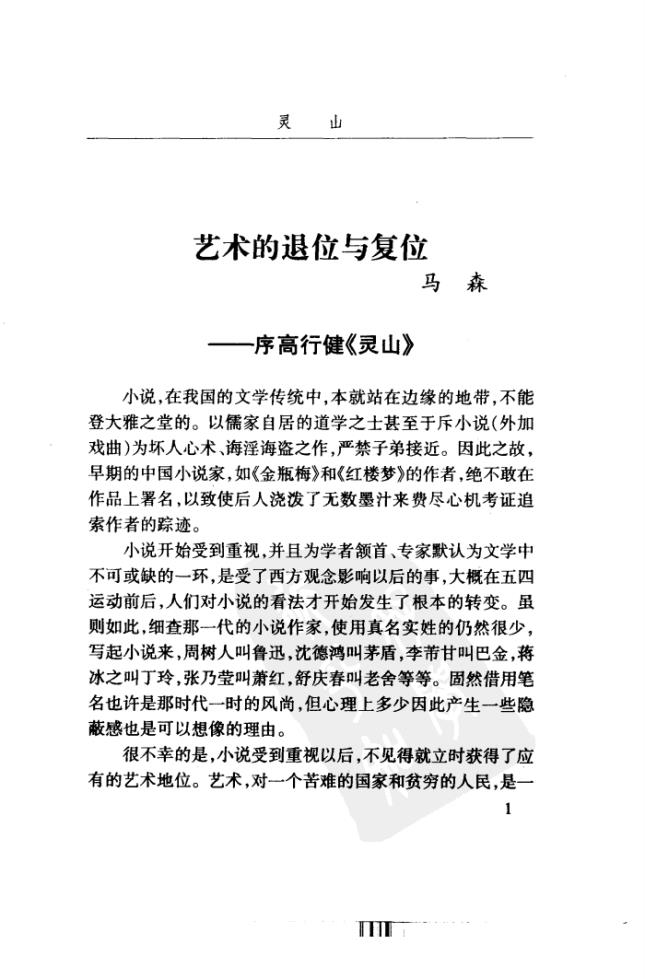
灵 山 艺术的退位与复位 马森 序高行健《灵山》 小说,在我国的文学传统中,本就站在边缘的地带,不能 登大雅之堂的。以儒家自居的道学之士甚至于斥小说(外加 戏曲)为坏人心术、海淫海盗之作,严禁子弟接近。因此之故, 早期的中国小说家,如《金瓶梅》和《红楼梦》的作者,绝不敢在 作品上署名,以致使后人浇泼了无数墨汁来费尽心机考证追 索作者的踪迹。 小说开始受到重视,并且为学者额首、专家默认为文学中 不可或缺的一环,是受了西方观念影响以后的事,大概在五四 运动前后,人们对小说的看法才开始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虽 则如此,细查那一代的小说作家,使用真名实姓的仍然很少, 写起小说来,周树人叫鲁迅,沈德鸿叫茅盾,李芾甘叫巴金,蒋 冰之叫丁玲,张乃莹叫萧红,舒庆春叫老舍等等。固然借用笔 名也许是那时代一时的风尚,但心理上多少因此产生一些隐 蔽感也是可以想像的理由。 很不幸的是,小说受到重视以后,不见得就立时获得了应 有的艺术地位。艺术,对一个苦难的国家和贫穷的人民,是一 1 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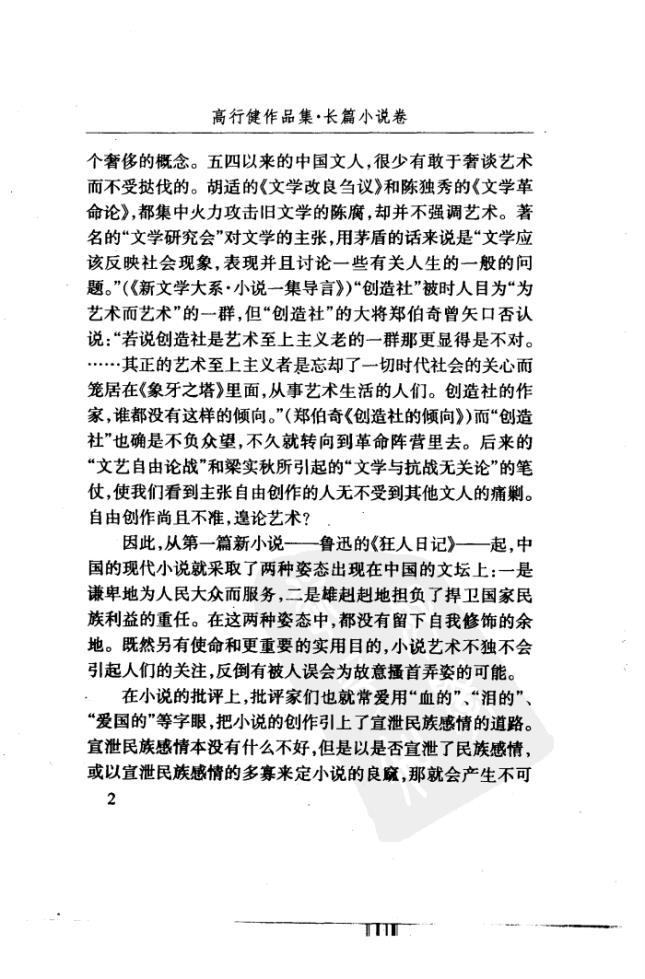
高行健作品集·长篇小说卷 个奢侈的概念。五四以来的中国文人,很少有敢于奢谈艺术 而不受挞伐的。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 命论》,都集中火力攻击旧文学的陈腐,却并不强调艺术。著 名的“文学研究会”对文学的主张,用茅盾的话来说是“文学应 该反映社会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的一般的问 题。”(《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创造社”被时人目为“为 艺术而艺术”的一群,但“创造社”的大将郑伯奇曾矢口否认 说:“若说创造社是艺术至上主义老的一群那更显得是不对。 …其正的艺术至上主义者是忘却了一切时代社会的关心而 笼居在《象牙之塔》里面,从事艺术生活的人们。创造社的作 家,谁都没有这样的倾向。”(郑伯奇《创造社的倾向》)而“创造 社”也确是不负众望,不久就转向到革命阵营里去。后来的 “文艺自由论战”和梁实秋所引起的“文学与抗战无关论”的笔 仗,使我们看到主张自由创作的人无不受到其他文人的痛剿。 自由创作尚且不准,逢论艺术? 因此,从第一篇新小说一鲁迅的《狂人日记》—起,中 国的现代小说就采取了两种姿态出现在中国的文坛上:一是 谦卑地为人民大众而服务,二是雄赳赳地担负了捍卫国家民 族利益的重任。在这两种姿态中,都没有留下自我修饰的余 地。既然另有使命和更重要的实用目的,小说艺术不独不会 引起人们的关注,反倒有被人误会为故意搔首弄姿的可能。 在小说的批评上,批评家们也就常爱用“血的”、“泪的”、 “爱国的”等字眼,把小说的创作引上了宣泄民族感情的道路。 宜泄民族感情本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以是否宜泄了民族感情, 或以宣泄民族感情的多寡来定小说的良魔,那就会产生不可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