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往事並不如煙 章诒和
往事並不如煙 章诒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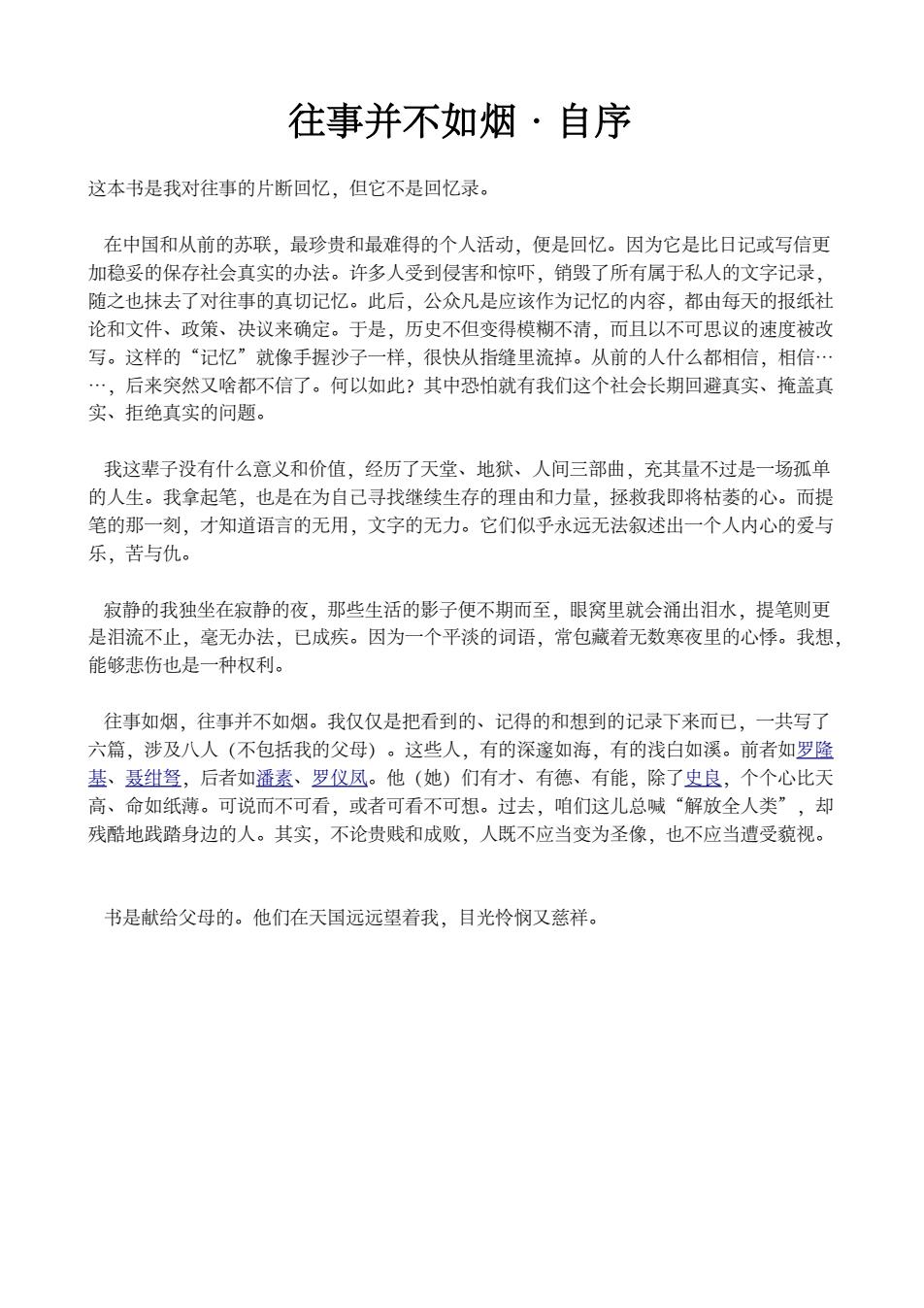
住事并不如烟·自序 这本书是我对往事的片断回忆,但它不是回忆录。 在中国和从前的苏联,最珍贵和最难得的个人活动,便是回忆。因为它是比日记或写信更 加稳妥的保存社会真实的办法。许多人受到侵害和惊吓,销毁了所有属于私人的文字记录, 随之也抹去了对往事的真切记忆。此后,公众凡是应该作为记忆的内容,都由每天的报纸社 论和文件、政策、决议来确定。于是,历史不但变得模糊不清,而且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被改 写。这样的“记忆”就像手握沙子一样,很快从指缝里流掉。从前的人什么都相信,相信… …,后来突然又啥都不信了。何以如此?其中恐怕就有我们这个社会长期回避真实、掩盖真 实、拒绝真实的问题。 我这辈子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经历了天堂、地狱、人间三部曲,充其量不过是一场孤单 的人生。我拿起笔,也是在为自己寻找继续生存的理由和力量,拯救我即将枯萎的心。而提 笔的那一刻,才知道语言的无用,文字的无力。它们似乎永远无法叙述出一个人内心的爱与 乐,苦与仇。 寂静的我独坐在寂静的夜,那些生活的影子便不期而至,眼窝里就会涌出泪水,提笔则更 是泪流不止,毫无办法,已成疾。因为一个平淡的词语,常包藏着无数寒夜里的心悸。我想, 能够悲伤也是一种权利。 往事如烟,往事并不如烟。我仅仅是把看到的、记得的和想到的记录下来而已,一共写了 六篇,涉及八人(不包括我的父母)。这些人,有的深邃如海,有的浅白如溪。前者如罗隆 基、聂绀弩,后者如潘素、罗仪凤。他(她)们有才、有德、有能,除了史良,个个心比天 高、命如纸薄。可说而不可看,或者可看不可想。过去,咱们这儿总喊“解放全人类”,却 残酷地践踏身边的人。其实,不论贵贱和成败,人既不应当变为圣像,也不应当遭受藐视。 书是献给父母的。他们在天国远远望着我,目光怜悯又慈祥
往事并不如烟·自序 这本书是我对往事的片断回忆,但它不是回忆录。 在中国和从前的苏联,最珍贵和最难得的个人活动,便是回忆。因为它是比日记或写信更 加稳妥的保存社会真实的办法。许多人受到侵害和惊吓,销毁了所有属于私人的文字记录, 随之也抹去了对往事的真切记忆。此后,公众凡是应该作为记忆的内容,都由每天的报纸社 论和文件、政策、决议来确定。于是,历史不但变得模糊不清,而且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被改 写。这样的“记忆”就像手握沙子一样,很快从指缝里流掉。从前的人什么都相信,相信… …,后来突然又啥都不信了。何以如此?其中恐怕就有我们这个社会长期回避真实、掩盖真 实、拒绝真实的问题。 我这辈子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经历了天堂、地狱、人间三部曲,充其量不过是一场孤单 的人生。我拿起笔,也是在为自己寻找继续生存的理由和力量,拯救我即将枯萎的心。而提 笔的那一刻,才知道语言的无用,文字的无力。它们似乎永远无法叙述出一个人内心的爱与 乐,苦与仇。 寂静的我独坐在寂静的夜,那些生活的影子便不期而至,眼窝里就会涌出泪水,提笔则更 是泪流不止,毫无办法,已成疾。因为一个平淡的词语,常包藏着无数寒夜里的心悸。我想, 能够悲伤也是一种权利。 往事如烟,往事并不如烟。我仅仅是把看到的、记得的和想到的记录下来而已,一共写了 六篇,涉及八人(不包括我的父母)。这些人,有的深邃如海,有的浅白如溪。前者如罗隆 基、聂绀弩,后者如潘素、罗仪凤。他(她)们有才、有德、有能,除了史良,个个心比天 高、命如纸薄。可说而不可看,或者可看不可想。过去,咱们这儿总喊“解放全人类”,却 残酷地践踏身边的人。其实,不论贵贱和成败,人既不应当变为圣像,也不应当遭受藐视。 书是献给父母的。他们在天国远远望着我,目光怜悯又慈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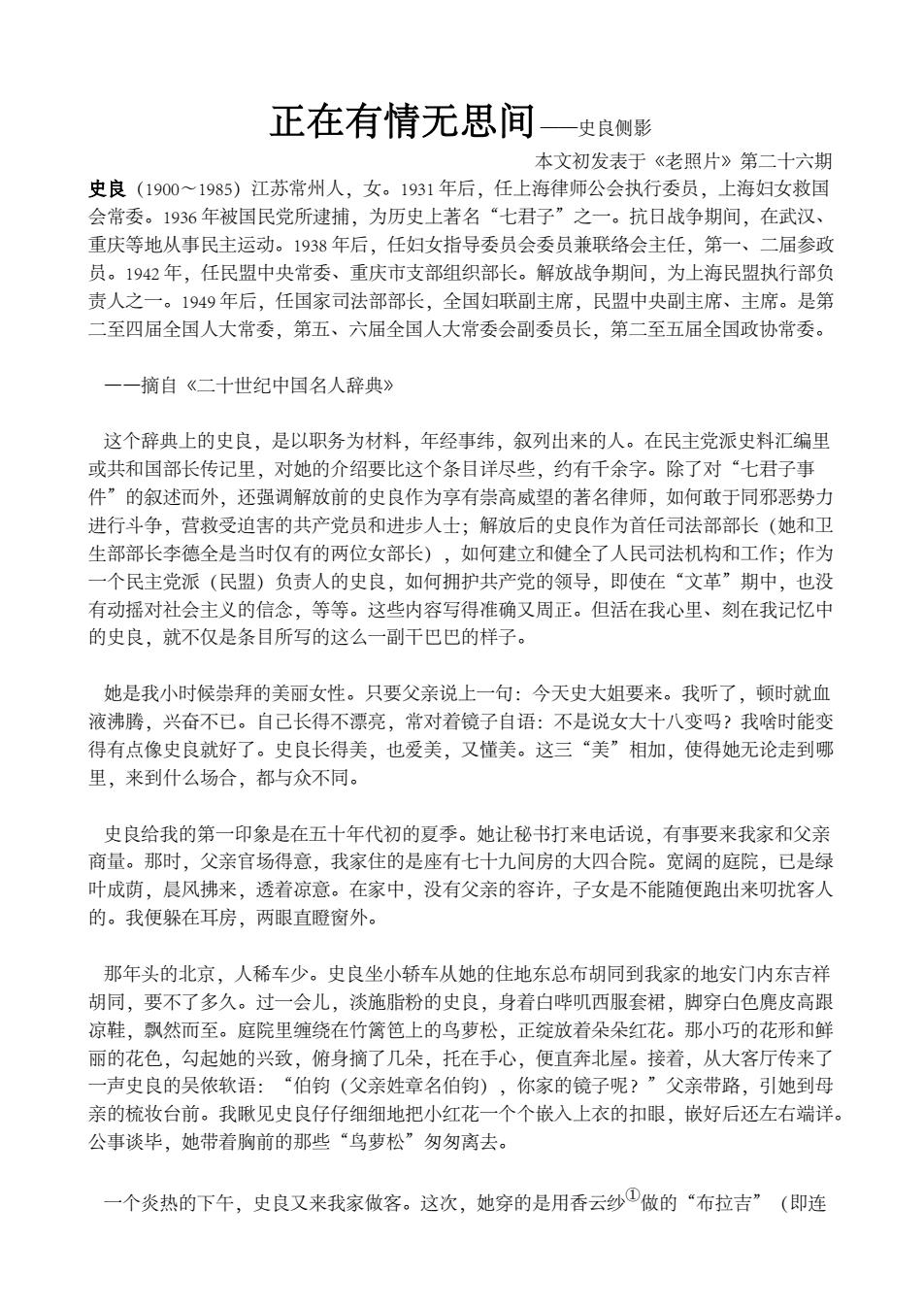
正在有情无思间 —史良侧影 本文初发表于《老照片》第二十六期 史良(1900~1985)江苏常州人,女。1931年后,任上海律师公会执行委员,上海妇女救国 会常委。1936年被国民党所逮捕,为历史上著名“七君子”之一。抗日战争期间,在武汉、 重庆等地从事民主运动。1938年后,任妇女指导委员会委员兼联络会主任,第一、二届参政 员。1942年,任民盟中央常委、重庆市支部组织部长。解放战争期间,为上海民盟执行部负 责人之一。1949年后,任国家司法部部长,全国妇联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主席。是第 二至四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至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一一摘自《二十世纪中国名人辞典》 这个辞典上的史良,是以职务为材料,年经事纬,叙列出来的人。在民主党派史料汇编里 或共和国部长传记里,对她的介绍要比这个条目详尽些,约有千余字。除了对“七君子事 件”的叙述而外,还强调解放前的史良作为享有崇高威望的著名律师,如何敢于同邪恶势力 进行斗争,营救受迫害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解放后的史良作为首任司法部部长(她和卫 生部部长李德全是当时仅有的两位女部长),如何建立和健全了人民司法机构和工作;作为 一个民主党派(民盟)负责人的史良,如何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即使在“文革”期中,也没 有动摇对社会主义的信念,等等。这些内容写得准确又周正。但活在我心里、刻在我记忆中 的史良,就不仅是条目所写的这么一副干巴巴的样子。 她是我小时候崇拜的美丽女性。只要父亲说上一句:今天史大姐要来。我听了,顿时就血 液沸腾,兴奋不已。自己长得不漂亮,常对着镜子自语:不是说女大十八变吗?我啥时能变 得有点像史良就好了。史良长得美,也爱美,又懂美。这三“美”相加,使得她无论走到哪 里,来到什么场合,都与众不同。 史良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在五十年代初的夏季。她让秘书打来电话说,有事要来我家和父亲 商量。那时,父亲官场得意,我家住的是座有七十九间房的大四合院。宽阔的庭院,已是绿 叶成荫,晨风拂来,透着凉意。在家中,没有父亲的容许,子女是不能随便跑出来叨扰客人 的。我便躲在耳房,两眼直瞪窗外。 那年头的北京,人稀车少。史良坐小轿车从她的住地东总布胡同到我家的地安门内东吉祥 胡同,要不了多久。过一会儿,淡施脂粉的史良,身着白哔叽西服套裙,脚穿白色麂皮高跟 凉鞋,飘然而至。庭院里缠绕在竹篱笆上的鸟萝松,正绽放着朵朵红花。那小巧的花形和鲜 丽的花色,勾起她的兴致,俯身摘了几朵,托在手心,便直奔北屋。接着,从大客厅传来了 一声史良的吴侬软语:“伯钧(父亲姓章名伯钧),你家的镜子呢?”父亲带路,引她到母 亲的梳妆台前。我瞅见史良仔仔细细地把小红花一个个嵌入上衣的扣眼,嵌好后还左右端详。 公事谈毕,她带着胸前的那些“鸟萝松”匆匆离去。 一个炎热的下午,史良又来我家做客。这次,她穿的是用香云纱①做的“布拉吉”(即连
正在有情无思间──史良侧影 本文初发表于《老照片》第二十六期 史良(1900~1985)江苏常州人,女。1931 年后,任上海律师公会执行委员,上海妇女救国 会常委。1936 年被国民党所逮捕,为历史上著名“七君子”之一。抗日战争期间,在武汉、 重庆等地从事民主运动。1938 年后,任妇女指导委员会委员兼联络会主任,第一、二届参政 员。1942 年,任民盟中央常委、重庆市支部组织部长。解放战争期间,为上海民盟执行部负 责人之一。1949 年后,任国家司法部部长,全国妇联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主席。是第 二至四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至五届全国政协常委。 ——摘自《二十世纪中国名人辞典》 这个辞典上的史良,是以职务为材料,年经事纬,叙列出来的人。在民主党派史料汇编里 或共和国部长传记里,对她的介绍要比这个条目详尽些,约有千余字。除了对“七君子事 件”的叙述而外,还强调解放前的史良作为享有崇高威望的著名律师,如何敢于同邪恶势力 进行斗争,营救受迫害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解放后的史良作为首任司法部部长(她和卫 生部部长李德全是当时仅有的两位女部长),如何建立和健全了人民司法机构和工作;作为 一个民主党派(民盟)负责人的史良,如何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即使在“文革”期中,也没 有动摇对社会主义的信念,等等。这些内容写得准确又周正。但活在我心里、刻在我记忆中 的史良,就不仅是条目所写的这么一副干巴巴的样子。 她是我小时候崇拜的美丽女性。只要父亲说上一句:今天史大姐要来。我听了,顿时就血 液沸腾,兴奋不已。自己长得不漂亮,常对着镜子自语:不是说女大十八变吗?我啥时能变 得有点像史良就好了。史良长得美,也爱美,又懂美。这三“美”相加,使得她无论走到哪 里,来到什么场合,都与众不同。 史良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在五十年代初的夏季。她让秘书打来电话说,有事要来我家和父亲 商量。那时,父亲官场得意,我家住的是座有七十九间房的大四合院。宽阔的庭院,已是绿 叶成荫,晨风拂来,透着凉意。在家中,没有父亲的容许,子女是不能随便跑出来叨扰客人 的。我便躲在耳房,两眼直瞪窗外。 那年头的北京,人稀车少。史良坐小轿车从她的住地东总布胡同到我家的地安门内东吉祥 胡同,要不了多久。过一会儿,淡施脂粉的史良,身着白哔叽西服套裙,脚穿白色麂皮高跟 凉鞋,飘然而至。庭院里缠绕在竹篱笆上的鸟萝松,正绽放着朵朵红花。那小巧的花形和鲜 丽的花色,勾起她的兴致,俯身摘了几朵,托在手心,便直奔北屋。接着,从大客厅传来了 一声史良的吴侬软语:“伯钧(父亲姓章名伯钧),你家的镜子呢?”父亲带路,引她到母 亲的梳妆台前。我瞅见史良仔仔细细地把小红花一个个嵌入上衣的扣眼,嵌好后还左右端详。 公事谈毕,她带着胸前的那些“鸟萝松”匆匆离去。 一个炎热的下午,史良又来我家做客。这次,她穿的是用香云纱①做的“布拉吉”(即连

衣裙)。她走后,母亲把史良的这身衣服夸赞得不得了,对我说:“自从新中国的电影、话 剧,把香云纱的裤褂作为国民党特务的专业服以后,人们拿这世界上最凉快的衣料简直就没 有办法了。你爸爸从香港带回的几件香云纱成衣,也只好在家休息的时候换上,成了业余装。 看看人家史大姐(这一直是母亲对她的叫法),居然能做成“布拉吉”穿到司法部去。”此 后四十余载,我没见过第二个女人像史良这样地穿着。 直到九十年代末,北京的时髦女性在“怀旧风”的席卷之下,拣起了香云纱。我跑遍大型 商厦,终于也找到一件用它做的西式衬衫。面对三百多元的价格,我毫不犹豫地拿下。其实, 这不是在买衬衫,而是为了复制出一种记忆。 一九五六年,母亲与她同去印度访问,史良是中国妇女代表团团长,母亲是代表团的成员。 这些中国妇女界的精英们在参观了医院、学校、幼儿园,瞻仰了泰姬·玛哈尔陵墓,被尼赫 鲁总理接见后,由接待人员将她们带到新德里最繁华的地段去逛街,带到一家最高级的服饰 店去购物。史良在华贵精美的众多印度丝绸中细挑慢拣,抽出一匹薄如蝉翼且用银丝绣满草 叶花纹的白色衣料,欣赏再三。她把末端之一角斜搭在肩上,对着镜子左顾右盼,并招呼母 亲说:“健生(母亲姓李名健生),快来看看,这是多好的衣料哇。”母亲凑过去,看了一 眼,扭身便走。 走出商店,史良气呼呼地问:“那块衣料,你觉得不好看吗?” 母亲说:“你光顾了好看,不想想我们口袋里有几枚铜板。团员每人八十卢比,你是团长, 也才一百八十卢比。买得起吗?” 史良说:“买不起,欣赏一下,也好。” 母亲说:“老板、伙计好几个人围着你转,到头来你老人家只是欣赏一下。这不叫人家看 出咱们的穷相嘛。” 她不作声了。 史良是考究生活的,希望别人也能如此,同她一样。我的这个看法,是由一桩小事引起。 一个寒冷的冬日,民盟中央的几个负责人罗隆基、胡愈之、周新民、萨空了、楚图南、邓初 民、吴晗、闵刚侯、许广平等,在我家开会。但凡家有来客,父亲必给每位沏茶。人多的话, 还叫洪秘书事先在玻璃杯外壁贴上一个用白纸剪成的圆形小标签,那上面有用毛笔工整地写 着的阿拉伯数字:一,二,三,四,五…客人按先后依次而拿。会开久了,茶喝多了,大 人们陆续如厕。我和姐姐的书房紧挨卫生间,谁去方便我都能瞧见,而且这些先生们进进出 出,看到我都要打个招呼,聊上几句。第一位如厕且多次方便的人,是罗隆基,因为他有糖 尿病。这次的会可能是开得太长了,女士们也开始方便。许广平先来,由于是第一次,不熟 悉我家的卫生间,故让我陪厕。 我告诉她:“您用过的手纸直接丢进马桶,用水冲掉。” 许广平听了,极认真地对我说:“这个做法不好,手纸容易堵塞马桶。要放个纸篓,用过 的手纸就丢进去,每晚再把它倒进垃圾箱。”她又用手指着水箱底下的一角说:“纸篓可以 放在这个地方
衣裙)。她走后,母亲把史良的这身衣服夸赞得不得了,对我说:“自从新中国的电影、话 剧,把香云纱的裤褂作为国民党特务的专业服以后,人们拿这世界上最凉快的衣料简直就没 有办法了。你爸爸从香港带回的几件香云纱成衣,也只好在家休息的时候换上,成了业余装。 看看人家史大姐(这一直是母亲对她的叫法),居然能做成“布拉吉”穿到司法部去。”此 后四十余载,我没见过第二个女人像史良这样地穿着。 直到九十年代末,北京的时髦女性在“怀旧风”的席卷之下,拣起了香云纱。我跑遍大型 商厦,终于也找到一件用它做的西式衬衫。面对三百多元的价格,我毫不犹豫地拿下。其实, 这不是在买衬衫,而是为了复制出一种记忆。 一九五六年,母亲与她同去印度访问,史良是中国妇女代表团团长,母亲是代表团的成员。 这些中国妇女界的精英们在参观了医院、学校、幼儿园,瞻仰了泰姬·玛哈尔陵墓,被尼赫 鲁总理接见后,由接待人员将她们带到新德里最繁华的地段去逛街,带到一家最高级的服饰 店去购物。史良在华贵精美的众多印度丝绸中细挑慢拣,抽出一匹薄如蝉翼且用银丝绣满草 叶花纹的白色衣料,欣赏再三。她把末端之一角斜搭在肩上,对着镜子左顾右盼,并招呼母 亲说:“健生(母亲姓李名健生),快来看看,这是多好的衣料哇。”母亲凑过去,看了一 眼,扭身便走。 走出商店,史良气呼呼地问:“那块衣料,你觉得不好看吗?” 母亲说:“你光顾了好看,不想想我们口袋里有几枚铜板。团员每人八十卢比,你是团长, 也才一百八十卢比。买得起吗?” 史良说:“买不起,欣赏一下,也好。” 母亲说:“老板、伙计好几个人围着你转,到头来你老人家只是欣赏一下。这不叫人家看 出咱们的穷相嘛。” 她不作声了。 史良是考究生活的,希望别人也能如此,同她一样。我的这个看法,是由一桩小事引起。 一个寒冷的冬日,民盟中央的几个负责人罗隆基、胡愈之、周新民、萨空了、楚图南、邓初 民、吴晗、闵刚侯、许广平等,在我家开会。但凡家有来客,父亲必给每位沏茶。人多的话, 还叫洪秘书事先在玻璃杯外壁贴上一个用白纸剪成的圆形小标签,那上面有用毛笔工整地写 着的阿拉伯数字:一,二,三,四,五……客人按先后依次而拿。会开久了,茶喝多了,大 人们陆续如厕。我和姐姐的书房紧挨卫生间,谁去方便我都能瞧见,而且这些先生们进进出 出,看到我都要打个招呼,聊上几句。第一位如厕且多次方便的人,是罗隆基,因为他有糖 尿病。这次的会可能是开得太长了,女士们也开始方便。许广平先来,由于是第一次,不熟 悉我家的卫生间,故让我陪厕。 我告诉她:“您用过的手纸直接丢进马桶,用水冲掉。” 许广平听了,极认真地对我说:“这个做法不好,手纸容易堵塞马桶。要放个纸篓,用过 的手纸就丢进去,每晚再把它倒进垃圾箱。”她又用手指着水箱底下的一角说:“纸篓可以 放在这个地方

史良继之。来了,又走了。她没有对我家的卫生间及其使用发表任何看法。翌日下午,我 正在做功课,突然门铃声大作。洪秘书跑进客厅,对父亲说:“史部长来了,手里还提着两 大包东西。”听罢,父母二人你看我,我看你,显然不解其来由。 史良被请进客厅。她把牛皮纸包的东西往客厅当中的紫檀嵌螺钿大理石台面的圆桌上一放, 笑眯眯道:“我今天不请自到,是特意给你们送洗脸毛巾来的。一包是一打,一打是十二条。 这是两包,共二十四条。我昨天去卫生间,看了你家用的毛巾都该换了。”她转身对母亲说: “健生,一条毛巾顶多只能用两周,不能用到发硬。”母亲的脸顿时红了,父亲也很不好意 思。 我跑到卫生间,生平第一次用“不能发硬”的标准,去审视家族全体成员的洗脸毛巾。天 哪!父亲、母亲、姐姐和我的四条毛巾,活像四条发黄的干鱼挂在那里。尤其是我用的那条, 尾梢已然抽丝并绺儿了。此后,我家的毛巾不再使到变硬发黄,但始终也没能达到史良指示 的标准:一条用两周。那年月提倡的是艰苦朴素、勤俭节约。我问父亲:“史阿姨的生活是 不是过得有点奢侈?” 父亲说:“这不是奢侈,是文明。我在德国留学,住在一个柏林老太婆的家里。她是个犹 太人,生活非常节俭。但她每天给我收拾房间的时候,都要换床单。雪白的床单怎么又要换? 一我问老太太。她讲,除了乞丐和疯子,德国的家庭都如此。” 在民盟中央,一般人都知道史良与父亲的私人关系是相当不错的。一只小罐焖鸡,也让我 看到了这一点。一次,父亲患重感冒,愈后人很虚弱。史良得知后,很快叫人送来一只沉甸 甸的宜兴小罐,母亲揭开盖子,一股鸡汤的浓香直扑鼻底。她还带话给母亲:“不管伯钧生 不生病,他今后吃鸡都要像这样单做。” 父亲用小细瓷勺舀着喝,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说:“史大姐因高血压住进北京医院的时 候,小陆都要送这种小罐鸡汤。” 对父亲吃小罐鸡,我特别眼馋。一日,又见饭桌上摆着那只史良送的宜兴小罐,不禁叹道: “什么时候我能得上感冒,才好呢。” 母亲问:“为什么?” 我说:“那样,我不就也能喝上小罐鸡汤了。” 父亲大笑,并告诉了史良。 史良来我家,每次都是一个人,她的丈夫在哪儿呢?在我对史良产生了近乎崇拜的好感之 后,便对她的一切都有了兴趣和好奇。我问父亲:“史阿姨的丈夫是谁?我怎么从来没见 过?” 父亲说:“她的丈夫叫陆殿东,外交部的一个专员,这个差事是周恩来安排的。他的年龄 比史大姐小,所以大家都叫他小陆。当时在上海,史大姐已经是个名律师的时候,小陆还在 巡捕房当巡捕
史良继之。来了,又走了。她没有对我家的卫生间及其使用发表任何看法。翌日下午,我 正在做功课,突然门铃声大作。洪秘书跑进客厅,对父亲说:“史部长来了,手里还提着两 大包东西。”听罢,父母二人你看我,我看你,显然不解其来由。 史良被请进客厅。她把牛皮纸包的东西往客厅当中的紫檀嵌螺钿大理石台面的圆桌上一放, 笑眯眯道:“我今天不请自到,是特意给你们送洗脸毛巾来的。一包是一打,一打是十二条。 这是两包,共二十四条。我昨天去卫生间,看了你家用的毛巾都该换了。”她转身对母亲说: “健生,一条毛巾顶多只能用两周,不能用到发硬。”母亲的脸顿时红了,父亲也很不好意 思。 我跑到卫生间,生平第一次用“不能发硬”的标准,去审视家族全体成员的洗脸毛巾。天 哪!父亲、母亲、姐姐和我的四条毛巾,活像四条发黄的干鱼挂在那里。尤其是我用的那条, 尾梢已然抽丝并绺儿了。此后,我家的毛巾不再使到变硬发黄,但始终也没能达到史良指示 的标准:一条用两周。那年月提倡的是艰苦朴素、勤俭节约。我问父亲:“史阿姨的生活是 不是过得有点奢侈?” 父亲说:“这不是奢侈,是文明。我在德国留学,住在一个柏林老太婆的家里。她是个犹 太人,生活非常节俭。但她每天给我收拾房间的时候,都要换床单。雪白的床单怎么又要换? ——我问老太太。她讲,除了乞丐和疯子,德国的家庭都如此。” 在民盟中央,一般人都知道史良与父亲的私人关系是相当不错的。一只小罐焖鸡,也让我 看到了这一点。一次,父亲患重感冒,愈后人很虚弱。史良得知后,很快叫人送来一只沉甸 甸的宜兴小罐,母亲揭开盖子,一股鸡汤的浓香直扑鼻底。她还带话给母亲:“不管伯钧生 不生病,他今后吃鸡都要像这样单做。” 父亲用小细瓷勺舀着喝,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说:“史大姐因高血压住进北京医院的时 候,小陆都要送这种小罐鸡汤。” 对父亲吃小罐鸡,我特别眼馋。一日,又见饭桌上摆着那只史良送的宜兴小罐,不禁叹道: “什么时候我能得上感冒,才好呢。” 母亲问:“为什么?” 我说:“那样,我不就也能喝上小罐鸡汤了。” 父亲大笑,并告诉了史良。 史良来我家,每次都是一个人,她的丈夫在哪儿呢?在我对史良产生了近乎崇拜的好感之 后,便对她的一切都有了兴趣和好奇。我问父亲:“史阿姨的丈夫是谁?我怎么从来没见 过?” 父亲说:“她的丈夫叫陆殿东,外交部的一个专员,这个差事是周恩来安排的。他的年龄 比史大姐小,所以大家都叫他小陆。当时在上海,史大姐已经是个名律师的时候,小陆还在 巡捕房当巡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