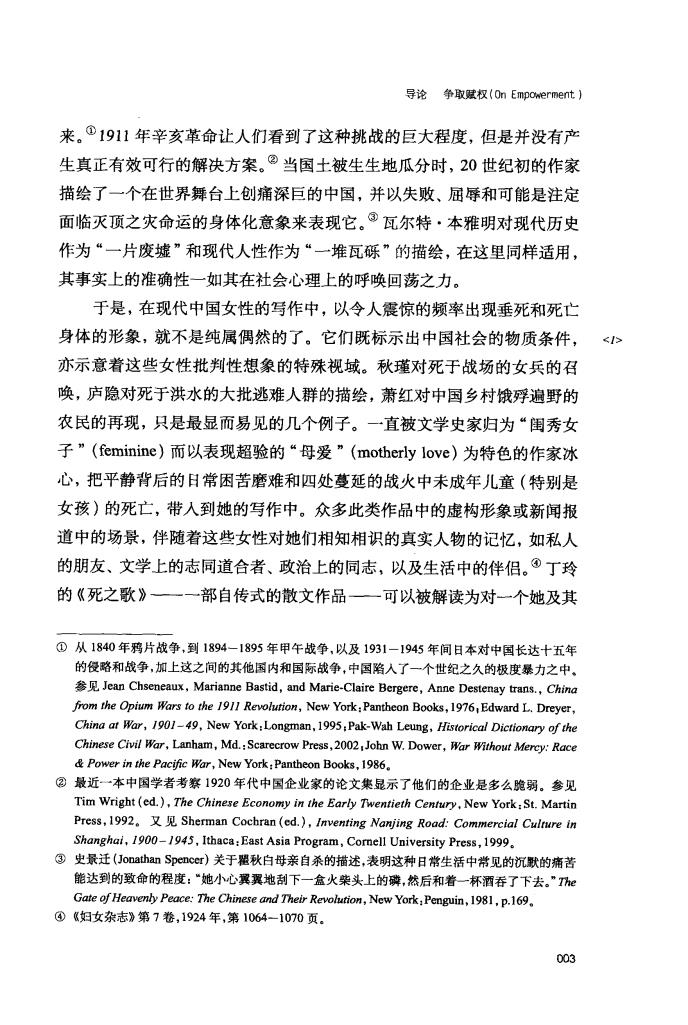
导论争取赋权(0 n Empowerment.) 来。①1911年辛亥革命让人们看到了这种挑战的巨大程度,但是并没有产 生真正有效可行的解决方案。③当国土被生生地瓜分时,20世纪初的作家 描绘了一个在世界舞台上创痛深巨的中国,并以失败、屈辱和可能是注定 面临灭顶之灾命运的身体化意象来表现它。③瓦尔特·本雅明对现代历史 作为“一片废墟”和现代人性作为“一堆瓦砾”的描绘,在这里同样适用, 其事实上的准确性一如其在社会心理上的呼唤回荡之力。 于是,在现代中国女性的写作中,以令人震惊的频率出现垂死和死亡 身体的形象,就不是纯属偶然的了。它们既标示出中国社会的物质条件, <I> 亦示意着这些女性批判性想象的特殊视域。秋瑾对死于战场的女兵的召 唤,庐隐对死于洪水的大批逃难人群的描绘,萧红对中国乡村饿殍遍野的 农民的再现,只是最显而易见的几个例子。一直被文学史家归为“闺秀女 子”(feminine)而以表现超验的“母爱”(motherly love)为特色的作家冰 心,把平静背后的日常困苦磨难和四处蔓延的战火中未成年儿童(特别是 女孩)的死亡,带人到她的写作中。众多此类作品中的虚构形象或新闻报 道中的场景,伴随着这些女性对她们相知相识的真实人物的记忆,如私人 的朋友、文学上的志同道合者、政治上的同志,以及生活中的伴侣。①丁玲 的《死之歌》一一一部自传式的散文作品—一可以被解读为对一个她及其 ①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894-1895年甲午战争,以及1931一1945年间日本对中国长达十五年 的侵略和战争,加上这之间的其他国内和国际战争,中国陷入了一个世纪之久的极度暴力之中, Jean Chseneaux,Marianne Bastid,and Marie-Claire Bergere,Anne Destenay trans.,China from the Opium Wars to the 1911 Revolution,New York:Pantheon Books,1976,Edward L.Dreyer, China at War,1901-49,New York:Longman,1995:Pak-Wah Leung,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Lanham,Md.:Scarecrow Press,2002.John W.Dower,War Without Mercy:Race Power in the Pacific War,New York:Pantheon Books,1986. ②最近一本中国学者考察1920年代中国企业家的论文集显示了他们的企业是多么脆弱。参见 Tim Wright (ed.),The Chinese Economy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St.Martin Press,1992.Sherman Cochran(ed.),Inventing Nanjing Road:Commercial Culture in Shanghai,1900-1945,Ithaca:East Asia Program,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9. ③史景迁(Jonathan Spencer)关于翟秋白母亲自杀的描述,表明这种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沉默的痛苦 能达到的致命的程度:“她小心翼翼地刮下一盒火柴头上的磷,然后和着一杯酒吞了下去。”Te Gate of Heavenby Peace:The Chinese and Their Revolution,New York:Penguin,1981,p.169. ④《妇女杂志》第7卷,1924年,第1064-1070页. 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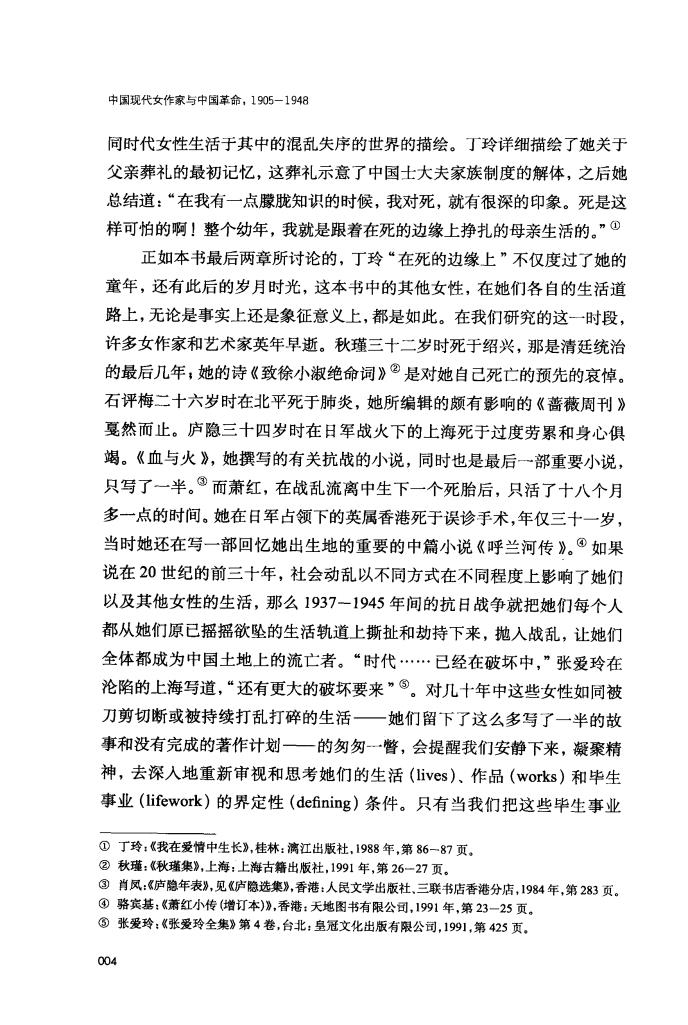
中国现代女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一1948 同时代女性生活于其中的混乱失序的世界的描绘。丁玲详细描绘了她关于 父亲葬礼的最初记忆,这葬礼示意了中国士大夫家族制度的解体,之后她 总结道:“在我有一点朦胧知识的时候,我对死,就有很深的印象。死是这 样可怕的啊!整个幼年,我就是跟着在死的边缘上挣扎的母亲生活的。”@ 正如本书最后两章所讨论的,丁玲“在死的边缘上”不仅度过了她的 童年,还有此后的岁月时光,这本书中的其他女性,在她们各自的生活道 路上,无论是事实上还是象征意义上,都是如此。在我们研究的这一时段, 许多女作家和艺术家英年早逝。秋瑾三十二岁时死于绍兴,那是清廷统治 的最后几年,她的诗《致徐小淑绝命词》②是对她自己死亡的预先的哀悼。 石评梅二十六岁时在北平死于肺炎,她所编辑的颇有影响的《蔷薇周刊》 戛然而止。庐隐三十四岁时在日军战火下的上海死于过度劳累和身心俱 竭。《血与火》,她撰写的有关抗战的小说,同时也是最后一部重要小说, 只写了一半。③而萧红,在战乱流离中生下一个死胎后,只活了十八个月 多一点的时间。她在日军占领下的英属香港死于误诊手术,年仅三十一岁, 当时她还在写一部回忆她出生地的重要的中篇小说《呼兰河传》。①如果 说在20世纪的前三十年,社会动乱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她们 以及其他女性的生活,那么1937一1945年间的抗日战争就把她们每个人 都从她们原已摇摇欲坠的生活轨道上撕扯和劫持下来,抛入战乱,让她们 全体都成为中国土地上的流亡者。“时代…已经在破坏中,”张爱玲在 沦陷的上海写道,“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⑤。对几十年中这些女性如同被 刀剪切断或被持续打乱打碎的生活一她们留下了这么多写了一半的故 事和没有完成的著作计划一的匆匆一瞥,会提醒我们安静下来,凝聚精 神,去深入地重新审视和思考她们的生活(lives)、作品(works)和毕生 事业(lifework)的界定性(defining)条件。只有当我们把这些毕生事业 ①丁玲:《我在爱情中生长》,桂林:漓江出版社,1988年,第86一87页。 ②秋瑾:《秋瑾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6一27页。 ③肖凤:《庐隐年表》,见《庐隐选集》,香港:人民文学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年,第283页。 ④骆宾基:《萧红小传(增订本)》,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1年,第23一25页。 ⑤张爱玲:《张爱玲全集》第4卷,台北: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第425页, 0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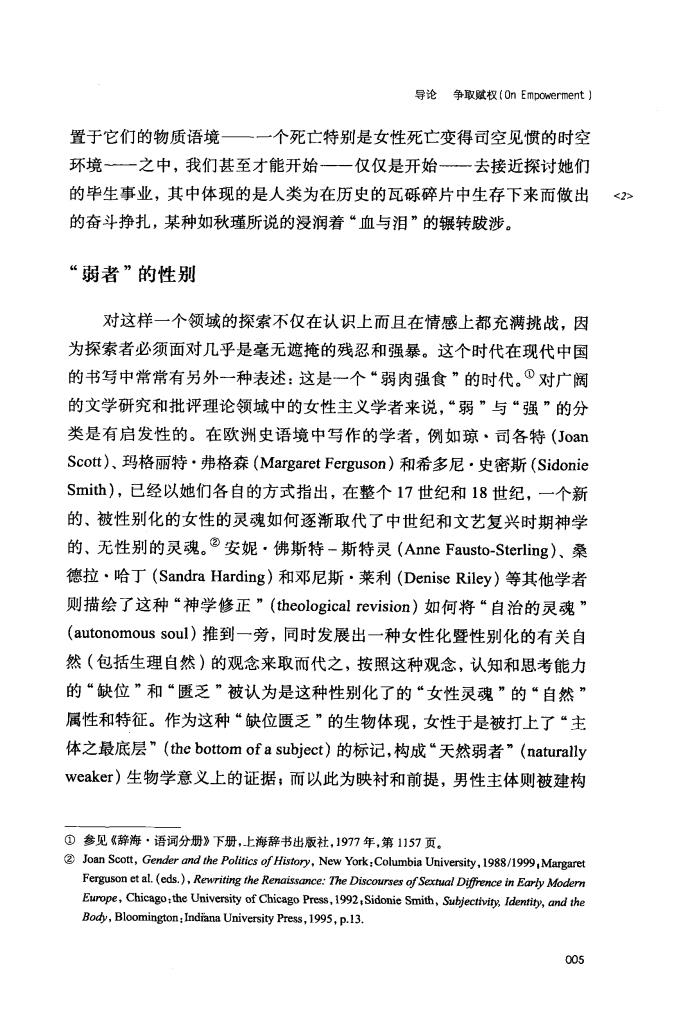
导论争取赋权(On Empowerment】 置于它们的物质语境 一一个死亡特别是女性死亡变得司空见惯的时空 环境一之中,我们甚至才能开始—仅仅是开始一去接近探讨她们 的毕生事业,其中体现的是人类为在历史的瓦砾碎片中生存下来而做出 <2 的奋斗挣扎,某种如秋瑾所说的浸润着“血与泪”的辗转跋涉。 “弱者”的性别 对这样一个领域的探索不仅在认识上而且在情感上都充满挑战,因 为探索者必须面对几乎是毫无遮掩的残忍和强暴。这个时代在现代中国 的书写中常常有另外一种表述: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①对广阔 的文学研究和批评理论领域中的女性主义学者来说,“弱”与“强”的分 类是有启发性的。在欧洲史语境中写作的学者,例如琼·司各特(Joan Scott)、玛格丽特·弗格森(Margaret Ferguson)和希多尼·史密斯(Sidonie Smith),已经以她们各自的方式指出,在整个17世纪和18世纪,一个新 的、被性别化的女性的灵魂如何逐渐取代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神学 的、无性别的灵魂。②安妮·佛斯特-斯特灵(Anne Fausto-Sterling)、桑 德拉·哈丁(Sandra Harding)和邓尼斯·莱利(Denise Riley)等其他学者 则描绘了这种“神学修正”(theological revision)如何将“自治的灵魂” (autonomous soul)推到一旁,同时发展出一种女性化暨性别化的有关自 然(包括生理自然)的观念来取而代之,按照这种观念,认知和思考能力 的“缺位”和“匮乏”被认为是这种性别化了的“女性灵魂”的“自然” 属性和特征。作为这种“缺位匮乏”的生物体现,女性于是被打上了“主 体之最底层”(the bottom of a subject)的标记,构成“天然弱者”(naturally weaker)生物学意义上的证据,而以此为映衬和前提,男性主体则被建构 ①参见《辞海·语词分册》下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77年,第1157页。 2Joan Scott,Gender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1988/1999,Margaret Ferguson et al.(eds.),Rewriting the Renaissance:The Discourses of Sextual Diffrence in Early Modern Europe,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Sidonie Smith,Subjectivity,Identity,and the Body,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5,p.13. 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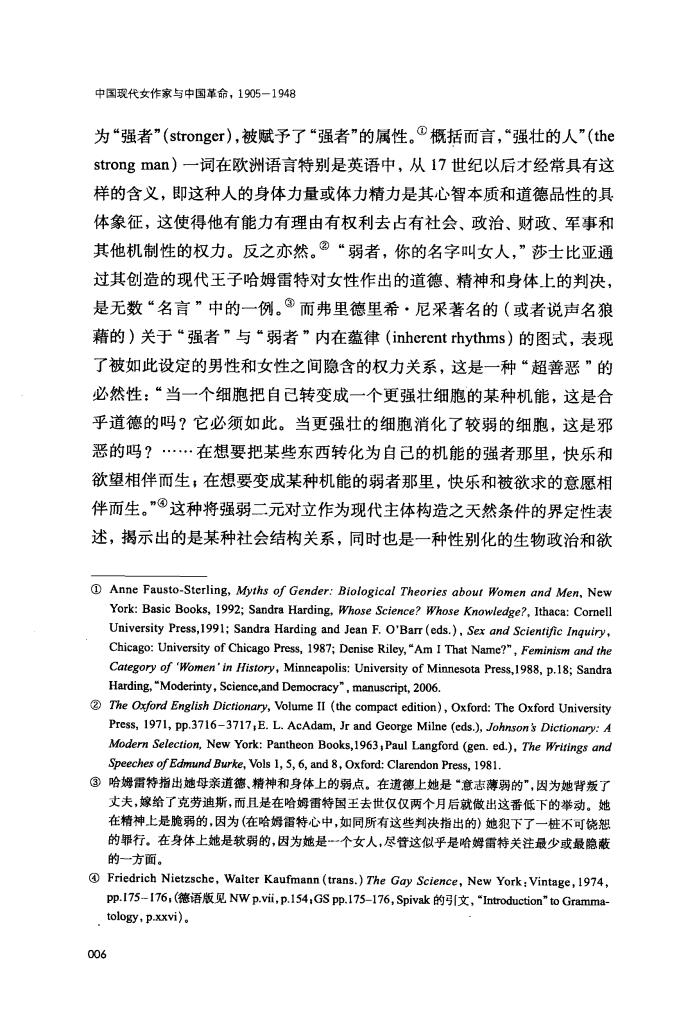
中国现代女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 为“强者”(stronger),被赋予了“强者”的属性。®概括而言,“强壮的人”(the strong man)一词在欧洲语言特别是英语中,从17世纪以后才经常具有这 样的含义,即这种人的身体力量或体力精力是其心智本质和道德品性的具 体象征,这使得他有能力有理由有权利去占有社会、政治、财政、军事和 其他机制性的权力。反之亦然。②“弱者,你的名字叫女人,”莎士比亚通 过其创造的现代王子哈姆雷特对女性作出的道德、精神和身体上的判决, 是无数“名言”中的一例。③而弗里德里希·尼采著名的(或者说声名狼 藉的)关于“强者"与“弱者”内在蕴律(inherent rhythms)的图式,表现 了被如此设定的男性和女性之间隐含的权力关系,这是一种“超善恶”的 必然性:“当一个细胞把自己转变成一个更强壮细胞的某种机能,这是合 乎道德的吗?它必须如此。当更强壮的细胞消化了较弱的细胞,这是邪 恶的吗?…在想要把某些东西转化为自已的机能的强者那里,快乐和 欲望相伴而生,在想要变成某种机能的弱者那里,快乐和被欲求的意愿相 伴而生。”③这种将强弱二元对立作为现代主体构造之天然条件的界定性表 述,揭示出的是某种社会结构关系,同时也是一种性别化的生物政治和欲 Anne Fausto-Sterling,Myths of Gender:Biological Theories about Women and Men.New York:Basic Books,1992;Sandra Harding,Whose Science?Whose Knowledg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1;Sandra Harding and Jean F.O'Barr(eds.),Sex and Scientific Inguiry,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Denise Riley,"Am I That Name?",Feminism and the Category of 'Women'in History,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8,p.18;Sandra Harding,"Moderinty,Science,and Democracy",manuscript,2006. 2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Volume II (the compact edition),Oxford:Th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pp.3716-3717:E.L.AcAdam,Jr and George Milne (eds.),Johnsons Dictionary:A Modern Selection,New York:Pantheon Books,1963,Paul Langford (gen.ed.),The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Edmund Burke,Vols 1,5,6,and 8,Oxford:Clarendon Press,1981. ③哈姆雷特指出她母亲道德、精神和身体上的弱点。在道德上她是“意志薄弱的”,因为她背叛了 丈夫,嫁给了克劳迪斯,而且是在哈姆雷特国王去世仅仅两个月后就做出这番低下的举动。她 在精神上是脆弱的,因为(在哈姆雷特心中,如同所有这些判决指出的)她犯下了一桩不可饶恕 的罪行。在身体上她是软弱的,因为她是一个女人,尽管这似乎是哈姆雷特关注最少或最隐蔽 的一方面。 Friedrich Nietzsche,Walter Kaufmann(trans.)The Gay Science,New York:Vintage,1974, pp.I75-I76,(德语版见NWp.i,p.154,GSpp.175-176,Spivak的引文,“Introduction”to Gramma- tology,p.xxvi)。 0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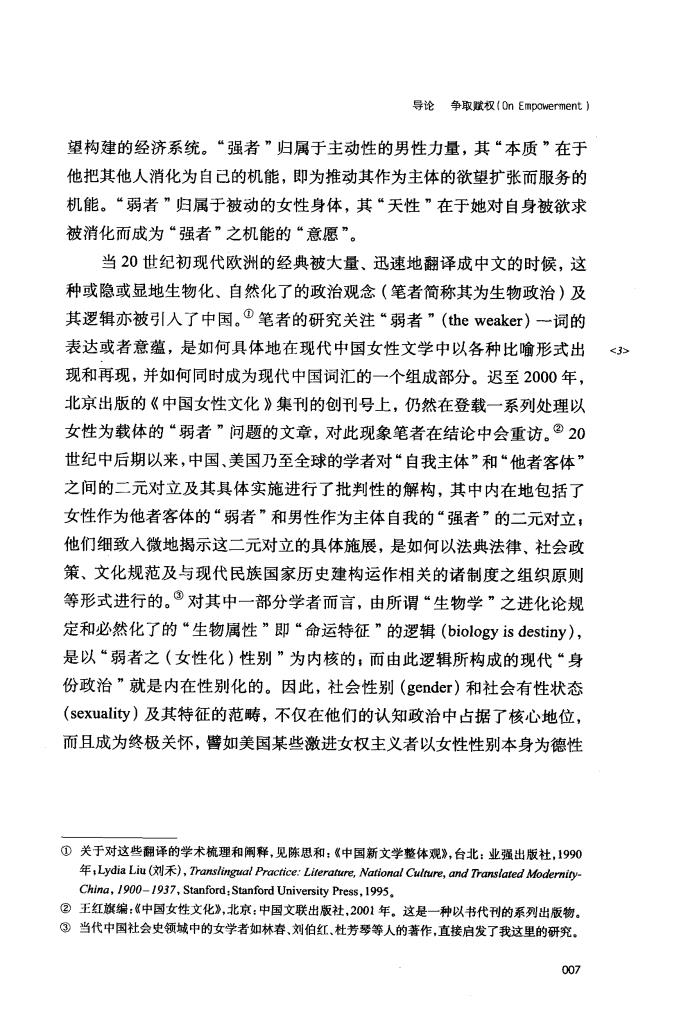
导论争取赋权(0 n Empowerment)】 望构建的经济系统。“强者”归属于主动性的男性力量,其“本质”在于 他把其他人消化为自已的机能,即为推动其作为主体的欲望扩张而服务的 机能。“弱者”归属于被动的女性身体,其“天性”在于她对自身被欲求 被消化而成为“强者”之机能的“意愿”。 当20世纪初现代欧洲的经典被大量、迅速地翻译成中文的时候,这 种或隐或显地生物化、自然化了的政治观念(笔者简称其为生物政治)及 其逻辑亦被引入了中国。@笔者的研究关注“弱者"(the weaker)一词的 表达或者意蕴,是如何具体地在现代中国女性文学中以各种比喻形式出 <33 现和再现,并如何同时成为现代中国词汇的一个组成部分。迟至2000年, 北京出版的《中国女性文化》集刊的创刊号上,仍然在登载一系列处理以 女性为载体的“弱者”问题的文章,对此现象笔者在结论中会重访。②20 世纪中后期以来,中国、美国乃至全球的学者对“自我主体”和“他者客体” 之间的二元对立及其具体实施进行了批判性的解构,其中内在地包括了 女性作为他者客体的“弱者”和男性作为主体自我的“强者”的二元对立, 他们细致入微地揭示这二元对立的具体施展,是如何以法典法律、社会政 策、文化规范及与现代民族国家历史建构运作相关的诸制度之组织原则 等形式进行的。③对其中一部分学者而言,由所谓“生物学”之进化论规 定和必然化了的“生物属性”即“命运特征”的逻辑(biology is destiny), 是以“弱者之(女性化)性别”为内核的,而由此逻辑所构成的现代“身 份政治”就是内在性别化的。因此,社会性别(gender)和社会有性状态 (sexuality)及其特征的范畴,不仅在他们的认知政治中占据了核心地位, 而且成为终极关怀,譬如美国某些激进女权主义者以女性性别本身为德性 ①关于对这些翻译的学术梳理和阐释,见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台北:业强出版社,1990 年,Lydia Liu(刘禾),Translingual Practice:.Literature,National Culture,.and Translated Modernity- China,/900-1937,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②王红旗编:《中国女性文化》,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这是一种以书代刊的系列出版物。 ③当代中国社会史领城中的女学者如林春、刘伯红、杜芳琴等人的著作,直接启发了我这里的研究。 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