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南联大:炮火中成长的“大师之园” 文/新京报记者高明 6月3日,云南师范大学里,学生们在一座座现代化的高楼大厦里进进出出。校园中央, 一间铁皮顶、泥巴墙、木格窗的房子显得格外突兀。 “这是目前仅存的一处西南联大的教室了。”82岁的周锦荪是西南联合大学云南校友会 副会长,精神好的时候,他常来这里走 一击 这间60平 方米的教室 有讲台和椅子, 却没有书桌。“别看教室这么简陋,这可是建筑 设计大师梁思成的杰作。”周锦荪笑笑说,抗战时期,联大经费严重不足,即便是建筑大师也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尽管物质条件异常艰苦,但西南联大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光彩照人的一所大学。 8年时间里,联大培养了2位诺贝尔奖得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和中国工程院院士近 百人,成为真 的 大师之园” 弗吉尼亚大学一位史学教授对西南联大进行了十年的研究后评价:“西南联大是中国历 史上最有意思的一所大学,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保存了最完好的教有形式,培养了最优秀的 人才,最值得人们研究。 师生“长征”组律联合大学 18岁的周锦荪考上西南联大物理系时,当时的校门还简陋得不堪入目 一块油的长 条木板横架在麻条石堆砌的两个石柱上,上写几个大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所学校已 是国内最强、最大的大学。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之后.北平、天津沦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与南开大学的 师生南下长沙,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几个月后战局吃紧,国民政府不得不催促再度 南迁,所有师生分海陆两路进入云南。 此次浩荡的南征是世界教有史上罕见的一次“长征 。这所由 三家本来相互颇有抵触 彼此充满学术竞争的大学组成的高等学府1938年4月2日于昆明迅速建立起来。 昆明多雨。周锦荪回忆,每逢下雨,雨点打在铁皮顶上,丁当作响,教授讲课便要提高 嗓门。一次,经济系教授陈岱孙上课时,因雨声太大,学生根本听不到教师讲课,陈教授无 奈便在黑板上写了“下课赏雨”。此段趣事在联大广为流传,并笑称“正所谓风声、雨声、读 书声,声声入耳” “教室如此,宿舍更不用提了。”周锦荪回忆,宿舍也是土坯墙,但却是茅草顶。每到外 面下大雨,屋内就下小雨,这时候睡在上铺的人只得取脸盆、油布四处接雨。下完雨,宿舍 里就变得泥泞不堪,甚至长起了杂草,学生们的鞋子往往穿一个雨季就烂了。同学们诙诺地 称鞋底磨穿了是“脚踏实地”,鞋尖鞋跟通洞叫做“空前绝后”。 “住得差,吃得也差。”昆明市教有研究所的退休老干部彭国涛是1940年考入西南联大 外文系的学生。他回忆说,联大学生食堂不仅伙食质量极差,而且很长一段时间每天只能吃 两顿饭,上午10点和下午4点各吃一餐。很多学生因无钱购买早点,肚子又饿,甚至没力气 去上头两堂课。彭国涛说,早上一般是稀饭,晚上才能吃到米饭。但因政府供给的是劣质米, 米饭里沙石、老鼠屎、糠屑很多,学生们戏称为“八宝饭”。“尽管当时处在抗战阶段,物价 飞涨,生活非常艰难,但从没有听说学生因为贫穷而辍学。”周锦荪说。 彭国涛回忆, 1941年年底,林语堂到昆明演讲,谈起西南联合大学时,林评价说,“西 南联大物质生活不得了,但精神生活了不得
西南联大:炮火中成长的“大师之园” 文/新京报记者 高明 6 月 3 日,云南师范大学里,学生们在一座座现代化的高楼大厦里进进出出。校园中央, 一间铁皮顶、泥巴墙、木格窗的房子显得格外突兀。 “这是目前仅存的一处西南联大的教室了。”82 岁的周锦荪是西南联合大学云南校友会 副会长,精神好的时候,他常来这里走一走。 这间 60 平方米的教室里有讲台和椅子,却没有书桌。“别看教室这么简陋,这可是建筑 设计大师梁思成的杰作。”周锦荪笑笑说,抗战时期,联大经费严重不足,即便是建筑大师也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尽管物质条件异常艰苦,但西南联大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光彩照人的一所大学。 8 年时间里,联大培养了 2 位诺贝尔奖得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和中国工程院院士近 百人,成为真正的“大师之园”。 弗吉尼亚大学一位史学教授对西南联大进行了十年的研究后评价:“西南联大是中国历 史上最有意思的一所大学,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保存了最完好的教育形式,培养了最优秀的 人才,最值得人们研究。” 师生“长征”组建联合大学 18 岁的周锦荪考上西南联大物理系时,当时的校门还简陋得不堪入目——一块油漆的长 条木板横架在麻条石堆砌的两个石柱上,上写几个大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所学校已 是国内最强、最大的大学。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之后,北平、天津沦陷。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与南开大学的 师生南下长沙,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几个月后战局吃紧,国民政府不得不催促再度 南迁,所有师生分海陆两路进入云南。 此次浩荡的南征是世界教育史上罕见的一次“长征”。这所由三家本来相互颇有抵触、 彼此充满学术竞争的大学组成的高等学府 1938 年 4 月 2 日于昆明迅速建立起来。 昆明多雨。周锦荪回忆,每逢下雨,雨点打在铁皮顶上,丁当作响,教授讲课便要提高 嗓门。一次,经济系教授陈岱孙上课时,因雨声太大,学生根本听不到教师讲课,陈教授无 奈便在黑板上写了“下课赏雨”。此段趣事在联大广为流传,并笑称“正所谓风声、雨声、读 书声,声声入耳”。 “教室如此,宿舍更不用提了。”周锦荪回忆,宿舍也是土坯墙,但却是茅草顶。每到外 面下大雨,屋内就下小雨,这时候睡在上铺的人只得取脸盆、油布四处接雨。下完雨,宿舍 里就变得泥泞不堪,甚至长起了杂草,学生们的鞋子往往穿一个雨季就烂了。同学们诙谐地 称鞋底磨穿了是“脚踏实地”,鞋尖鞋跟通洞叫做“空前绝后”。 “住得差,吃得也差。”昆明市教育研究所的退休老干部彭国涛是 1940 年考入西南联大 外文系的学生。他回忆说,联大学生食堂不仅伙食质量极差,而且很长一段时间每天只能吃 两顿饭,上午 10 点和下午 4 点各吃一餐。很多学生因无钱购买早点,肚子又饿,甚至没力气 去上头两堂课。彭国涛说,早上一般是稀饭,晚上才能吃到米饭。但因政府供给的是劣质米, 米饭里沙石、老鼠屎、糠屑很多,学生们戏称为“八宝饭”。“尽管当时处在抗战阶段,物价 飞涨,生活非常艰难,但从没有听说学生因为贫穷而辍学。”周锦荪说。 彭国涛回忆,1941 年年底,林语堂到昆明演讲,谈起西南联合大学时,林评价说,“西 南联大物质生活不得了,但精神生活了不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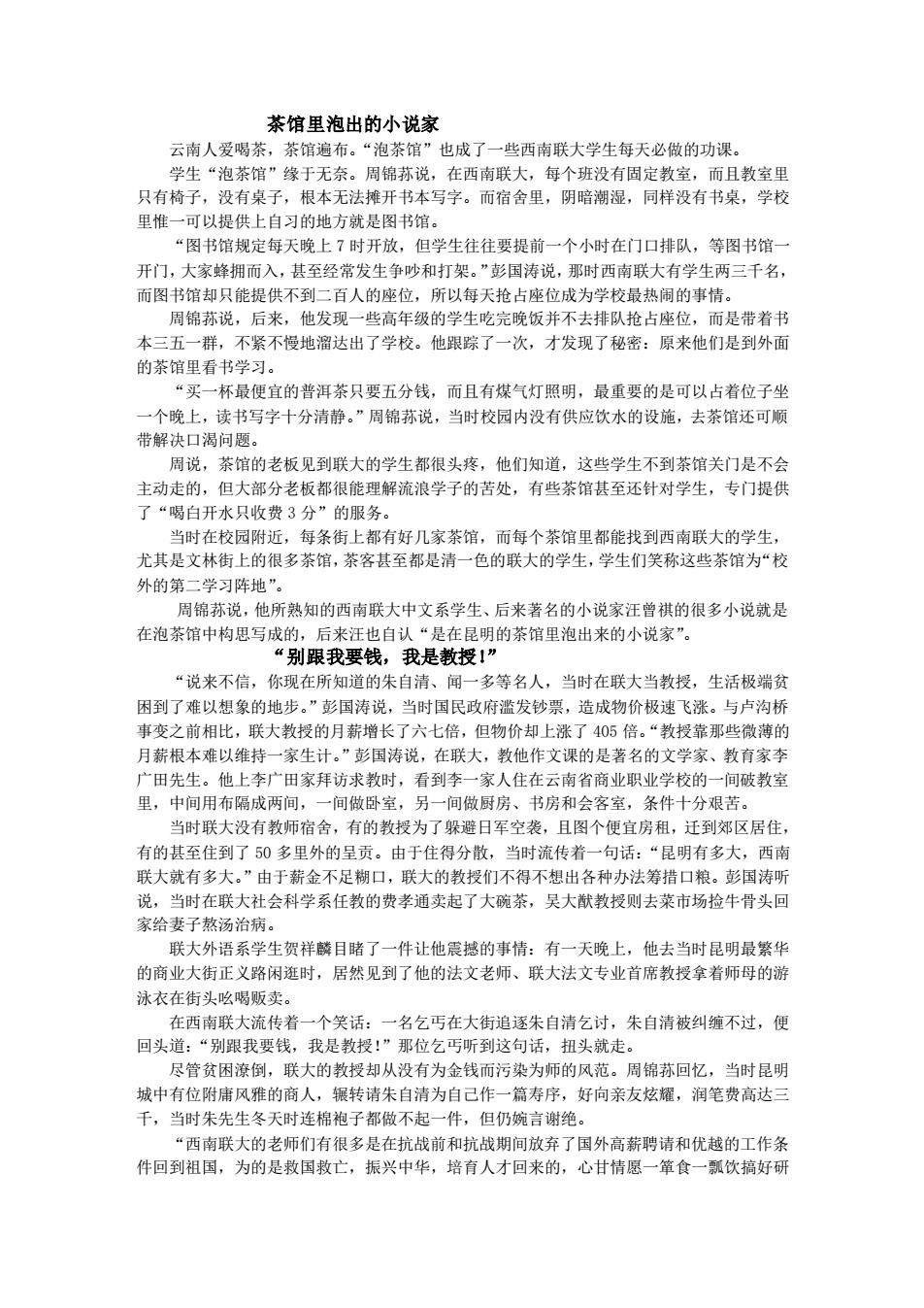
茶馆里泡出的小说家 云南人爱喝茶,茶馆遍布。“泡茶馆”也成了一些西南联大学生每天必做的功课 学生“泡茶馆”缘于无奈。周锦苏说,在西南联大,每个班没有固定教室,而且教室里 只有椅子,没有桌子,根本无法摊开书本写字。而宿舍里,阴暗淘湿,同样没有书桌,学校 里惟一可以提供上自习的地方就是图书馆。 “图书馆规定每天晚上7时开放,但学生往往要提前一个小时在门口排队,等图书馆 开门,大家蜂拥而入,甚至经常发生争吵和打架。”彭国涛说,那时西南联大有学生两三千名, 而图书馆却只能提 不 百人的座位 所以每天抢占座位成为学校最热的事情 周锦荪说,后来,他发现一些高年级的学生吃完晚饭并不去排队抢占座位,而是带若书 本三五一群,不紧不慢地溜达出了学校。他跟踪了一次,才发现了秘密:原来他们是到外面 的茶馆里看书学习。 “买一杯最便官的普洱茶只要五分钱,而日右煤气灯照明,最重要的是可以占若位子坐 个晚上,读书写字十分清静。”周锦荪说,当时校园内没有供应饮水的设施,去茶馆还可顺 带解决口渴问题 周说,茶馆的老板见到联大的学生都很头疼,他们知道,这些学生不到茶馆关门是不会 主动走的,但大部分老板都很能理解流浪学子的苦处,有些茶馆甚至还针对学生,专门提供 了“喝白开水只收费3分”的服务。 当时在校园附近,每条街上都有好几家茶馆,而每个茶馆里都能找到西南联大的学生, 尤其是文林街上的根多茶馆,茶客葚至都是清 色的联大的学生,学生们笑称这些茶馆为“校 外的第二学习阵地”。 周锦荪说,他所熟知的西南联大中文系学生、后来著名的小说家汪曾祺的很多小说就是 在泡茶馆中构思写成的,后来汪也自认“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小说家”。 “别跟我要钱,我是教授1” “说来不信,你现在所知道的朱自清、闻一多等名人,当时在联大当教授,生活极端贫 困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彭国涛说,当时国民政府滥发钞票,造成物价极速飞涨。与卢沟桥 事变之前相比,联大教授的月薪增长了六七倍,但物价却上涨了405倍。“教授靠那些微薄的 月薪根本难以维持一家生计。“彭国涛说,在联大,教他作文课的是著名的文学家、教有家李 广田先生。他上李广田家拜访求教时,看到李一家人住在云南省商业职业学校的一间破教室 里,中间用布隔成两间, 一间做卧室,另一间做厨房、书房和会客室,条件十分艰苦 联大没有教师宿舍,有的教授为了躲避日 空袭,且图个便宜房租,迁到郊区居住 有的甚至住到了50多里外的里贡。由于住得分散,当时流传着一句话:“昆明有多大,西南 联大就有多大。”由于薪金不足糊口,联大的教授们不得不想出各种办法筹措口粮。彭国涛听 说,当时在联大社会科学系任数的费孝通卖起了大碗茶,吴大猷教授则去菜市场拾牛骨头回 家给妻子敖汤治病】 联大外语系学生贺样麟目睹了一件让他震撼的事情:有一天晚上,他去当时昆明最繁华 的商业大街正义路闲逛时,居然见到了他的法文老师、联大法文专业首席教授拿若师母的游 泳衣在街头吆喝贩卖 在西南联大流传若一个笑话:一名乞丐在大街追逐朱自清乞讨,朱自清被纠缠不过,便 回头道:“别跟我要钱,我是教授!”那位乞丐听到这句话,扭头就走。 尽管贫困漆倒,联大的教授却从没有为金钱而污染为师的风范。周锦荪回忆,当时昆明 城中有位附庙风雅的商人,报转请朱自清为自己作一篇寿序,好向亲友炫耀,润笔费高达 千,当时朱先生冬天时连棉袍子都做不起一件,但仍婉言谢绝。 “西南联大的老师们有很多是在抗战前和抗战期间放弃了国外高薪聘请和优越的工作条 件回到祖国,为的是救国救亡,振兴中华,培有人才回来的,心甘情愿一箪食一瓢饮搞好研
茶馆里泡出的小说家 云南人爱喝茶,茶馆遍布。“泡茶馆”也成了一些西南联大学生每天必做的功课。 学生“泡茶馆”缘于无奈。周锦荪说,在西南联大,每个班没有固定教室,而且教室里 只有椅子,没有桌子,根本无法摊开书本写字。而宿舍里,阴暗潮湿,同样没有书桌,学校 里惟一可以提供上自习的地方就是图书馆。 “图书馆规定每天晚上 7 时开放,但学生往往要提前一个小时在门口排队,等图书馆一 开门,大家蜂拥而入,甚至经常发生争吵和打架。”彭国涛说,那时西南联大有学生两三千名, 而图书馆却只能提供不到二百人的座位,所以每天抢占座位成为学校最热闹的事情。 周锦荪说,后来,他发现一些高年级的学生吃完晚饭并不去排队抢占座位,而是带着书 本三五一群,不紧不慢地溜达出了学校。他跟踪了一次,才发现了秘密:原来他们是到外面 的茶馆里看书学习。 “买一杯最便宜的普洱茶只要五分钱,而且有煤气灯照明,最重要的是可以占着位子坐 一个晚上,读书写字十分清静。”周锦荪说,当时校园内没有供应饮水的设施,去茶馆还可顺 带解决口渴问题。 周说,茶馆的老板见到联大的学生都很头疼,他们知道,这些学生不到茶馆关门是不会 主动走的,但大部分老板都很能理解流浪学子的苦处,有些茶馆甚至还针对学生,专门提供 了“喝白开水只收费 3 分”的服务。 当时在校园附近,每条街上都有好几家茶馆,而每个茶馆里都能找到西南联大的学生, 尤其是文林街上的很多茶馆,茶客甚至都是清一色的联大的学生,学生们笑称这些茶馆为“校 外的第二学习阵地”。 周锦荪说,他所熟知的西南联大中文系学生、后来著名的小说家汪曾祺的很多小说就是 在泡茶馆中构思写成的,后来汪也自认“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小说家”。 “别跟我要钱,我是教授!” “说来不信,你现在所知道的朱自清、闻一多等名人,当时在联大当教授,生活极端贫 困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彭国涛说,当时国民政府滥发钞票,造成物价极速飞涨。与卢沟桥 事变之前相比,联大教授的月薪增长了六七倍,但物价却上涨了 405 倍。“教授靠那些微薄的 月薪根本难以维持一家生计。”彭国涛说,在联大,教他作文课的是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李 广田先生。他上李广田家拜访求教时,看到李一家人住在云南省商业职业学校的一间破教室 里,中间用布隔成两间,一间做卧室,另一间做厨房、书房和会客室,条件十分艰苦。 当时联大没有教师宿舍,有的教授为了躲避日军空袭,且图个便宜房租,迁到郊区居住, 有的甚至住到了 50 多里外的呈贡。由于住得分散,当时流传着一句话:“昆明有多大,西南 联大就有多大。”由于薪金不足糊口,联大的教授们不得不想出各种办法筹措口粮。彭国涛听 说,当时在联大社会科学系任教的费孝通卖起了大碗茶,吴大猷教授则去菜市场捡牛骨头回 家给妻子熬汤治病。 联大外语系学生贺祥麟目睹了一件让他震撼的事情:有一天晚上,他去当时昆明最繁华 的商业大街正义路闲逛时,居然见到了他的法文老师、联大法文专业首席教授拿着师母的游 泳衣在街头吆喝贩卖。 在西南联大流传着一个笑话:一名乞丐在大街追逐朱自清乞讨,朱自清被纠缠不过,便 回头道:“别跟我要钱,我是教授!”那位乞丐听到这句话,扭头就走。 尽管贫困潦倒,联大的教授却从没有为金钱而污染为师的风范。周锦荪回忆,当时昆明 城中有位附庸风雅的商人,辗转请朱自清为自己作一篇寿序,好向亲友炫耀,润笔费高达三 千,当时朱先生冬天时连棉袍子都做不起一件,但仍婉言谢绝。 “西南联大的老师们有很多是在抗战前和抗战期间放弃了国外高薪聘请和优越的工作条 件回到祖国,为的是救国救亡,振兴中华,培育人才回来的,心甘情愿一箪食一瓢饮搞好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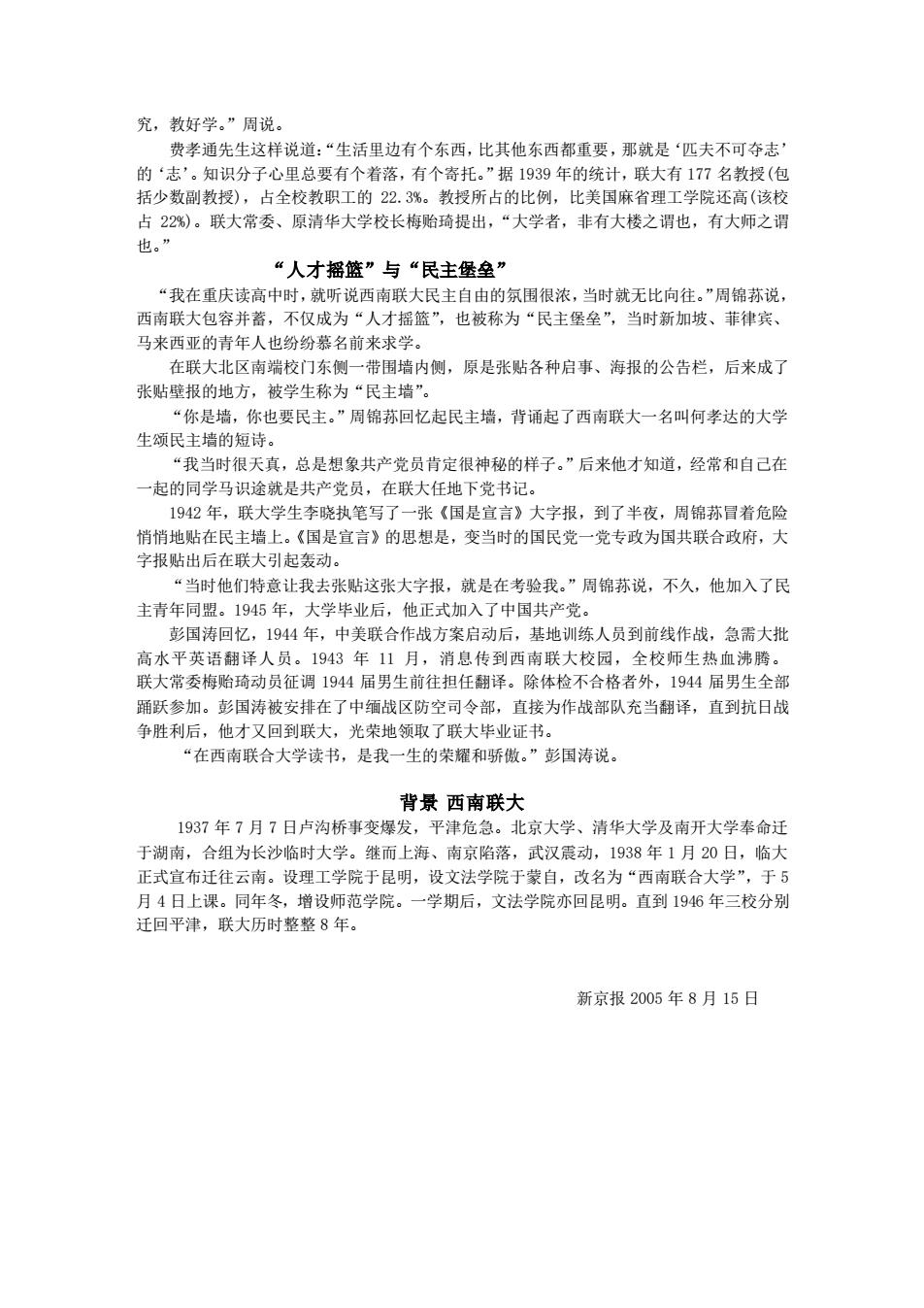
究,教好学。”周说。 费孝通先生这样说道:“生活里边有个东西,比其他东西都重要,那就是‘匹夫不可夺志 的志知识分 子心里总要有个着落,有个寄 ”据1939年的统计,联大有177名教授( 括少数副教授),占全校教职工的22.3%。教授所占的比例,比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还高(该校 占22%)。联大常委、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提出,“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 也。” “人才摇篮”与“民主保垒” “我在重庆读高中 西南联大包容并着 所说西南联大民主自由的氛围很浓,当时就无比向往。周锦荪说 不仅成为“人才摇篮也被称为“民主堡垒”,当时新加坡、菲律宾、 马来西亚的青年人也纷纷慕名前来求学。 在联大北区南端校门东侧一带围墙内侧,原是张贴各种启事、海报的公告栏,后来成了 张贴壁报的地方,被学生称为“民主墙”。 “你是墙,你也要民主。”周锦荪回忆起民主墙,背诵起了西南联大一名叫何孝达的大学 生颂民主培的短诗, “我当时很天真,总是想象共产党员肯定很神秘的样子。”后来他才知道,经常和自己在 “起的同学马识途就是共产党员,在联大任地下党书记。 1942年,联大学生李晓执笔写了一张《国是宜言》大字报,到了半夜,周锦荪冒若危险 悄悄地贴在民主墙上。《国是宣言》的思想是,变当时的国民党一党专政为国共联合政府,大 字报贴出后在联大引起轰动。 当时他们特意让我去张贴这张大字报,就是在考验我。”周锦荪说,不久,他加入了民 主青年同盟。1945年,大学毕业后,他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彭国涛回忆,1944年,中美联合作战方案启动后,基地训练人员到前线作战,急需大批 高水平英语翻译人员。1943年11月,消息传到西南联大校园,全校师生热血沸腾 联大常委梅贻琦动员征调1944届男生前往担任翻译。除体检不合格者外,1944届男生全部 踊跃参加。彭国涛被安排在了中缅战区防空司令部,直接为作战部队充当翻译,直到抗日战 争胜利后,他才又回到联大,光荣地领取了联大毕业证书。 “在西南联合大学读书,是我一生的荣耀和骄傲。”彭国涛说。 背景西南联大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危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及南开大学奉命迁 于湖南,合组为长沙临时大学。继而上海、南京陷落,武汉震动,1938年1月20日,临大 正式宜布迁往云南。设理工学院于昆明,设文法学院于蒙自,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于5 月4日上课。同年冬,增设师范学院。一学期后,文法学院亦回昆明。直到1946年三校分别 迁回平津,联大历时整整8年。 新京报2005年8月15日
究,教好学。”周说。 费孝通先生这样说道:“生活里边有个东西,比其他东西都重要,那就是‘匹夫不可夺志’ 的‘志’。知识分子心里总要有个着落,有个寄托。”据 1939 年的统计,联大有 177 名教授(包 括少数副教授),占全校教职工的 22.3%。教授所占的比例,比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还高(该校 占 22%)。联大常委、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提出,“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 也。” “人才摇篮”与“民主堡垒” “我在重庆读高中时,就听说西南联大民主自由的氛围很浓,当时就无比向往。”周锦荪说, 西南联大包容并蓄,不仅成为“人才摇篮”,也被称为“民主堡垒”,当时新加坡、菲律宾、 马来西亚的青年人也纷纷慕名前来求学。 在联大北区南端校门东侧一带围墙内侧,原是张贴各种启事、海报的公告栏,后来成了 张贴壁报的地方,被学生称为“民主墙”。 “你是墙,你也要民主。”周锦荪回忆起民主墙,背诵起了西南联大一名叫何孝达的大学 生颂民主墙的短诗。 “我当时很天真,总是想象共产党员肯定很神秘的样子。”后来他才知道,经常和自己在 一起的同学马识途就是共产党员,在联大任地下党书记。 1942 年,联大学生李晓执笔写了一张《国是宣言》大字报,到了半夜,周锦荪冒着危险 悄悄地贴在民主墙上。《国是宣言》的思想是,变当时的国民党一党专政为国共联合政府,大 字报贴出后在联大引起轰动。 “当时他们特意让我去张贴这张大字报,就是在考验我。”周锦荪说,不久,他加入了民 主青年同盟。1945 年,大学毕业后,他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彭国涛回忆,1944 年,中美联合作战方案启动后,基地训练人员到前线作战,急需大批 高水平英语翻译人员。1943 年 11 月,消息传到西南联大校园,全校师生热血沸腾。 联大常委梅贻琦动员征调 1944 届男生前往担任翻译。除体检不合格者外,1944 届男生全部 踊跃参加。彭国涛被安排在了中缅战区防空司令部,直接为作战部队充当翻译,直到抗日战 争胜利后,他才又回到联大,光荣地领取了联大毕业证书。 “在西南联合大学读书,是我一生的荣耀和骄傲。”彭国涛说。 背景 西南联大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危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及南开大学奉命迁 于湖南,合组为长沙临时大学。继而上海、南京陷落,武汉震动,1938 年 1 月 20 日,临大 正式宣布迁往云南。设理工学院于昆明,设文法学院于蒙自,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于 5 月 4 日上课。同年冬,增设师范学院。一学期后,文法学院亦回昆明。直到 1946 年三校分别 迁回平津,联大历时整整 8 年。 新京报 2005 年 8 月 15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