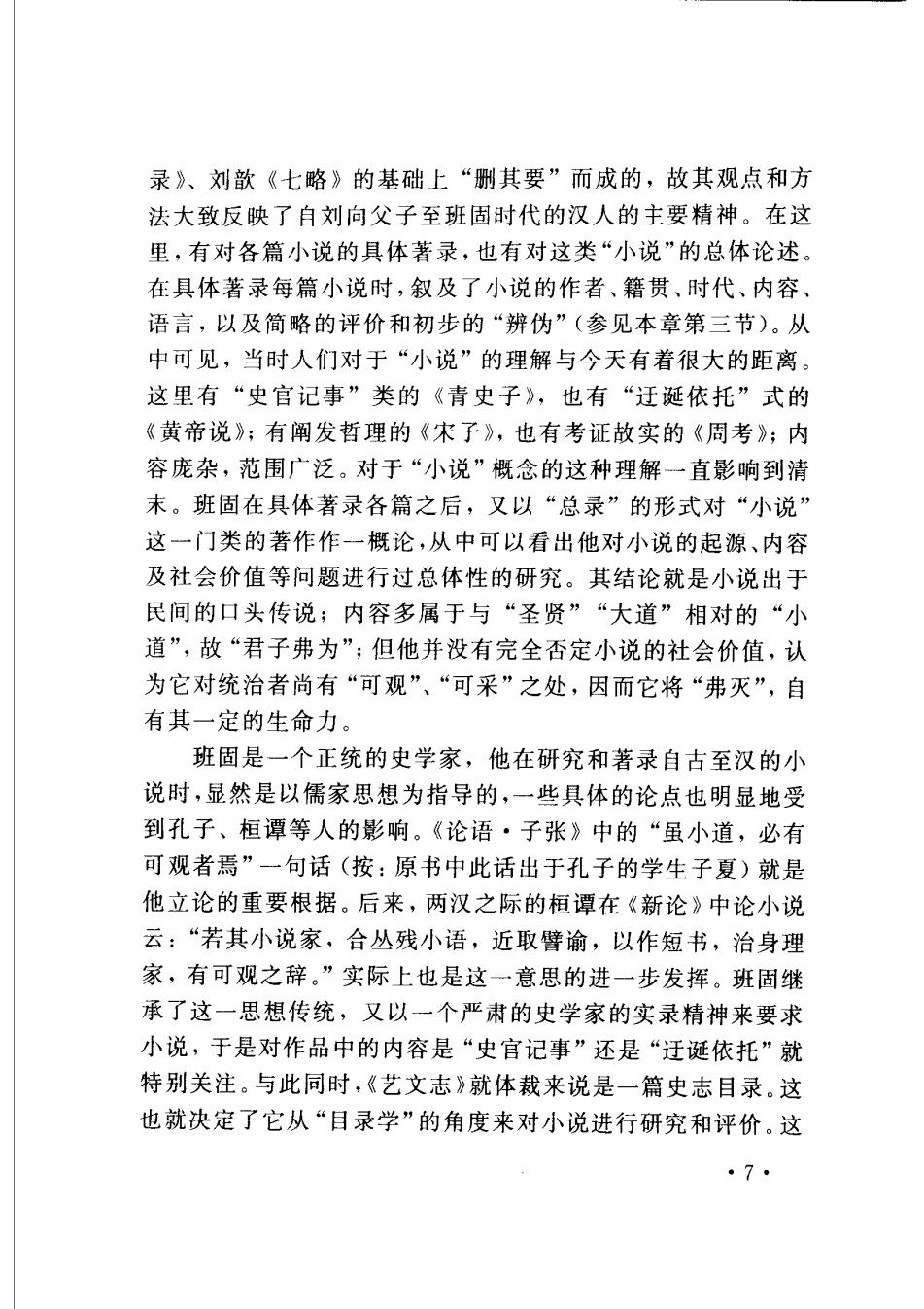
录》、刘歆《七略》的基础上“删其要”而成的,故其观点和方 法大致反映了自刘向父子至班固时代的汉人的主要精神。在这 里,有对各篇小说的具体著录,也有对这类“小说”的总体论述 在具体著录每篇小说时,叙及了小说的作者、籍贯、时代、内容、 语言,以及简略的评价和初步的“辨伪”(参见本章第三节)。从 中可见,当时人们对于“小说”的理解与今天有着很大的距离 这里有“史官记事”类的《青史子》,也有“迂诞依托”式的 《黄帝说》:有阐发哲理的《宋子》,也有考证故实的《周考》;内 容庞杂,范围广泛。对于“小说”概念的这种理解一直影响到清 末。班固在具体著录各篇之后,又以“总录”的形式对“小说” 这一门类的著作作一概论,从中可以看出他对小说的起源、内容 及社会价值等问题进行过总体性的研究。其结论就是小说出于 民间的口头传说;内容多属于与“圣贤”“大道”相对的“小 道”,故“君子弗为”;但他并没有完全否定小说的社会价值,认 为它对统治者尚有“可观”、“可采”之处,因而它将“弗灭”,自 有其一定的生命力。 班固是一个正统的史学家,他在研究和著录自古至汉的小 说时,显然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一些具体的论点也明显地受 到孔子、桓谭等人的影响。《论语·子张》中的“虽小道,必有 可观者焉”一句话(按:原书中此话出于孔子的学生子夏)就是 他立论的重要根据。后来,两汉之际的桓谭在《新论》中论小说 云:“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谕,以作短书,治身理 家,有可观之辞。”实际上也是这一意思的进一步发挥。班固继 承了这一思想传统,又以一个严肃的史学家的实录精神来要求 小说,于是对作品中的内容是“史官记事”还是“迂诞依托”就 特别关注。与此同时,《艺文志》就体裁来说是一篇史志目录。这 也就决定了它从“目录学”的角度来对小说进行研究和评价。这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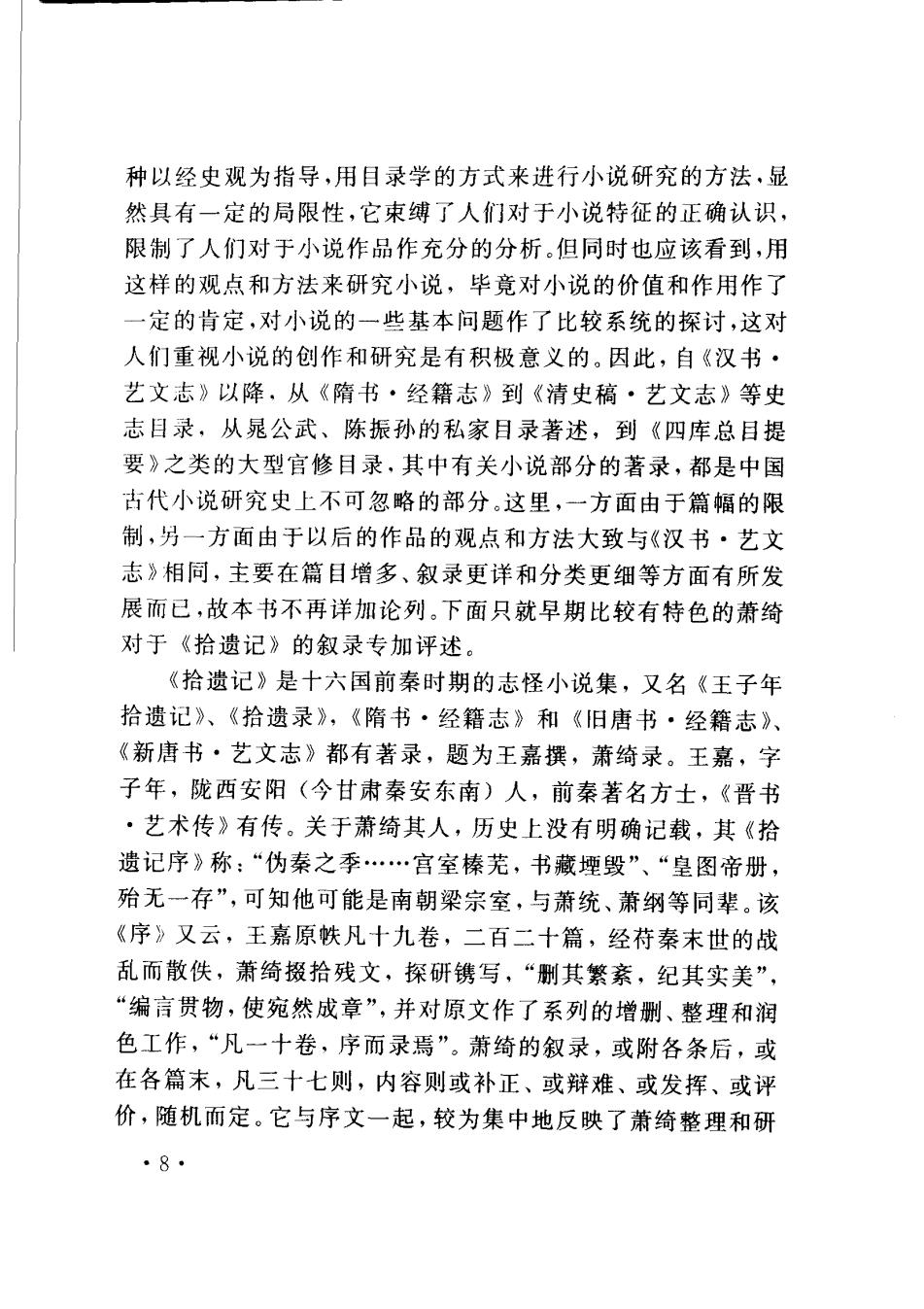
种以经史观为指导,用目录学的方式来进行小说研究的方法,显 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它束缚了人们对于小说特征的正确认识, 限制了人们对于小说作品作充分的分析。但同时也应该看到,用 这样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小说,毕竟对小说的价值和作用作了 一定的肯定,对小说的一些基本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探讨,这对 人们重视小说的创作和研究是有积极意义的。因此,自《汉书· 艺文志》以降,从《隋书·经籍志》到《清史稿·艺文志》等史 志目录,从晁公武、陈振孙的私家目录著述,到《四库总目提 要》之类的大型官修目录,其中有关小说部分的著录,都是中国 古代小说研究史上不可忽略的部分。这里,一方面由于篇幅的限 制,另一方面由于以后的作品的观点和方法大致与《汉书·艺文 志》相同,主要在篇目增多、叙录更详和分类更细等方面有所发 展而已,故本书不再详加论列。下面只就早期比较有特色的萧绮 对于《拾遗记》的叙录专加评述。 《拾遗记》是十六国前秦时期的志怪小说集,又名《王子年 拾遗记》、《拾遗录》,《隋书·经籍志》和《旧唐书·经籍志》、 《新唐书·艺文志》都有著录,题为王嘉撰,萧绮录。王嘉,字 子年,陇西安阳(今甘肃秦安东南)人,前秦著名方士,《晋书 ·艺术传》有传。关于萧绮其人,历史上没有明确记载,其《拾 遗记序》称:“伪秦之季.宫室榛芜,书藏堙毁”、“皇图帝册, 殆无一存”,可知他可能是南朝梁宗室,与萧统、萧纲等同辈。该 《序》又云,王嘉原帙凡十九卷,二百二十篇,经苻秦末世的战 乱而散佚,萧绮掇拾残文,探研镌写,“删其繁紊,纪其实美”, “编言贯物,使宛然成章”,并对原文作了系列的增删、整理和润 色工作,“凡一十卷,序而录焉”。萧绮的叙录,或附各条后,或 在各篇末,凡三十七则,内容则或补正、或辩难、或发挥、或评 价,随机而定。它与序文一起,较为集中地反映了萧绮整理和研 ·8

究小说的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 萧绮《拾遗记序》称:“文起羲炎以来,事迄西晋之末,五 运因循,十有四代”,因为原书多有亡败,所以按年代重新编次。 他认为,王嘉所搜撰的是属于“宪章稽古之文,绮综编杂之部” 的杂史,因而他根据经史的记载来加以对照和评论,指出《拾遗 记》具有“言匪浮诡,事弗定诬,详推往迹,则影彻经史;考验 真怪,则叶附图籍”的特征,提出“纪其实美”、“考验真怪”的 理论原则,要求言必有据,事必可考。在《拾遗记》各篇的录语 中,他力图贯彻《序》中提出的这种主张。例如卷一《春皇庖 牺》、《炎帝神农》所载伏羲和神农时代的神话传说,萧绮“录 曰:“《八索》载其遐轨,《九丘》纪其淳化,备昭籍箓,编列柱 史。考验先经,刊详往诰,事列方典,取征群籍,博采百家,求 详可证。”认为可与前经正诰所载的史实互证,对王嘉的记载予 以肯定。并且认为圣王时代,天下所以清平,灵瑞祯祥百出,是 由于“道真俗朴,理会冥旨,与四时齐其契,精灵协其德”,否 则,“祯祥之异,胡可致哉?”(卷一录语)用儒家观点如此这般 地加以推衍论证,以致清末谭献称道说:“萧绮附录,大义归于 正道,是非不谬圣人者已。”(《复堂日记》卷五)又如卷三《周 穆王》记周穆王乘八骏周游天下的传说,萧绮“录”日:“鳞骝 驶是之俦,亦腾骧以称骏,莫不待盛明而皆出”,以为异骏的出 现是圣明昌盛时代的标志,将幻奇的志怪小说内容勉强附会于 圣明至道的范围。同时,对那些他认为既不可考实,又不合经典 的记载,则表示否定。例如卷八《糜竺》条载糜竺家宝库失火, “火盛之时,见数十青衣童子来扑火,有青气如云,覆于火上,即 灭。童子又云:‘多聚鹳鸟之类,以禳火灾;鹳能聚水于巢上也。’ 家人乃收䴔鹊数千头养于池渠中,以压火。”萧“录”日:“羽毛 之类,非可以御烈火,于义则为乖,于事则违类,先《坟》旧 。9

《典》,说已其(疑原为“甚”字)详焉,”可以看出,史家的实 录精神与儒家的正统观念,对萧绮的批评倾向有着深刻的影响 然而,王嘉是富有文采的方士,《拾遗记》侈谈一些神仙怪 异之事,正如萧绮《序》所云“多涉祯祥之书,博采神仙之事, 妙万物而为言,盖绝世而弘博”,具有“殊怪必举”、“爱广向 奇”的特点,也就是说具有较为浓郁的文学色彩。批评对象的特 点决定了批评家在具体批评中不能无视志怪小说的文学特征而 一味地要求“影彻经史”。而且,从批评家主体方面说,虽然萧 绮站在儒家经史观的立场上去批评道家方士所写的志怪小说 但他却不是一个纯儒,不仅推崇王嘉所语怪、力、乱、神,而且 在录语中往往作诞漫无实的附会。这使得批评家既欲“削足适 履”以归附于经史,又欲彰明批评对象的志怪文学特征,在折衷 与游移中表现出了与《序》相牴牾而具有一定突破性的观点,所 谓“特取其爱博多奇之间,录其广异宏丽之靡”(卷一录语),就 是他整理和研究《拾遗记》所遵循的另一信条,从而使他的小说 思想具有了若干更有意义的内容。 这种新的意义首先表现在对那些与经史记载有差异的内容 能予以宽容,正确对待。如卷二《殷汤》条录语:“《诗》云: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斯文正矣。此说怀感而生,众言各异, 故记其殊别也。”认为虽与经史所载不吻合,也可权当一说。不 仅如此,他还能进一步突破经史观念,从小说角度对一些“似是 而非”的记载予以肯定。如《虞舜》条载舜时大频国使者来献方 物,夸耀其国“蛟以尾叩天求雨,鱼吸日之光”等神奇怪异的故 事。萧绮“录”日:“此言吸日而星雨皆坠,抑亦似是而非也。” 《周群》篇记猿变成老翁与周群谈论历代兴亡故事,萧“录”曰: “周群之学,通于神明,白猿之祥,有类越人问剑之言,其事迂 诞,若是而非也。”在萧绮看来,这些“若是而非”的历史事实 ·10·

的记载,仍有可观之处。又,《夏禹》篇录语云:“子年所述,涉 乎万古,与圣叶同,撻文求理,斯言如或可据。”并引用《尚 书》、《春秋传》的记载来对照,认为“详之正典,爰访杂说,若 真若似”。可以看出,他初步认识到了志怪小说的内容不一定完 全符合客观事实和历史记载,不一定拘泥于经典,只要能阐明道 理,内容上允许有虚幻成分的存在。尽管他的“实”是以经史为 依据,而且也没有进一步揭示虚与实之间的关系,但相对于同时 代的批评家以虚为实(郭璞)、“遂混虚实”(干宝)而言,他的 分辨显然使志怪小说向摆脱经史理论束缚的方向迈进了一步。 因为承认虚幻内容的存在,突破了史家“其事核,不虚美” 的实录精神,所以,萧绮对《拾遗记》创作手法的认识,也就突 破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的限制,从而揭示了其虚 构、夸张等“华而不实”的表现手法。《拾遗记》内容多涉神怪, 幻想奇特,想像丰富。刘知幾说它“全构虚辞,用惊愚俗”,对 于这一特征,萧绮有更为具体的认识。如卷六《前汉下》载汉宣 帝时有东方背明之国贡来物品,“有浃日之稻,种之十旬而熟:有 翻形稻,言食者死而更生,天而有寿;有明清稻,食者延年也: 清肠稻,食一粒历年不饥。有摇枝粟,其枝长而弱,无风常摇, 食之益髓;有凤冠粟,似凤鸟之冠,食者多力;.有通明麻 食者夜行不持烛,.其北有草,名虹草,枝长一丈,叶如车轮 根大如毂,花似朝虹之色。”萧绮“录”日:“宣帝之世,有嘉谷 玄稷之祥,亦不说今之所生,岂由神农、后稷播厥之功,抑亦王 子所称,非近俗所食。诠其名,华而不实。及乎飞走之类,神木 怪草,见奇而说,万世之瑰伟也。”《拾遗记》所载异物诸如“浮 绕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周而复始”的“贯月槎”、“舟形似螺, 沉行海底而水不浸人”的“沦波舟”、“暗中视物如昼,向镜语, 则镜中影应声而答”的“火齐镜”,以及“喊金鸟”、“骈蹄牛”、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