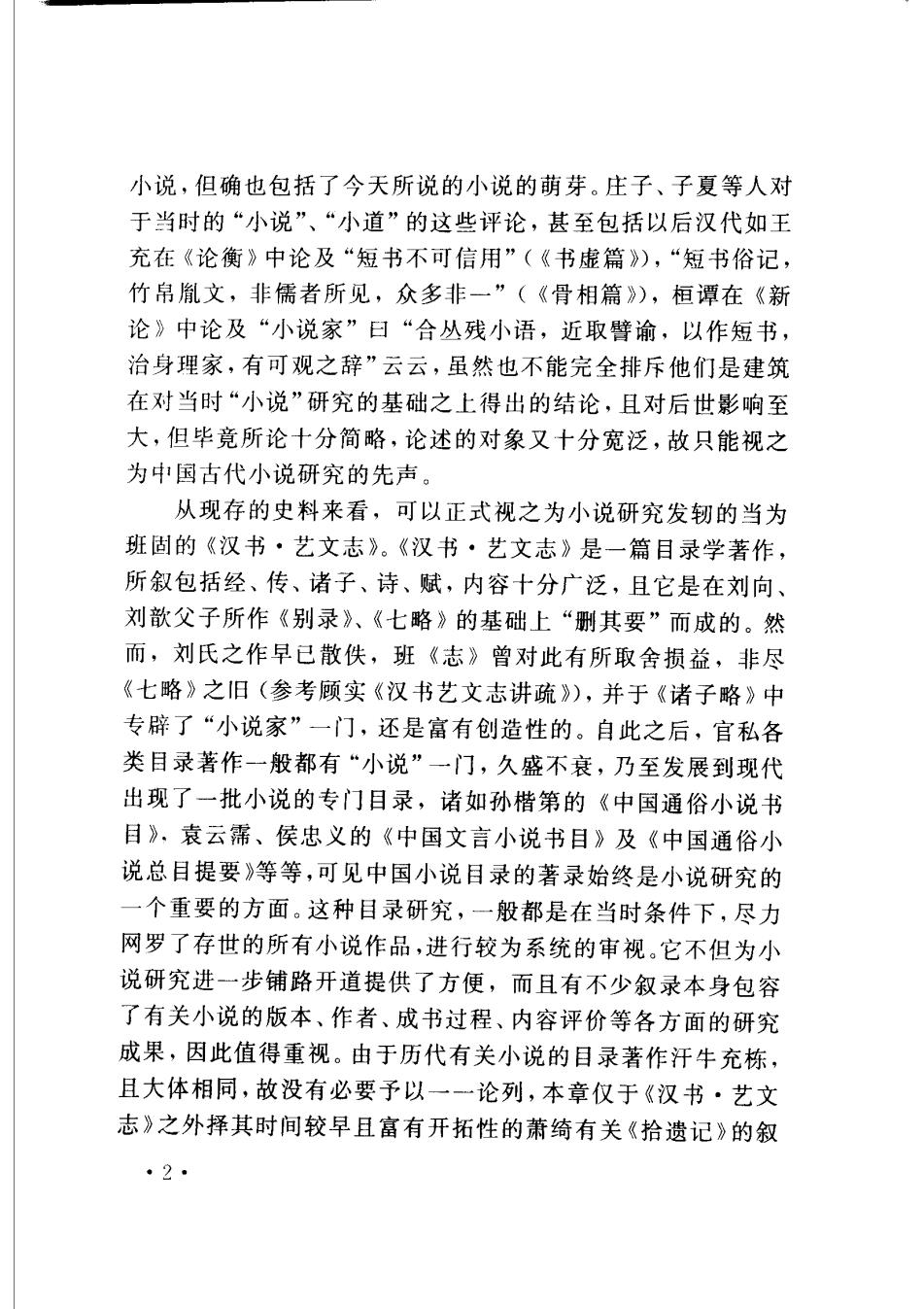
小说,但确也包括了今天所说的小说的萌芽。庄子、子夏等人对 于当时的“小说”、“小道”的这些评论,甚至包括以后汉代如王 充在《论衡》中论及“短书不可信用”(《书虚篇》),“短书俗记, 竹帛胤文,非儒者所见,众多非一”(《骨相篇》),桓谭在《新 论》中论及“小说家”日“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谕,以作短书, 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云云,虽然也不能完全排斥他们是建筑 在对当时“小说”研究的基础之上得出的结论,且对后世影响至 大,但毕竟所论十分简略,论述的对象又十分宽泛,故只能视之 为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先声。 从现存的史料来看,可以正式视之为小说研究发轫的当为 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汉书·艺文志》是一篇目录学著作, 所叙包括经、传、诸子、诗、赋,内容十分广泛,且它是在刘向、 刘歆父子所作《别录》、《七略》的基础上“删其要”而成的。然 而,刘氏之作早已散佚,班《志》曾对此有所取舍损益,非尽 《七略》之旧(参考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并于《诸子略》中 专辟了“小说家”一门,还是富有创造性的。自此之后,官私各 类目录著作一般都有“小说”一门,久盛不衰,乃至发展到现代 出现了一批小说的专门目录,诸如孙楷第的《中国通俗小说书 目》,袁云霈、侯忠义的《中国文言小说书目》及《中国通俗小 说总目提要》等等,可见中国小说目录的著录始终是小说研究的 一个重要的方面。这种目录研究,一般都是在当时条件下,尽力 网罗了存世的所有小说作品,进行较为系统的审视。它不但为小 说研究进一步铺路开道提供了方便,而且有不少叙录本身包容 了有关小说的版本、作者、成书过程、内容评价等各方面的研究 成果,因此值得重视。由于历代有关小说的目录著作汗牛充栋 且大体相同,故没有必要予以一一论列,本章仅于《汉书·艺文 志》之外择其时间较早且富有开拓性的萧绮有关《拾遗记》的叙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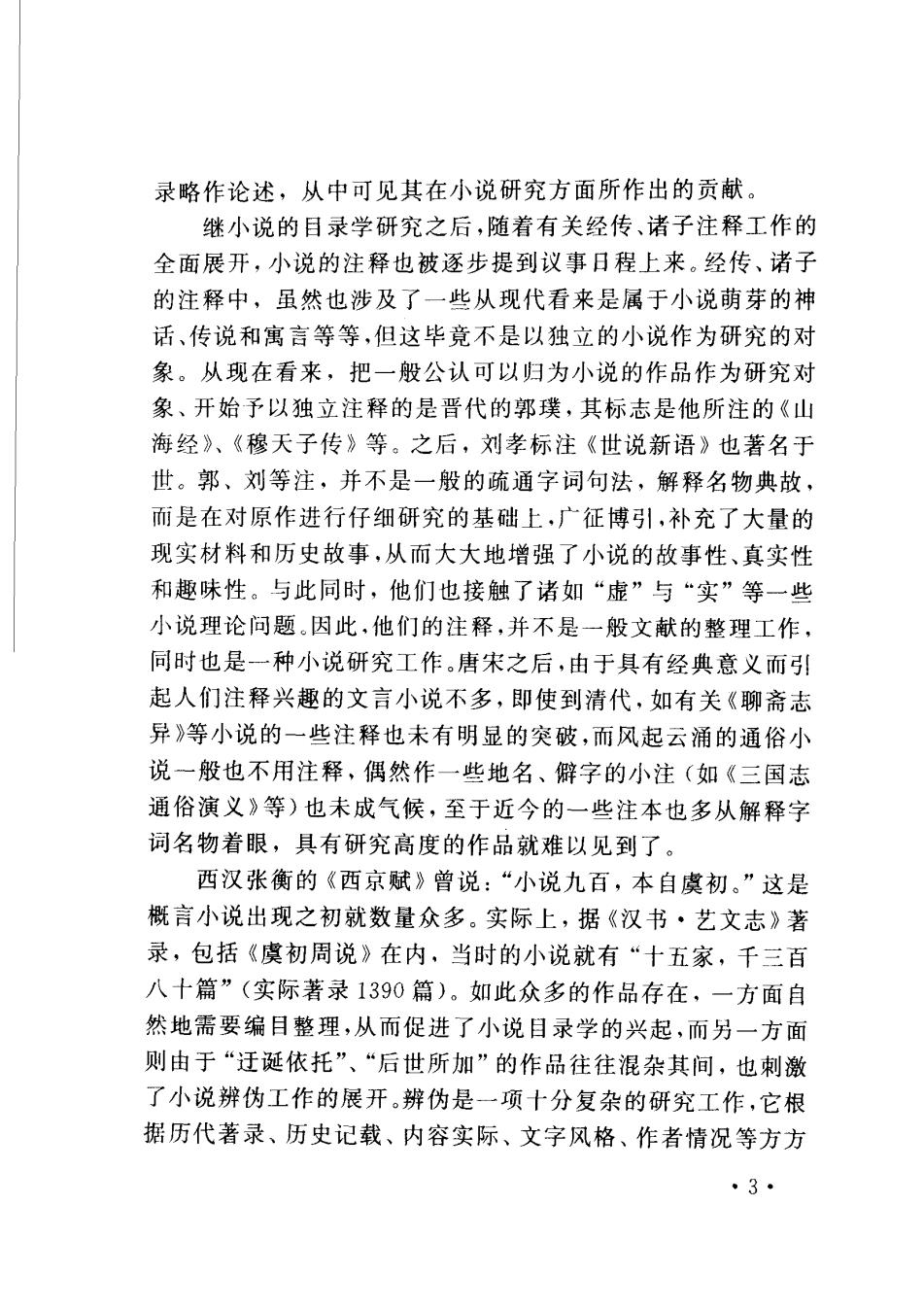
录略作论述,从中可见其在小说研究方面所作出的贡献。 继小说的目录学研究之后,随着有关经传、诸子注释工作的 全面展开,小说的注释也被逐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经传、诸子 的注释中,虽然也涉及了一些从现代看来是属于小说萌芽的神 话、传说和寓言等等,但这毕竞不是以独立的小说作为研究的对 象。从现在看来,把一般公认可以归为小说的作品作为研究对 象、开始予以独立注释的是晋代的郭璞,其标志是他所注的《山 海经》、《穆天子传》等。之后,刘孝标注《世说新语》也著名于 世。郭、刘等注,并不是一般的疏通字词句法,解释名物典故, 而是在对原作进行仔细研究的基础上,广征博引,补充了大量的 现实材料和历史故事,从而大大地增强了小说的故事性、真实性 和趣味性。与此同时,他们也接触了诸如“虚”与“实”等一些 小说理论问题。因此,他们的注释,并不是一般文献的整理工作, 同时也是一种小说研究工作。唐宋之后,由于具有经典意义而引 起人们注释兴趣的文言小说不多,即使到清代,如有关《聊斋志 异》等小说的一些注释也未有明显的突破,而风起云涌的通俗小 说一般也不用注释,偶然作一些地名、僻字的小注(如《三国志 通俗演义》等)也未成气候,至于近今的一些注本也多从解释字 词名物着眼,具有研究高度的作品就难以见到了。 西汉张衡的《西京赋》曾说:“小说九百,本自虞初。”这是 概言小说出现之初就数量众多。实际上,据《汉书·艺文志》著 录,包括《虞初周说》在内、当时的小说就有“十五家,千三百 八十篇”(实际著录1390篇)。如此众多的作品存在,一方面自 然地需要编目整理,从而促进了小说目录学的兴起,而另一方面 则由于“迂诞依托”、“后世所加”的作品往往混杂其间,也刺激 了小说辨伪工作的展开。辨伪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研究工作,它根 据历代著录、历史记载、内容实际、文字风格、作者情况等方方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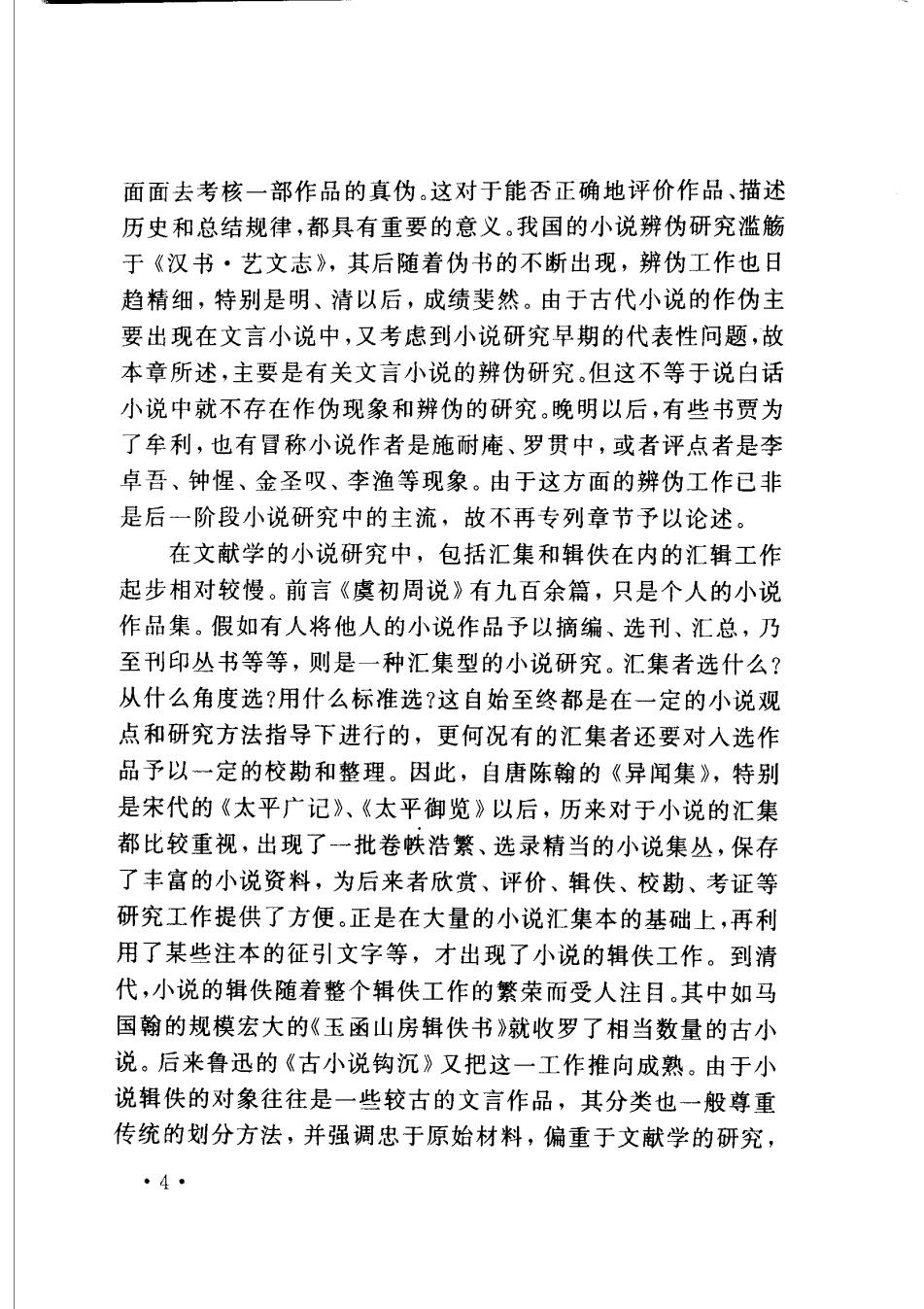
面面去考核一部作品的真伪。这对于能否正确地评价作品、描述 历史和总结规律,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的小说辨伪研究滥觞 于《汉书·艺文志》,其后随着伪书的不断出现,辨伪工作也日 趋精细,特别是明、清以后,成绩斐然。由于古代小说的作伪主 要出现在文言小说中,又考虑到小说研究早期的代表性问题,故 本章所述,主要是有关文言小说的辨伪研究。但这不等于说白话 小说中就不存在作伪现象和辨伪的研究。晚明以后,有些书贾为 了牟利,也有冒称小说作者是施耐庵、罗贯中,或者评点者是李 卓吾、钟惺、金圣叹、李渔等现象。由于这方面的辨伪工作已非 是后一阶段小说研究中的主流,故不再专列章节予以论述。 在文献学的小说研究中,包括汇集和辑佚在内的汇辑工作 起步相对较慢。前言《虞初周说》有九百余篇,只是个人的小说 作品集。假如有人将他人的小说作品予以摘编、选刊、汇总,乃 至刊印丛书等等,则是一种汇集型的小说研究。汇集者选什么? 从什么角度选?用什么标准选?这自始至终都是在一定的小说观 点和研究方法指导下进行的,更何况有的汇集者还要对人选作 品予以一定的校勘和整理。因此,自唐陈翰的《异闻集》,特别 是宋代的《太平广记》、《太平御览》以后,历来对于小说的汇集 都比较重视,出现了一批卷軼浩繁、选录精当的小说集丛,保存 了丰富的小说资料,为后来者欣赏、评价、辑佚、校勘、考证等 研究工作提供了方便。正是在大量的小说汇集本的基础上,再利 用了某些注本的征引文字等,才出现了小说的辑佚工作。到清 代,小说的辑佚随着整个辑佚工作的繁荣而受人注目。其中如马 国翰的规模宏大的《玉函山房辑佚书》就收罗了相当数量的古小 说。后来鲁迅的《古小说钩沉》又把这一工作推向成熟。由于小 说辑佚的对象往往是一些较古的文言作品,其分类也一般尊重 传统的划分方法,并强调忠于原始材料,偏重于文献学的研究,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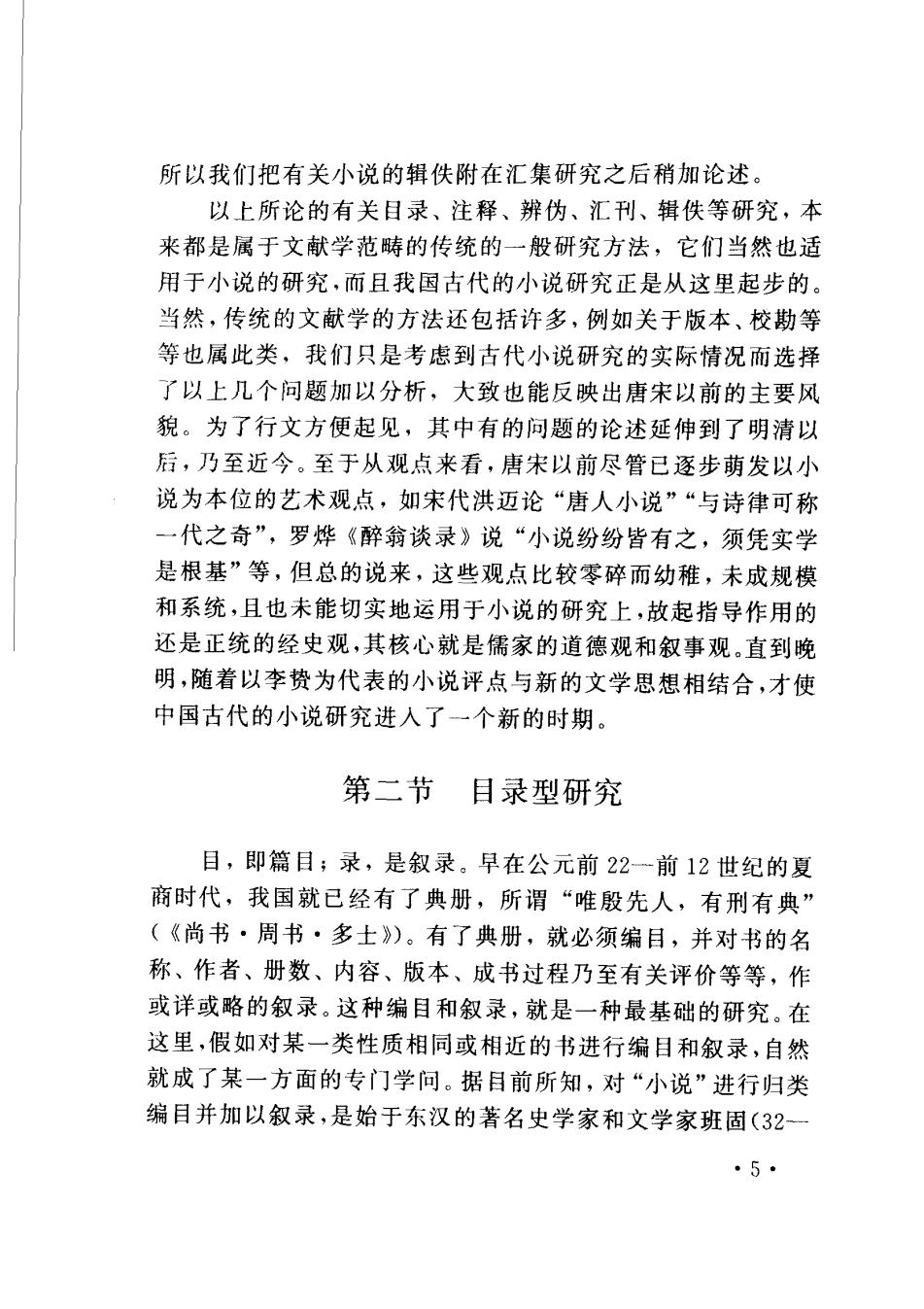
所以我们把有关小说的辑佚附在汇集研究之后稍加论述。 以上所论的有关目录、注释、辨伪、汇刊、辑佚等研究,本 来都是属于文献学范畴的传统的一般研究方法,它们当然也适 用于小说的研究,而且我国古代的小说研究正是从这里起步的。 当然,传统的文献学的方法还包括许多,例如关于版本、校勘等 等也属此类,我们只是考虑到古代小说研究的实际情况而选择 了以上几个问题加以分析,大致也能反映出唐宋以前的主要风 貌。为了行文方便起见,其中有的问题的论述延伸到了明清以 后,乃至近今。至于从观点来看,唐宋以前尽管已逐步萌发以小 说为本位的艺术观点,如宋代洪迈论“唐人小说”“与诗律可称 一代之奇”,罗烨《醉翁谈录》说“小说纷纷皆有之,须凭实学 是根基”等,但总的说来,这些观点比较零碎而幼稚,未成规模 和系统,且也未能切实地运用于小说的研究上,故起指导作用的 还是正统的经史观,其核心就是儒家的道德观和叙事观。直到晚 明,随着以李贽为代表的小说评点与新的文学思想相结合,才使 中国古代的小说研究进人了一个新的时期。 第二节目录型研究 目,即篇目;录,是叙录。早在公元前22一前12世纪的夏 商时代,我国就已经有了典册,所谓“唯殷先人,有刑有典” (《尚书·周书·多土》)。有了典册,就必须编目,并对书的名 称、作者、册数、内容、版本、成书过程乃至有关评价等等,作 或详或略的叙录。这种编目和叙录,就是一种最基础的研究。在 这里,假如对某一类性质相同或相近的书进行编目和叙录,自然 就成了某一方面的专门学问。据目前所知,对“小说”进行归类 编目并加以叙录,是始于东汉的著名史学家和文学家班固(32 ·5

92)的《汉书·艺文志》。此书在《诸子略》中特立了“小说” 门,撮录了“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按:实录1390篇)”: 《伊尹说》二十七篇。(其语浅薄,似依托也。) 《鬻子说》十九篇。(后世所加。) 《周考》七十六篇。(考周事也。) 《青史子》五十七篇。(古史官记事也。) 《师旷》六篇。(见《春秋》,其言浅薄,本与此同,似 因托之。) 《务成子》十一篇。(称“尧问”,非古语。) 《宋子》十八篇。(孙卿道:“《宋子》,其言黄老意。”) 《天乙》三篇。(天乙谓汤,其言非殷时,皆依托也。) 《黄帝说》四十篇。(迁诞依托。) 《封禅方说》十八篇。(武帝时。) 《待诏臣饶心术》二十五篇。(武帝时。) 《待诏臣安成未央术》一篇。 《臣寿周纪》七篇。(项国围人,宣帝时。) 《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侍 郎,号黄车使者。) 《百家》百三十九卷。 右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 造也。孔子日:“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 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 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乌荛狂夫之议也。 据班固《艺文志序》自言,其《艺文志》篇是在刘向《别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