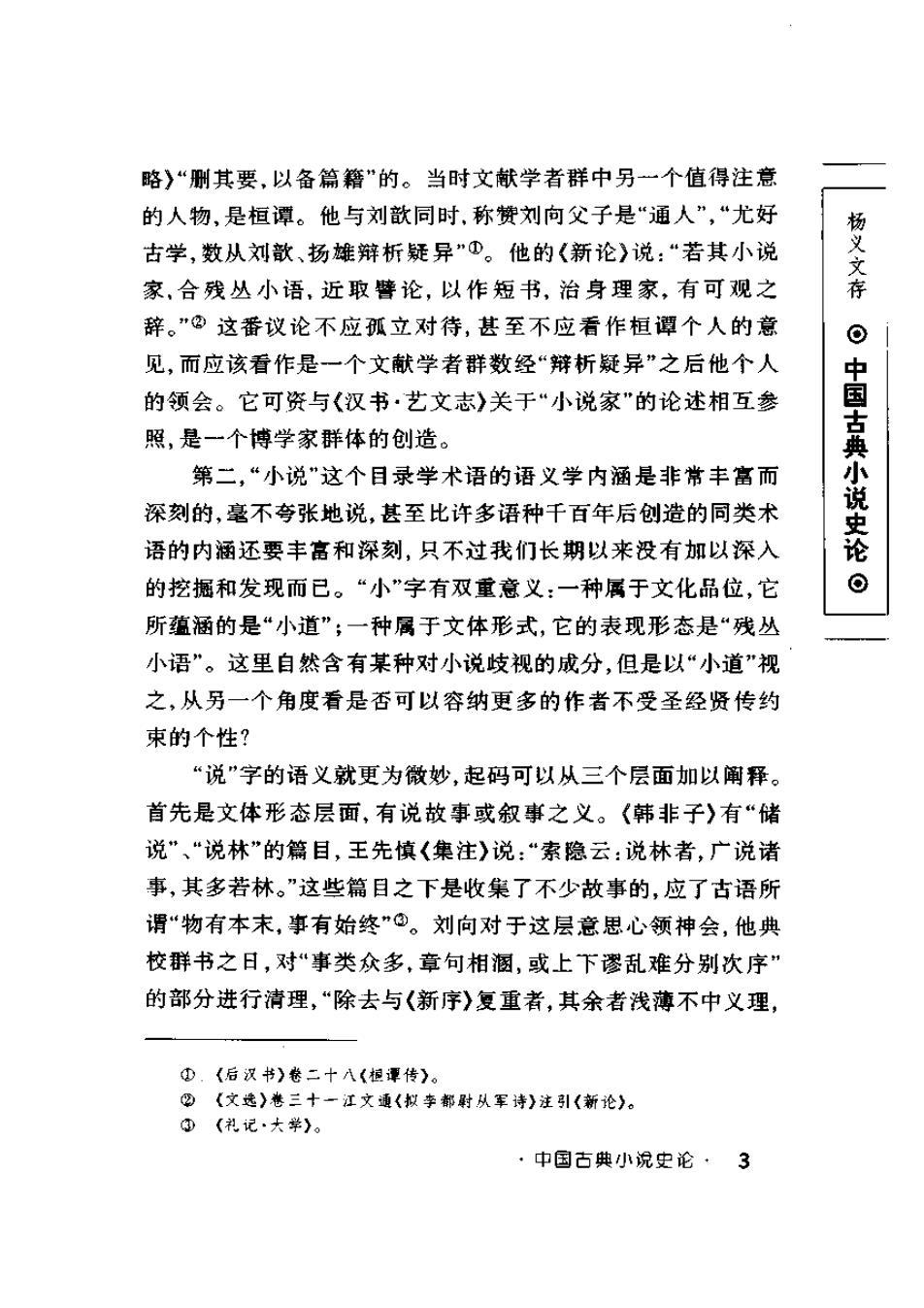
略》“删其要,以备篇籍”的。当时文献学者群中另一个值得注意 的人物,是桓谭。他与刘歆同时.称赞刘向父子是“通人”,“尤好 古学,数从刘歆、扬雄辩析疑异”①。他的《新论》说:“若其小说 家,合残丛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 存 辞。”②这番议论不应孤立对待,甚至不应看作桓谭个人的意 ⊙ 见,而应该看作是一个文献学者群数经“辩析疑异”之后他个人 的领会。它可资与《汉书·艺文志》关于“小说家”的论述相互参 国 照,是一个博学家群体的创造。 典 第二,“小说“这个目录学术语的语义学内涵是非常丰富而 深刻的,毫不夸张地说,甚至比许多语种千百年后创造的同类术 语的内涵还要丰富和深刻,只不过我们长期以来没有加以深入 的挖掘和发现而已。“小”字有双重意义:一种属于文化品位,它 所蕴涵的是“小道”;一种属于文体形式,它的表现形态是“残丛 小语”。这里自然含有某种对小说歧视的成分,但是以“小道”视 之,从另一个角度看是否可以容纳更多的作者不受圣经贤传约 束的个性? “说”字的语义就更为微妙,起码可以从三个层面加以阐释。 首先是文体形态层面,有说故事或叙事之义。《韩非子)有“储 说”、“说林”的篇目,王先慎《集注》说:“索隐云:说林者,广说诸 事,其多若林。”这些篇目之下是收集了不少故事的,应了古语所 谓“物有本末,事有始终”⊙。刘向对于这层意思心领神会,他典 校群书之日,对“事类众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谬乱难分别次序 的部分进行清理,“除去与(新序)复重者,其余者浅薄不中义理, ①.《后汉书)卷二十八《根潭传)。 ②(文选》卷三十一江文通《拟李都时从军诗)注引(新论)。 闭(刘记·大学》 ·中国古典小说史论·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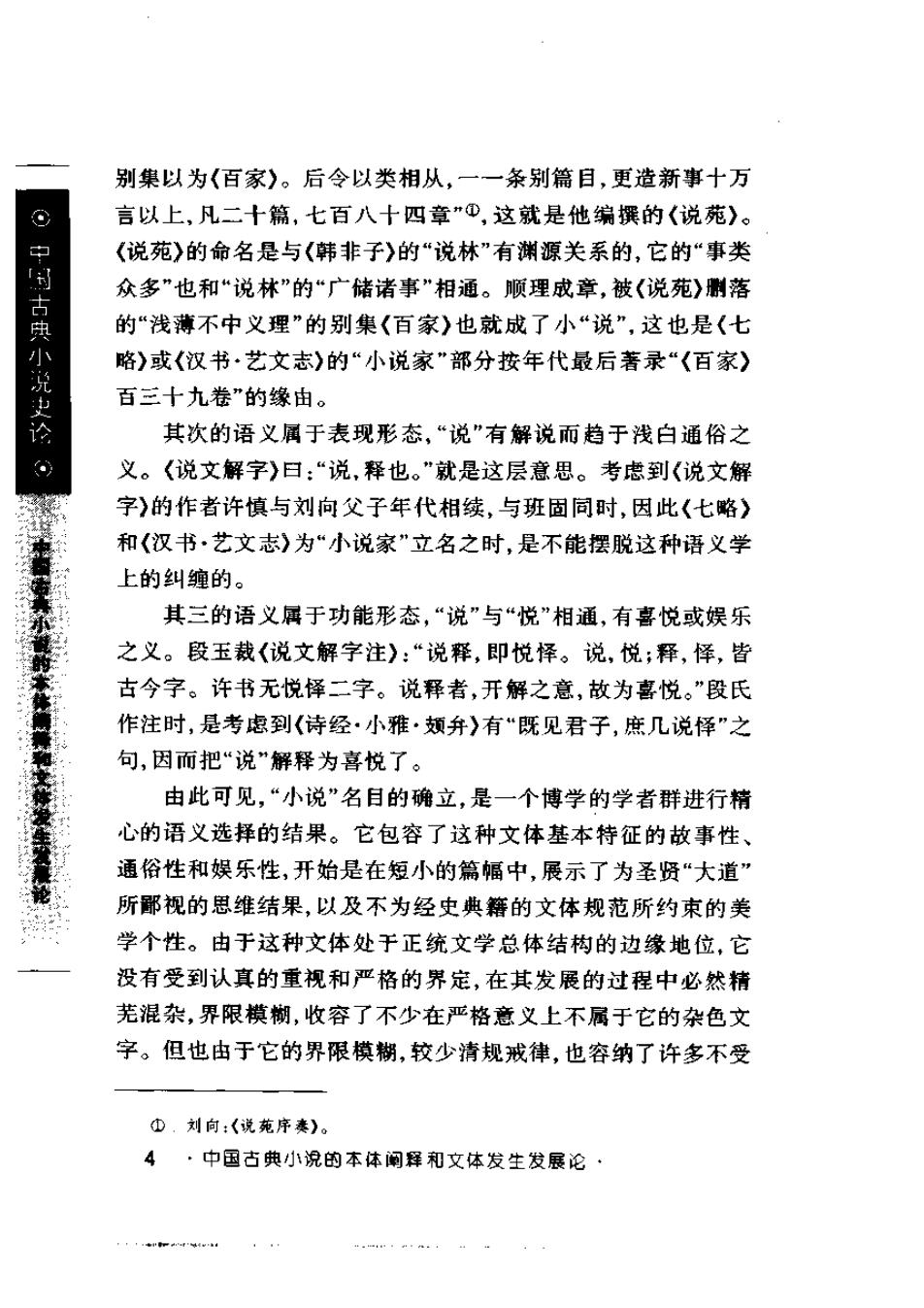
别集以为(百家)。后令以类相从,一一条别篇目,更造新事十万 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①,这就是他编撰的《说苑》。 中 (说苑》的命名是与(韩非子》的“说林”有渊源关系的,它的“事类 众多”也和“说林”的“广储诸事”相通。顺理成章,被《说苑》删落 的“浅薄不中义理”的别集〈百家)也就成了小“说”,这也是(七 小 略》或《汉书·艺文志》的“小说家“部分按年代最后著录“〈百家) 百三十九卷”的缘由。 论 其次的语义属于表现形态,“说”有解说而趋于浅白通俗之 义。〈说文解字)日:“说,释也。”就是这层意思。考虑到《说文解 字〉的作者许慎与刘向父子年代相续,与班固同时,因此(七略》 和《汉书·艺文志》为“小说家”立名之时,是不能摆脱这种语义学 上的纠缠的。 其三的语义属于功能形态,“说”与“悦”相通,有喜悦或娱乐 之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释,即悦怿。说,悦;释,怿,皆 古今字。许书无悦怿二字。说释者,开解之意,故为喜悦。”段氏 作注时,是考虑到(诗经·小雅·類弁》有“既见君子,庶几说怿”之 句,因而把“说”解释为喜悦了。 由此可见,“小说”名目的确立,是一个博学的学者群进行精 心的语义选择的结果。它包容了这种文体基本特征的故事性 通俗性和娱乐性,开始是在短小的篇幅中,展示了为圣贤“大道” 所鄙视的思维结果,以及不为经史典籍的文体规范所约束的美 学个性。由于这种文体处于正统文学总体结构的边缘地位,它 没有受到认真的重视和严格的界定,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必然精 芜混杂,界限模糊,收容了不少在严格意义上不属于它的杂色文 字。但也由于它的界限模糊,较少清规戒律,也容纳了许多不受 ①。刘向:(说苑序秦》 4·中国古典小说的本体闸释和文体发生发展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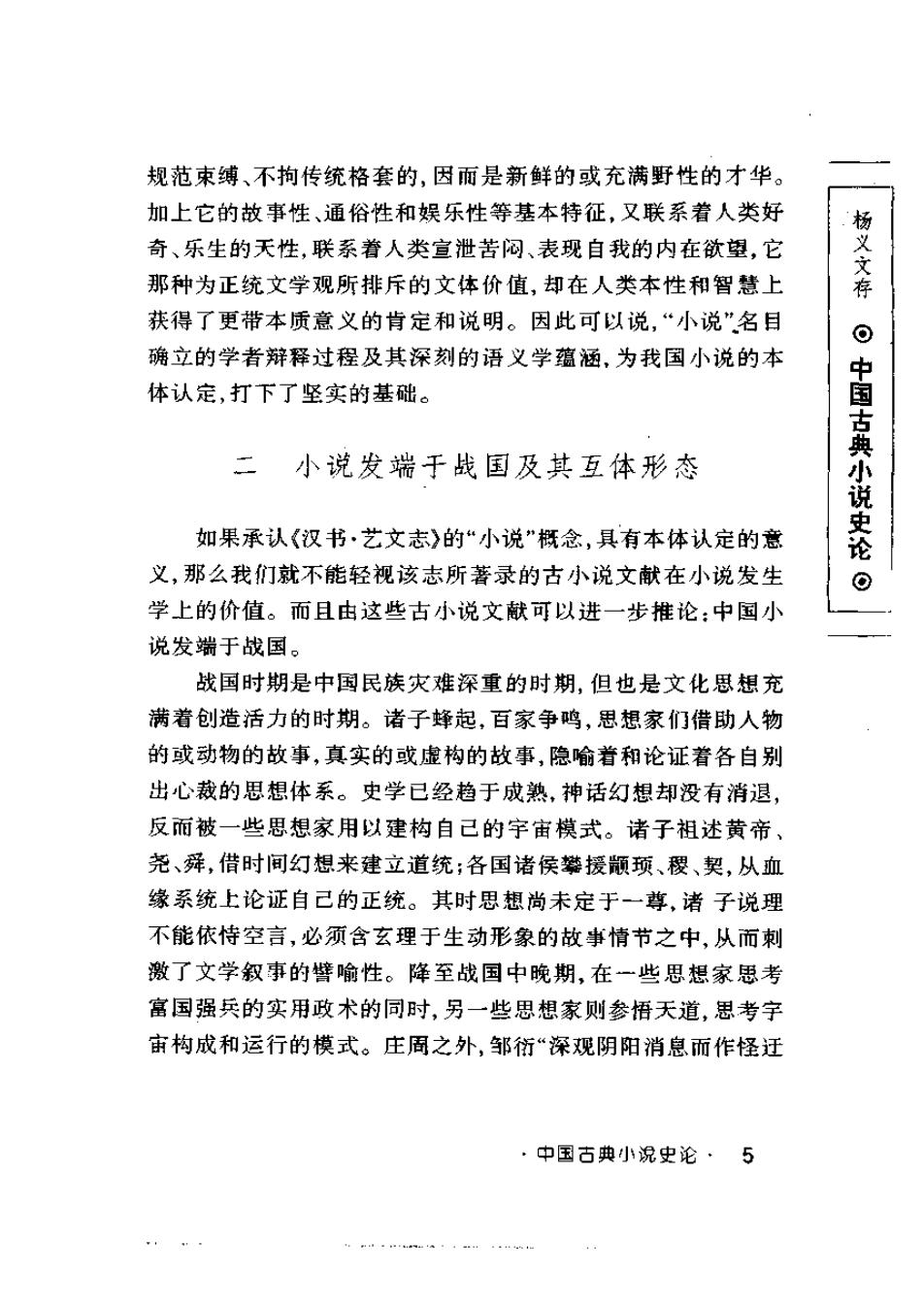
规范束缚、不拘传统格套的,因而是新鲜的或充满野性的才华。 加上它的故事性、通俗性和娱乐性等基本特征,又联系着人类好 奇、乐生的天性,联系着人类宣泄苦闷、表现自我的内在欲望,它 那种为正统文学观所排斥的文体价值,却在人类本性和智慧上 义文存 获得了更带本质意义的肯定和说明。因此可以说,“小说”名目 0 确立的学者辩释过程及其深刻的语义学蕴涵,为我国小说的本 体认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小说发端于战国及其互体形态 小说 如果承认《汉书·艺文志》的“小说”概念,具有本体认定的意 论 义,那么我们就不能轻视该志所著录的古小说文献在小说发生 学上的价值。而且由这些古小说文献可以进一步推论:中国小 说发端于战国。 战国时期是中国民族灾难深重的时期,但也是文化思想充 满着创造活力的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思想家们借助人物 的或动物的故事,真实的或虚构的故事,隐喻着和论证着各自别 出心裁的思想体系。史学已经趋于成熟,神话幻想却没有消退 反而被一些思想家用以建构自己的宇宙模式。诸子祖述黄帝 尧、舜,借时间幻想来建立道统;各国诸侯攀援颛顼、稷、契,从血 缘系统上论证自己的正统。其时思想尚未定于一尊,诸子说理 不能依恃空言,必须含玄理于生动形象的故事情节之中,从而刺 激了文学叙事的譬喻性。降至战国中晚期,在一些思想家思考 富国强兵的实用政术的同时,另一些思想家则参悟天道,思考字 宙构成和运行的模式。庄周之外,邹衍“深规阴阳消息而作怪迁 ·中国古典小说史论·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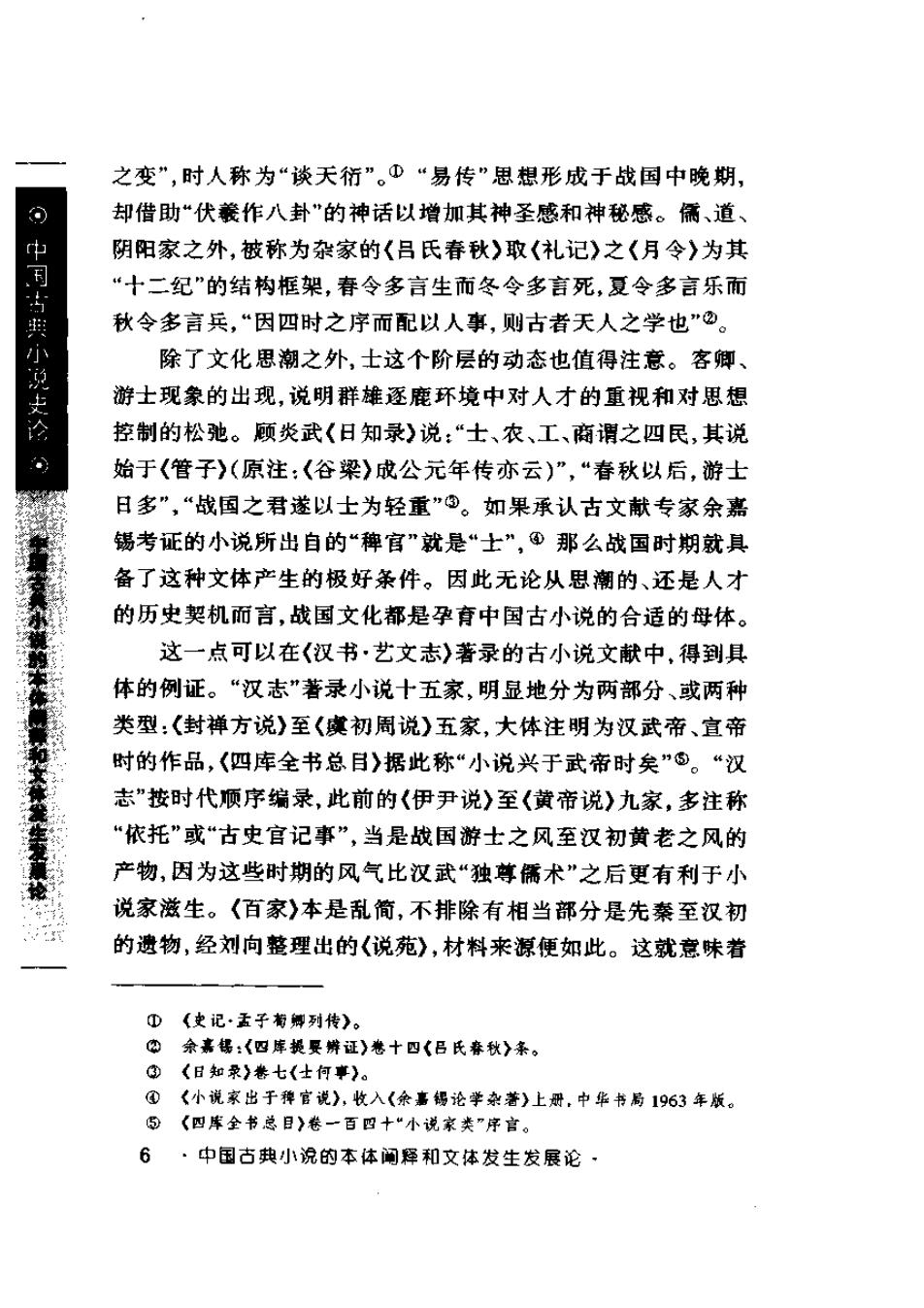
之变”,时人称为“谈天衍”。少“易传”思想形成于战国中晚期, 却借助“伏羲作八卦”的神话以增加其神圣感和神秘感。儒、道 中国 阴阳家之外,被称为杂家的《吕氏春秋)取《礼记》之《月令》为其 “十二纪”的结构框架,春令多言生而冬令多言死,夏令多言乐而 秋令多言兵,“因四时之序而配以人事,则古者天人之学也”②。 除了文化思潮之外,士这个阶层的动态也值得注意。客卿 游士现象的出现,说明群雄逐鹿环境中对人才的重视和对思想 控制的松驰。顾炎武《日知录)说:“士、农、工、商调之四民,其说 始于(管子)(原注:(谷梁》成公元年传亦云)”,“春秋以后,游士 日多”,“战国之君遂以士为轻重”⑤。如果承认古文献专家余嘉 锡考证的小说所出自的“稗官”就是“士”,④那么战国时期就具 备了这种文体产生的极好条件。因此无论从思潮的、还是人才 的历史契机而言,战国文化都是孕育中国古小说的合适的母体。 这一点可以在(《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古小说文献中,得到具 体的例证。“汉志”著录小说十五家,明显地分为两部分、或两种 类型:(封禅方说)至《虞初周说)五家,大体注明为汉武帝、宜帝 时的作品,《四库全书总目》据此称“小说兴于武帝时矣”⑤。“汉 志”按时代顺序编录,此前的《伊尹说》至《黄帝说》九家,多注称 “依托”或“古史官记事”,当是战国游士之风至汉初黄老之风的 产物,因为这些时期的风气比汉武“独尊儒术”之后更有利于小 说家滋生。〈百家)本是乱简,不排除有相当部分是先秦至汉初 的遗物,经刘向整理出的(说苑》,材料来源便如此。这就意味着 ①《史记·盂子葡舞列传》。 心余嘉锡:《四库要辨证)卷十四《B氏春秋》来。 《日知录》卷七(士何事)。 ④《小说家出于弹官说),收入(余嘉锡论学杂著)上册,中张书局1963年版。 ⑤《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小说家类”序官。 6·中国古典小说的本体间释和文体发生发展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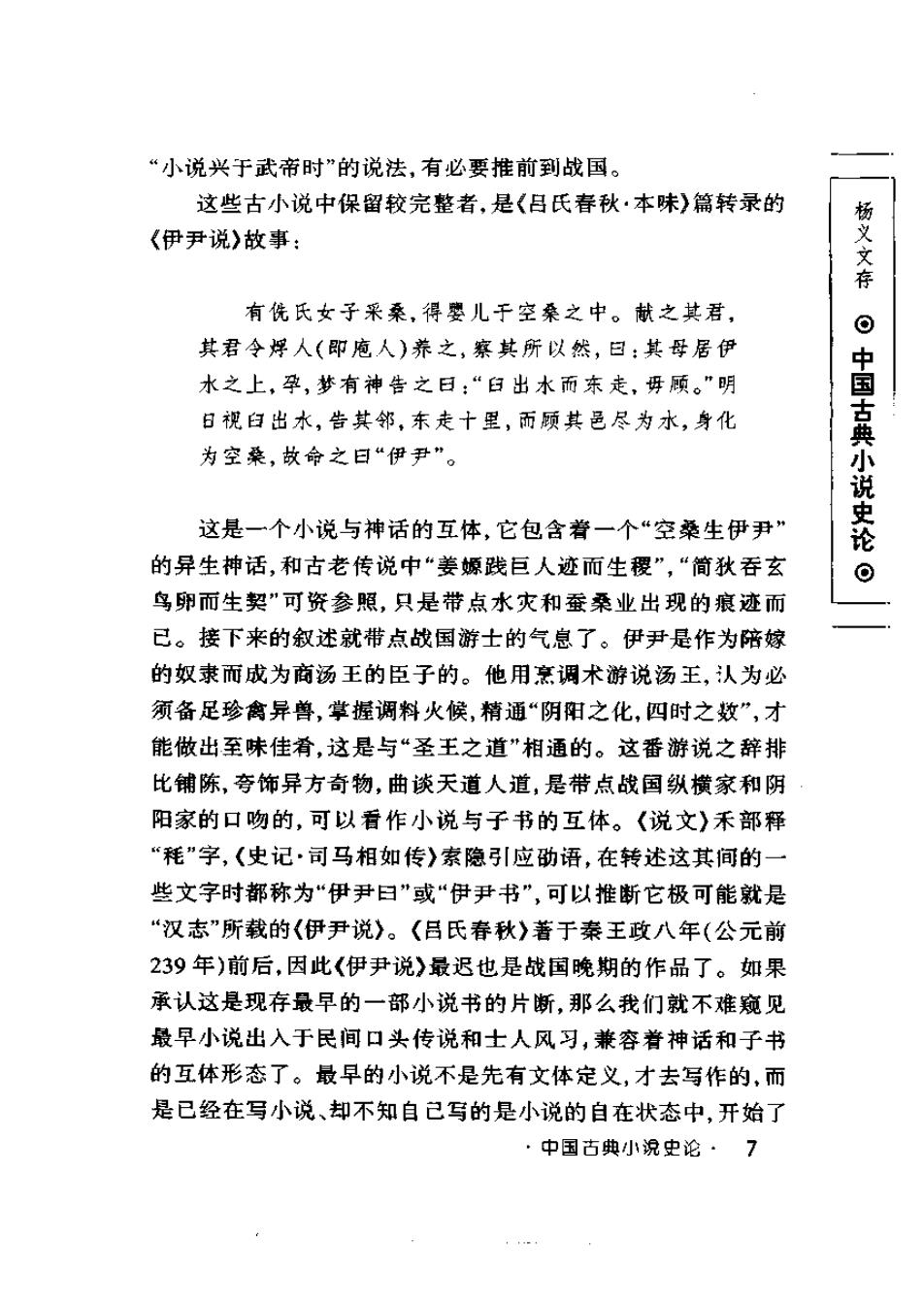
“小说兴于武帝时”的说法,有必要推前到战国。 这些古小说中保留较完整者,是《吕氏春秋·本味)篇转录的 《伊尹说》故事 义文存 有桃氏女子采桑,得婴儿于空桑之中。献之其君, ⊙ 其君令焊人(即庖人)养之,察其所以然,日:其母居伊 水之上,孕,梦有神告之日:“臼出水而东走,毋顾。”明 中国 日视白出水,告其邻,东走十里,而顾其邑尽为水,身化 为空桑,故命之日“伊尹”。 这是一个小说与神话的互体,它包含着一个“空桑生伊尹” 论 的异生神话,和古老传说中“姜螈践巨人迹而生稷”,“简秋吞玄 鸟卵而生契”可资参照,只是带点水灾和蚕桑业出现的痕迹而 已。接下来的叙述就带点战国游士的气息了。伊尹是作为陪嫁 的奴隶而成为商汤王的臣子的。他用烹调术游说汤王,认为必 须备足珍禽异兽,掌握调料火候,精通“阴阳之化,四时之数”,才 能做出至味佳肴,这是与“圣王之道”相通的。这番游说之辞排 比铺陈,夸饰异方奇物,曲谈天道人道,是带点战国纵横家和阴 阳家的口吻的,可以看作小说与子书的互体。《说文》禾部释 “耗”字,(史记·司马相如传)索隐引应劭语,在转述这其间的一 些文字时都称为“伊尹日”或“伊尹书”,可以推断它极可能就是 “汉志”所载的(伊尹说》。〈吕氏春秋)著于秦王政八年(公元前 239年)前后,因此(伊尹说》最迟也是战国晚期的作品了。如果 承认这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小说书的片断,那么我们就不难窥见 最早小说出入于民间口头传说和士人风习,兼容着神话和子书 的互体形态了。最早的小说不是先有文体定义,才去写作的,而 是已经在写小说、却不知自己写的是小说的自在状态中,开始了 ·中国古典小说史论·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