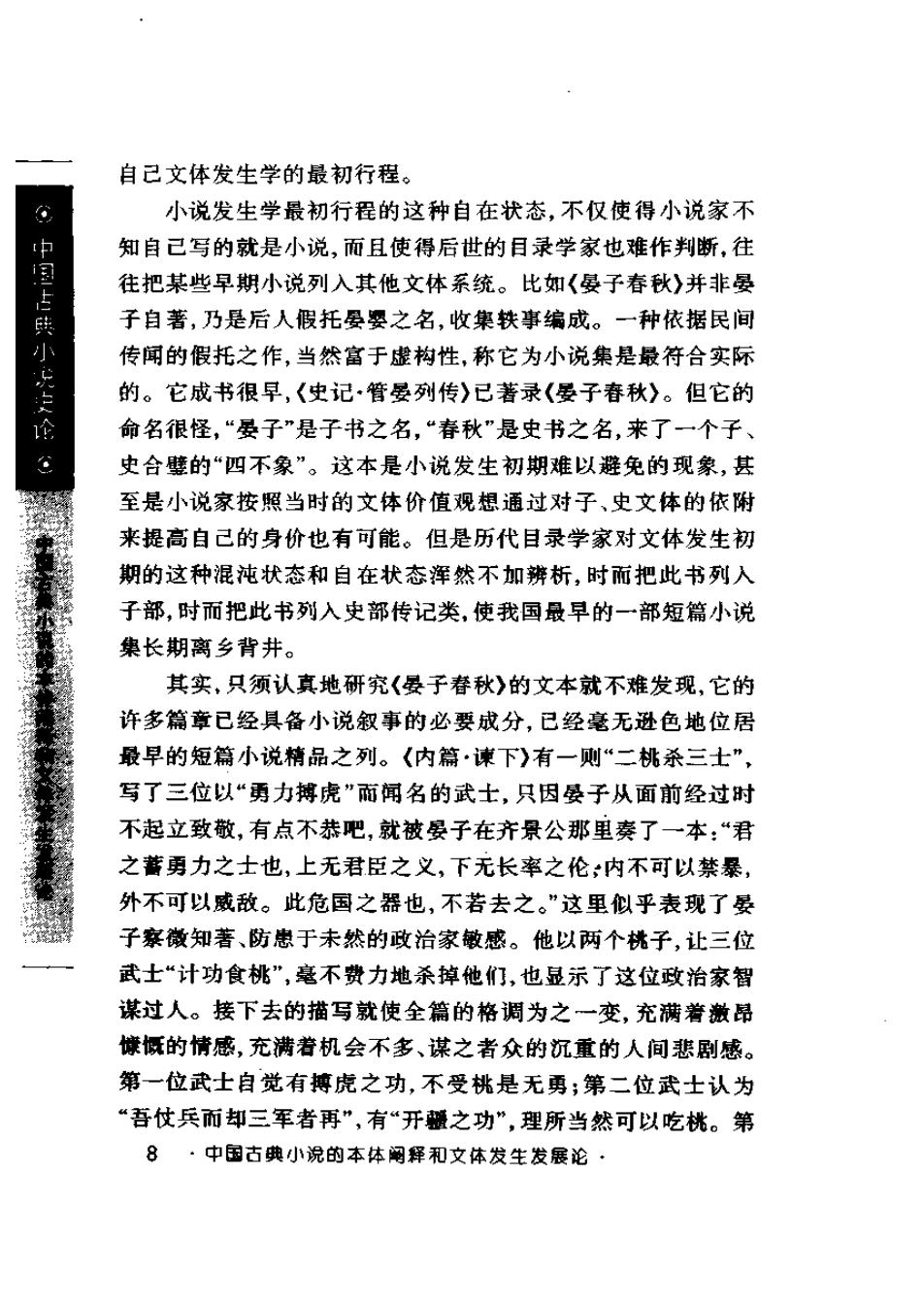
自己文体发生学的最初行程。 小说发生学最初行程的这种自在状态,不仅使得小说家不 知自已写的就是小说,而且使得后世的目录学家也难作判断,往 国 往把某些早期小说列入其他文体系统。比如《晏子春秋)并非晏 子自著,乃是后人假托晏婴之名,收集扶事编成。一种依据民间 传闻的假托之作,当然富于虚构性,称它为小说集是最符合实际 K 大论 的。它成书很早,〈史记,管晏列传》已著录(晏子春秋》。但它的 命名很怪,“晏子”是子书之名,“春秋”是史书之名,来了一个子 史合璧的“四不象”。这本是小说发生初期难以避免的现象,甚 至是小说家按照当时的文体价值观想通过对子、史文体的依附 来提高自己的身价也有可能。但是历代目录学家对文体发生初 期的这种混沌状态和自在状态浑然不加辨析,时而把此书列入 子部,时而把此书列入史部传记类,使我国最早的一一部短篇小说 集长期离乡背井。 其实,只须认真地研究《晏子春秋》的文本就不难发现,它的 许多篇章已经具备小说叙事的必要成分,已经毫无逊色地位居 最早的短篇小说精品之列。《内篇·谏下)有一则“二桃杀三士” 写了三位以“勇力搏虎”而闻名的武士,只因县子从面前经过时 不起立致敬,有点不恭吧,就被晏子在齐景公那里奏了一本:“君 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无君臣之义,下无长率之伦:内不可以禁暴, 外不可以威敌。此危国之器也,不若去之。”这里似乎表现了晏 子察徽知著、防患于未然的政治家敏感。他以两个桃子,让三位 武士“计功食桃”,毫不费力地杀掉他们,也显示了这位政治家智 谋过人。接下去的描写就使全篇的格调为之一变,充满着激昂 慷橱的情感,充满若机会不多、谋之者众的沉重的人间悲剧感。 第一位武士自觉有博虎之功,不受桃是无勇;第二位武士认为 “吾仗兵而却三军者再”,有“开疆之功”,理所当然可以吃桃。第 8·中国古典小说的本体阐释和文体发生发展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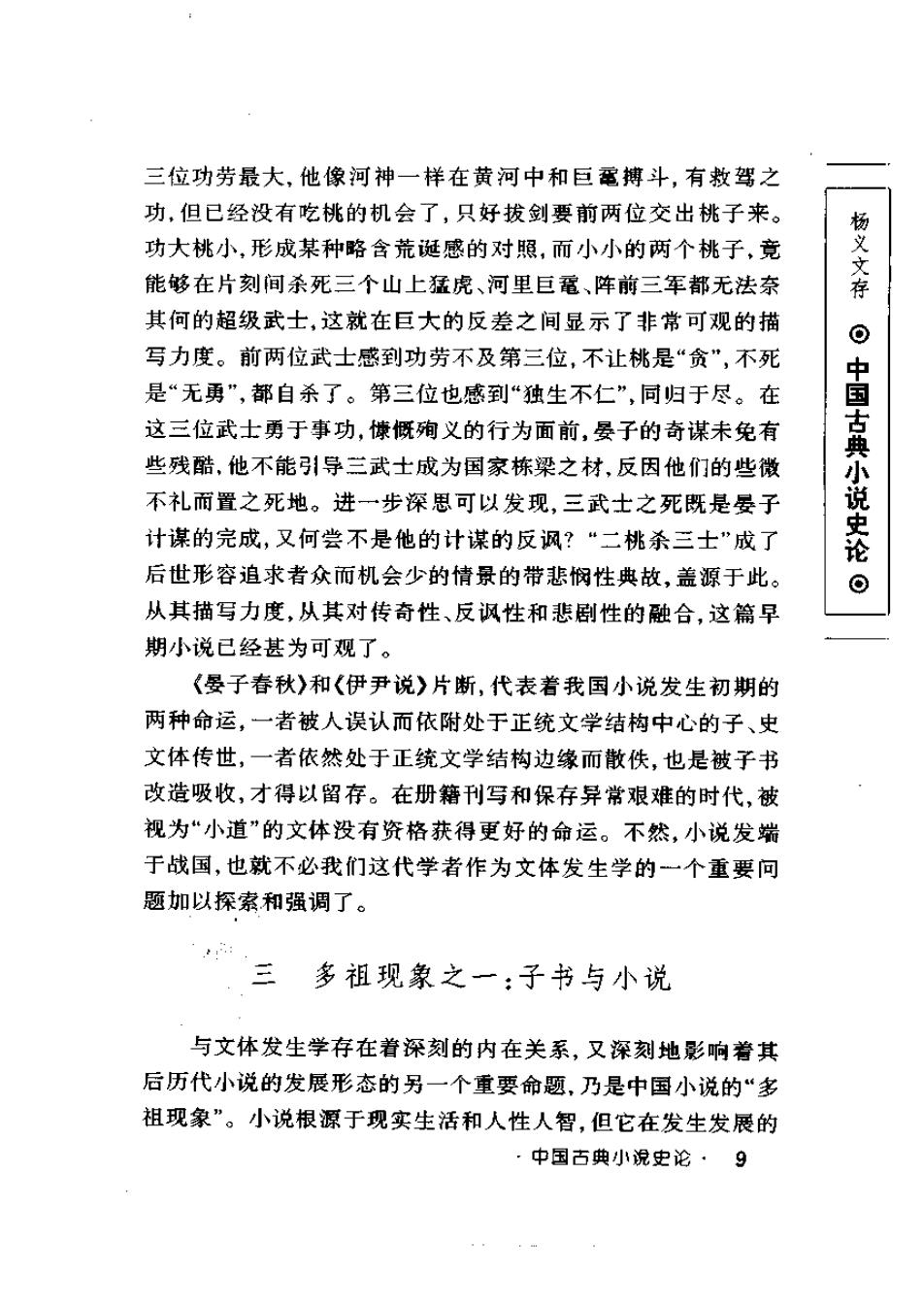
三位功劳最大,他像河神一样在黄河中和巨鼋搏斗,有救驾之 功,但已经没有吃桃的机会了,只好拔剑要前两位交出桃子来。 功大桃小,形成某种略含荒诞感的对照,而小小的两个桃子,竞 能够在片刻间杀死三个山上猛虎、河里巨鼋、阵前三军都无法奈 其何的超级武士,这就在巨大的反差之间显示了非常可观的描 ⊙ 写力度。前两位武士感到功劳不及第三位,不让桃是“贪”,不死 中 是“无勇”,都自杀了。第三位也感到“独生不仁”,同归于尽。在 这三位武士勇于事功,慷慨殉义的行为面前,晏子的奇谋未免有 些残酷,他不能引导三武士成为国家栋梁之材,反因他们的些微 不礼而置之死地。进一步深思可以发现,三武士之死既是晏子 计谋的完成,又何尝不是他的计谋的反讽?“二桃杀三士”成了 史论 后世形容追求者众而机会少的情景的带悲悯性典故,盖源于此。 ⊙ 从其描写力度,从其对传奇性、反讽性和悲剧性的融合,这篇早 期小说已经甚为可观了。 《晏子春秋)和《伊尹说》片断,代表着我国小说发生初期的 两种命运,一者被人误认而依附处于正统文学结构中心的子、史 文体传世,一者依然处于正统文学结构边缘而散佚,也是被子书 改造吸收,才得以留存。在册籍刊写和保存异常艰难的时代,被 视为“小道”的文体没有资格获得更好的命运。不然,小说发端 于战国,也就不必我们这代学者作为文体发生学的一个重要问 题加以探索和强调了。 三多祖现象之一:子书与小说 与文体发生学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关系,又深刻地影响着其 后历代小说的发展形态的另一个重要命题,乃是中国小说的“多 祖现象”。小说根源于现实生活和人性人智,但它在发生发展的 ·中国古典小说史论·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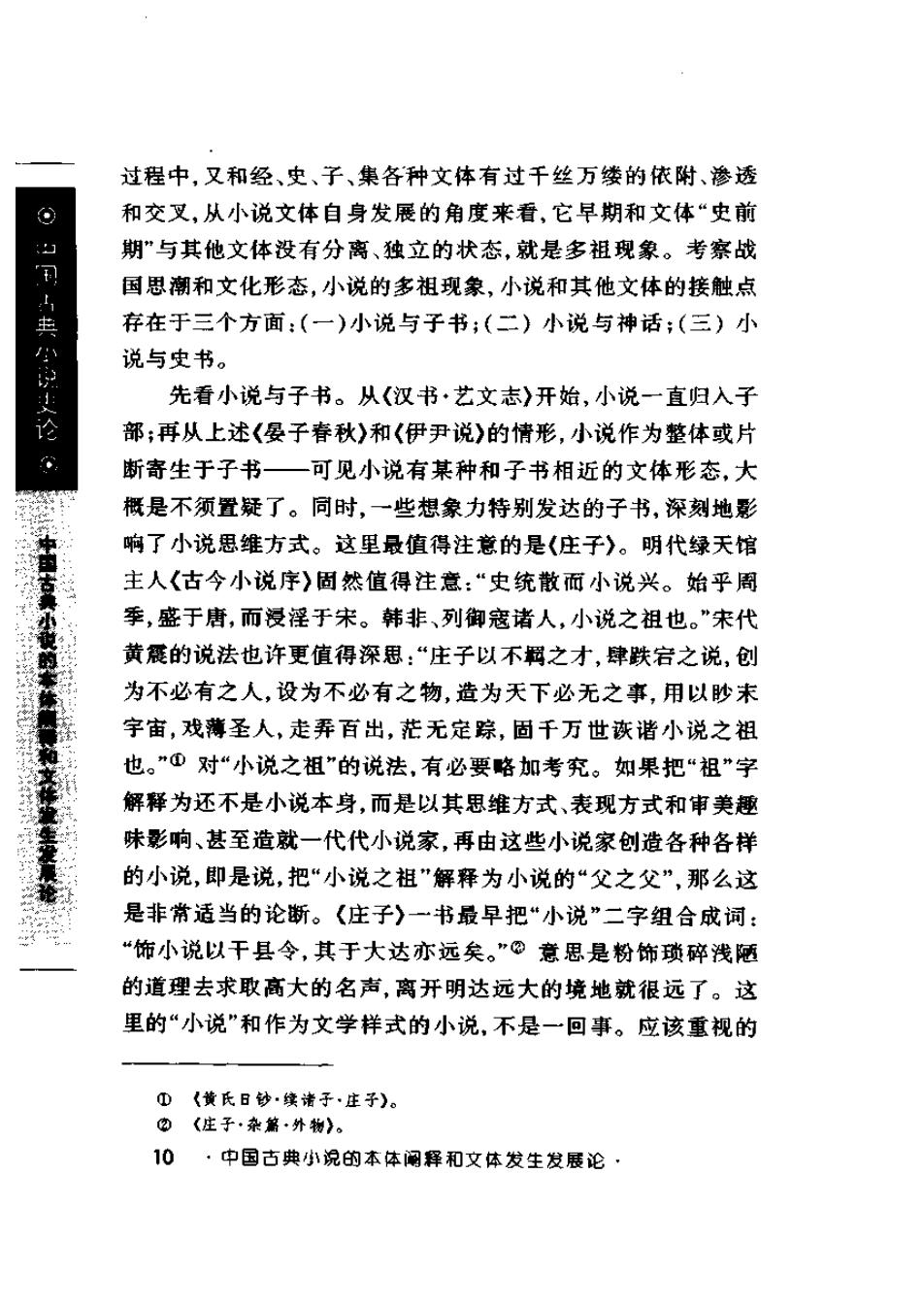
过程中,又和经、史、子、集各种文体有过千丝万缕的依附、渗透 ⊙ 和交叉,从小说文体自身发展的角度来看,它早期和文体“史前 期”与其他文体没有分离、独立的状态,就是多祖现象。考察战 国思潮和文化形态,小说的多祖现象,小说和其他文体的接触点 存在于三个方面:(一)小说与子书:(二)小说与神话:(三)小 说与史书。 先看小说与子书。从《汉书·艺文志》开始,小说一直归入子 论 部;再从上述(晏子春秋)和《伊尹说》的情形,小说作为整体或片 断寄生于子书一可见小说有某种和子书相近的文体形态,大 概是不须置疑了。同时,一些想象力特别发达的子书,深刻地影 响了小说思维方式。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庄子〉。明代绿天馆 主人《古今小说序》固然值得注意:“史统散而小说兴。始乎周 季,盛于唐,而浸淫于宋。韩非、列御寇诸人,小说之祖也。”宋代 黄展的说法也许更值得深思:“庄子以不羁之才,肆跌宕之说,创 为不必有之人,设为不必有之物,造为天下必无之事,用以眇末 字宙,戏薄圣人,走弄百出,花无定踪,固千万世诙谐小说之祖 也。”①对“小说之祖”的说法,有必要略加考究。如果把“祖”字 解释为还不是小说本身,而是以其思维方式、表现方式和审美趣 味影响、甚至造就一代代小说家,再由这些小说家创造各种各样 的小说,即是说,把“小说之祖”解释为小说的“父之父”,那么这 是非常适当的论断。《庄子)一书最早把“小说”二字组合成词: “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四意思是粉饰琰碎浅陋 的道理去求取高大的名声,离开明达远大的境地就很远了。这 里的“小说”和作为文学样式的小说,不是一回事。应该重视的 ①《黄氏日纱续诸子·庄子) ②《庄子·杂第·外物》。 10 ·中国古典小说的本体闻释和文体发生发展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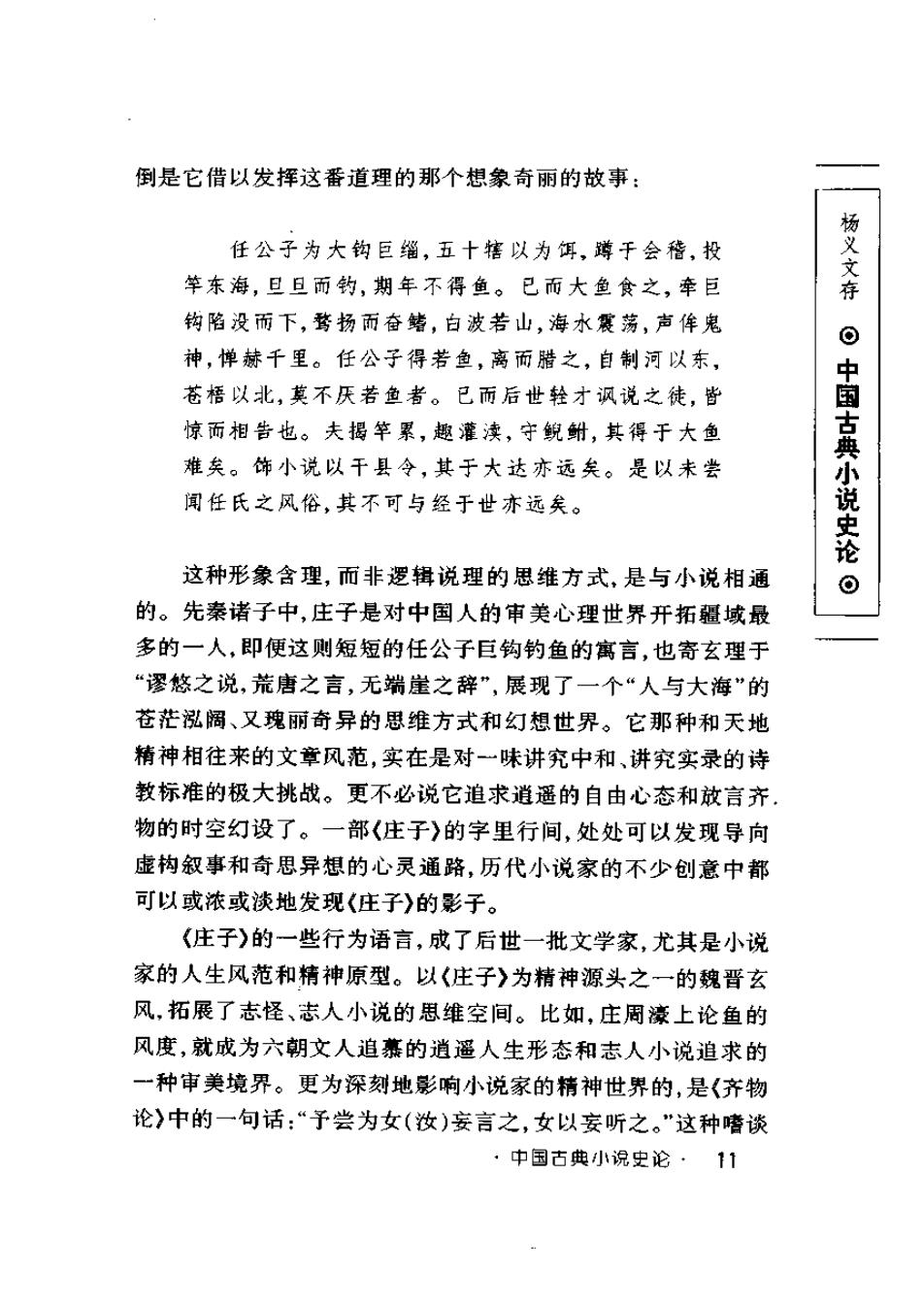
倒是它借以发挥这番道理的那个想象奇丽的故事: 任公子为大钩巨缁,五十辖以为饵,蹲于会稽,投 竿东海,旦旦而钓,期年不得鱼。已而大鱼食之,牵巨 钩陷没而下,骛扬而奋鳍,白波若山,海水震荡,声侔鬼 神,惮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鱼,离而腊之,自制河以东, 苍梧以北,莫不厌若鱼者。已而后世轮才讽说之徒,皆 惊而湘告也。夫揭竿累,趣灌渎,守鲵鲋,其得于大鱼 嘉 难矣。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是以未尝 闻任氏之风俗,其不可与经于世亦远矣。 墨 这种形象含理,而非逻辑说理的思维方式,是与小说相通 的。先秦诸子中,庄子是对中国人的审美心理世界开拓疆域最 多的一人,即便这则短短的任公子巨钩钓鱼的寓言,也寄玄理于 “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展现了一个“人与大海”的 苍茫泓阔、又瑰丽奇异的思维方式和幻想世界。它那种和天地 精神相往来的文章风范,实在是对一味讲究中和、讲究实录的诗 教标准的极大挑战。更不必说它追求道遥的自由心态和放言齐 物的时空幻设了。一部(庄子》的字里行间,处处可以发现导向 虚构叙事和奇思异想的心灵通路,历代小说家的不少创意中都 可以或浓或淡地发现《庄子》的影子。 《庄子)的一些行为语言,成了后世一批文学家,尤其是小说 家的人生风范和精神原型。以《庄子》为精神源头之一的魏晋玄 风,拓展了志怪、志人小说的思维空间。比如,庄周濠上论鱼的 风度,就成为六朝文人追燕的逍遥人生形态和志人小说追求的 一种审美境界。更为深刻地影响小说家的精神世界的,是《齐物 论》中的一句话:“予尝为女(汝)妄言之,女以妄听之。”这种嗜谈 ·中国古典小说史论·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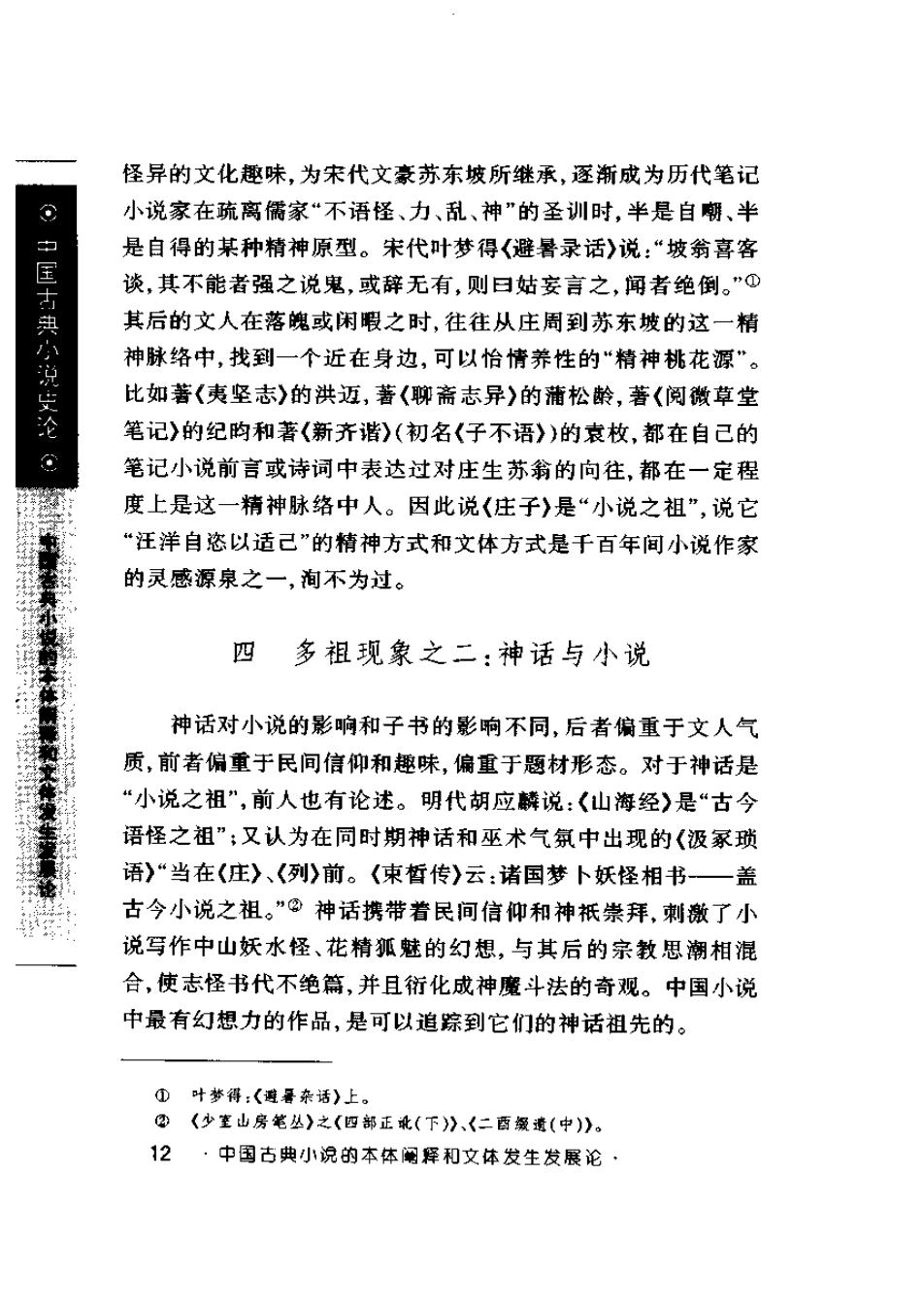
怪异的文化趣味,为宋代文素苏东坡所继承,逐渐成为历代笔记 小说家在疏离儒家“不语怪、力、乱、神”的圣训时,半是自嘲、半 中 是自得的某种精神原型。宋代叶梦得(避暑录话》说:“坡翁喜客 国 谈,其不能者强之说鬼,或辞无有,则日姑妄言之,闻者绝倒。”① 其后的文人在落魄或闲暇之时,往往从庄周到苏东坡的这一精 小说论 神脉络中,找到一个近在身边,可以怡情养性的“精神桃花源”。 比如著(夷坚志》的洪迈,著(聊斋志异)的蒲松龄,著《阅微草堂 笔记)的纪胸和著《新齐谐)(初名《子不语》)的袁枚,都在自己的 笔记小说前言或诗词中表达过对庄生苏翁的向往,都在一定程 度上是这一精神脉络中人。因此说(庄子》是“小说之祖”,说它 “汪洋自恣以适己”的精神方式和文体方式是千百年间小说作家 的灵感源泉之一,洵不为过。 四多祖现象之二:神话与小说 神话对小说的影响和子书的影响不同,后者偏重于文人气 质,前者偏重于民间信仰和趣味,偏重于题材形态。对于神话是 “小说之祖”,前人也有论述。明代胡应麟说:(山海经》是“古今 语怪之祖”;又认为在同时期神话和巫术气氛中出现的《汲冢琐 语》“当在(庄》、《列》前。《束皙传》云:诸国梦卜妖怪相书一盖 古今小说之祖。”②神话携带着民间信仰和神柢崇拜,刺撒了小 说写作中山妖水怪、花精狐魅的幻想,与其后的宗教思潮相混 合,使志怪书代不绝篇,并且衍化成神魔斗法的奇观。中国小说 中最有幻想力的作品,是可以追踪到它们的神话祖先的。 ①叶梦得:《避景杂话)上。 ②《少室山房笔丛》之(四部正乘(下)》、《仁西餐遗(中)》 12 ·中国古典小说的本体阐释和文体发生发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