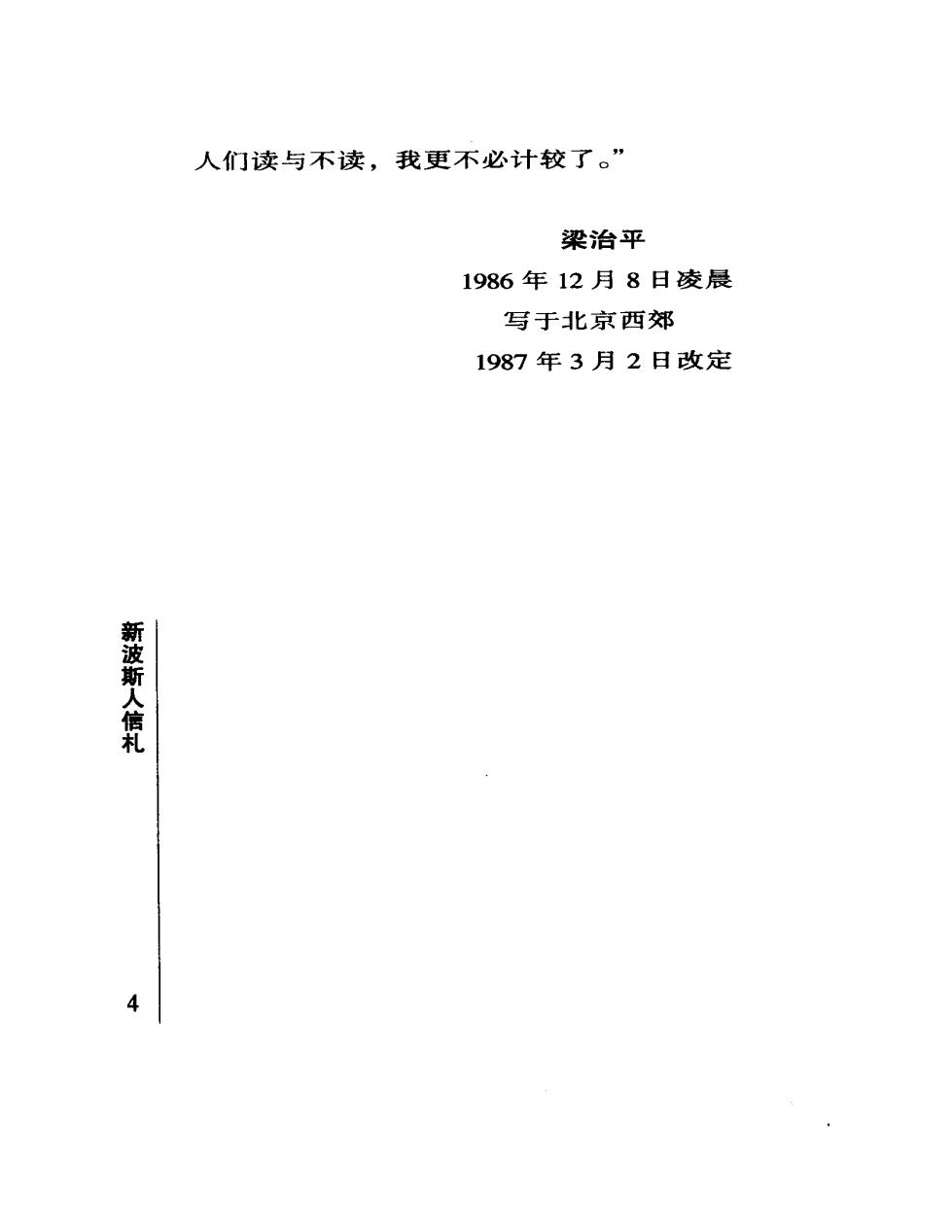
人们读与不读,我更不必计较了。” 梁治平 1986年12月8日凌晨 写于北京西郊 1987年3月2日改定 新波斯人信札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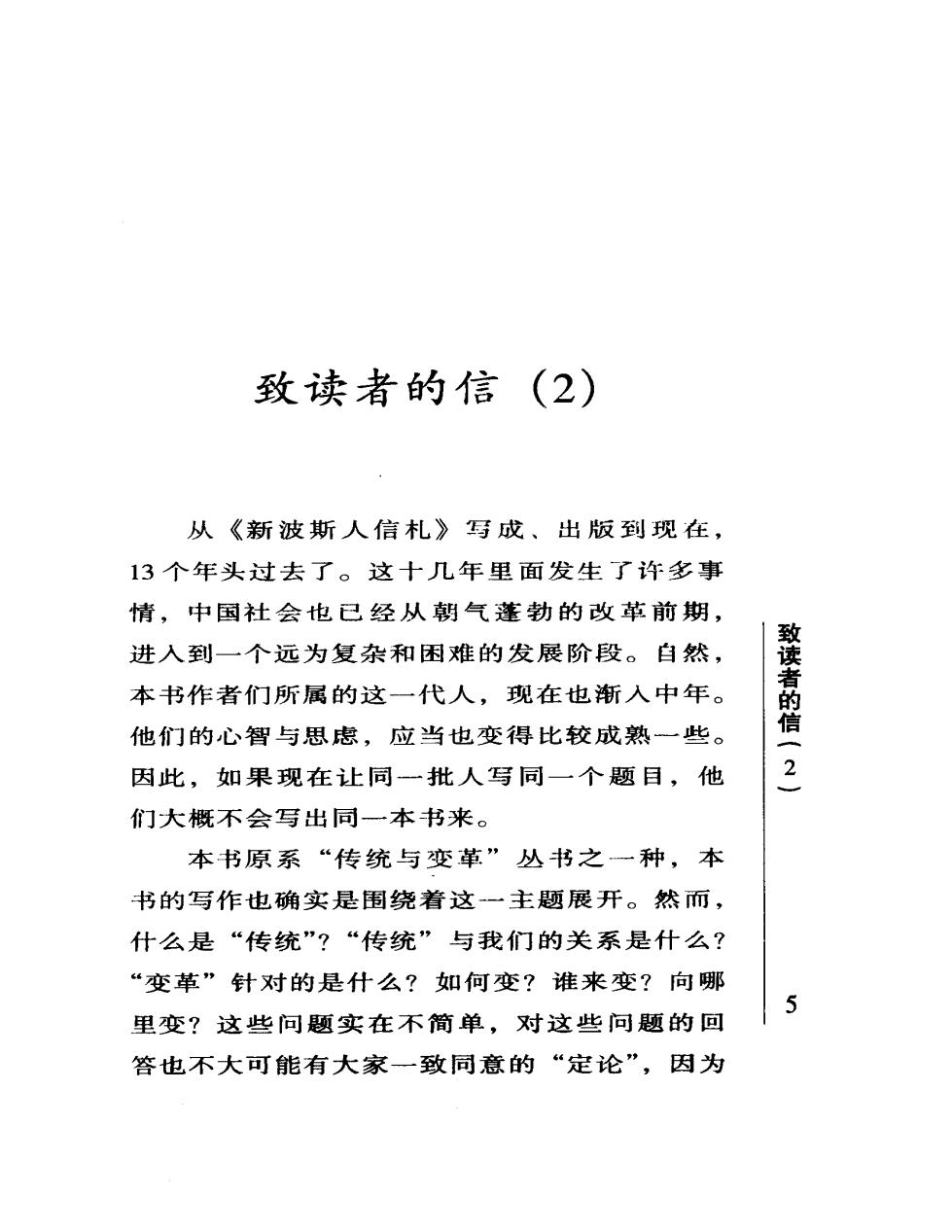
致读者的信(2) 从《新波斯人信札》写成、出版到现在, 13个年头过去了。这十几年里面发生了许多事 情,中国社会也己经从朝气蓬勃的改革前期, 进入到一个远为复杂和困难的发展阶段。自然, 本书作者们所属的这一代人,现在也渐入中年。 致读者的 他们的心智与思虑,应当也变得比较成熟一些。 因此,如果现在让同一批人写同一个题目,他 2 们大概不会写出同一本书来。 本书原系“传统与变革”丛书之一种,本 书的写作也确实是围绕着这一主题展开。然而, 什么是“传统”?“传统”与我们的关系是什么? “变革”针对的是什么?如何变?谁来变?向哪 里变?这些问题实在不简单,对这些问题的回 答也不大可能有大家一致同意的“定论”,因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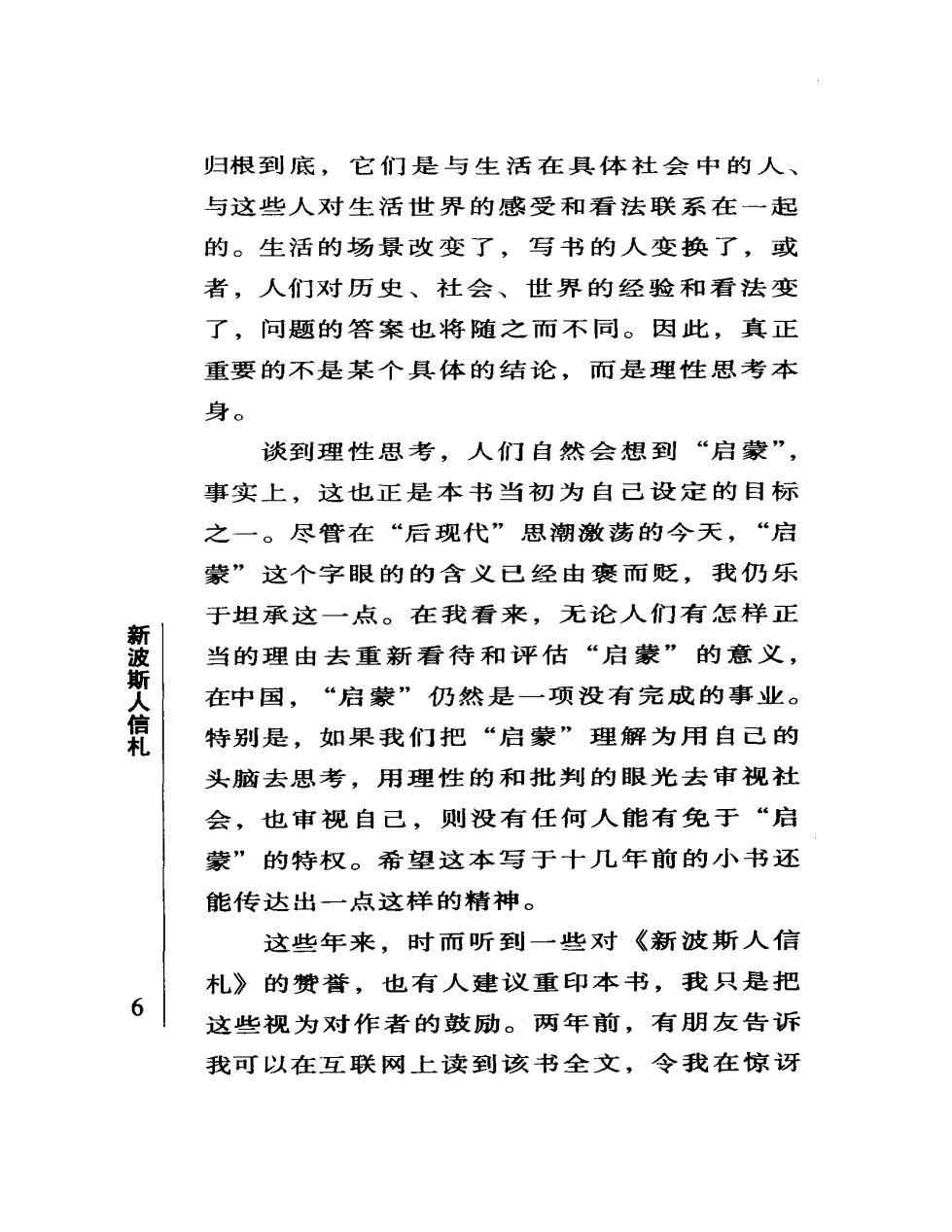
归根到底,它们是与生活在具体社会中的人、 与这些人对生活世界的感受和看法联系在一起 的。生活的场景改变了,写书的人变换了,或 者,人们对历史、社会、世界的经验和看法变 了,问题的答案也将随之而不同。因此,真正 重要的不是某个具体的结论,而是理性思考本 身。 谈到理性思考,人们自然会想到“启蒙”, 事实上,这也正是本书当初为自己设定的目标 之一。尽管在“后现代”思潮激荡的今天,“启 蒙”这个字眼的的含义已经由褒而贬,我仍乐 于坦承这一点。在我看来,无论人们有怎样正 新波斯人信札 当的理由去重新看待和评估“启蒙”的意义, 在中国,“启蒙”仍然是一项没有完成的事业。 特别是,如果我们把“启蒙”理解为用自己的 头脑去思考,用理性的和批判的眼光去审视社 会,也审视自己,则没有任何人能有免于“启 蒙”的特权。希望这本写于十几年前的小书还 能传达出一点这样的精神。 这些年来,时而听到一些对《新波斯人信 札》的赞誉,也有人建议重印本书,我只是把 6 这些视为对作者的鼓励。两年前,有朋友告诉 我可以在互联网上读到该书全文,令我在惊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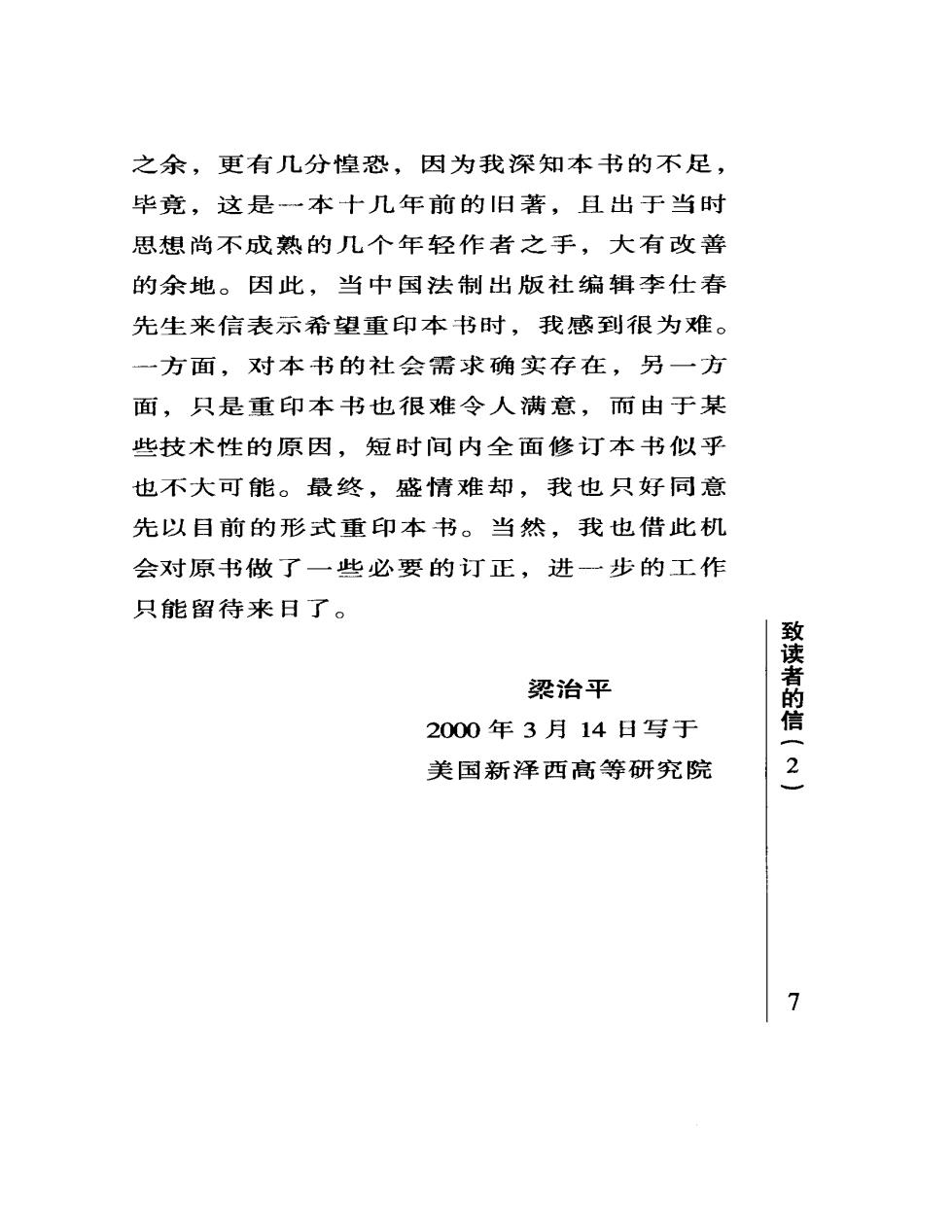
之余,更有几分惶恐,因为我深知本书的不足, 毕竞,这是一本十几年前的旧著,且出于当时 思想尚不成熟的几个年轻作者之手,大有改善 的余地。因此,当中国法制出版社编辑李仕春 先生来信表示希望重印本书时,我感到很为难。 一一方面,对本书的社会需求确实存在,另一方 面,只是重印本书也很难令人满意,而由于某 些技术性的原因,短时间内全面修订本书似乎 也不大可能。最终,盛情难却,我也只好同意 先以目前的形式重印本书。当然,我也借此机 会对原书做了一些必要的订正,进一步的工作 只能留待来日了。 梁治平 致读者的信 2000年3月14日写于 美国新泽西高等研究院 2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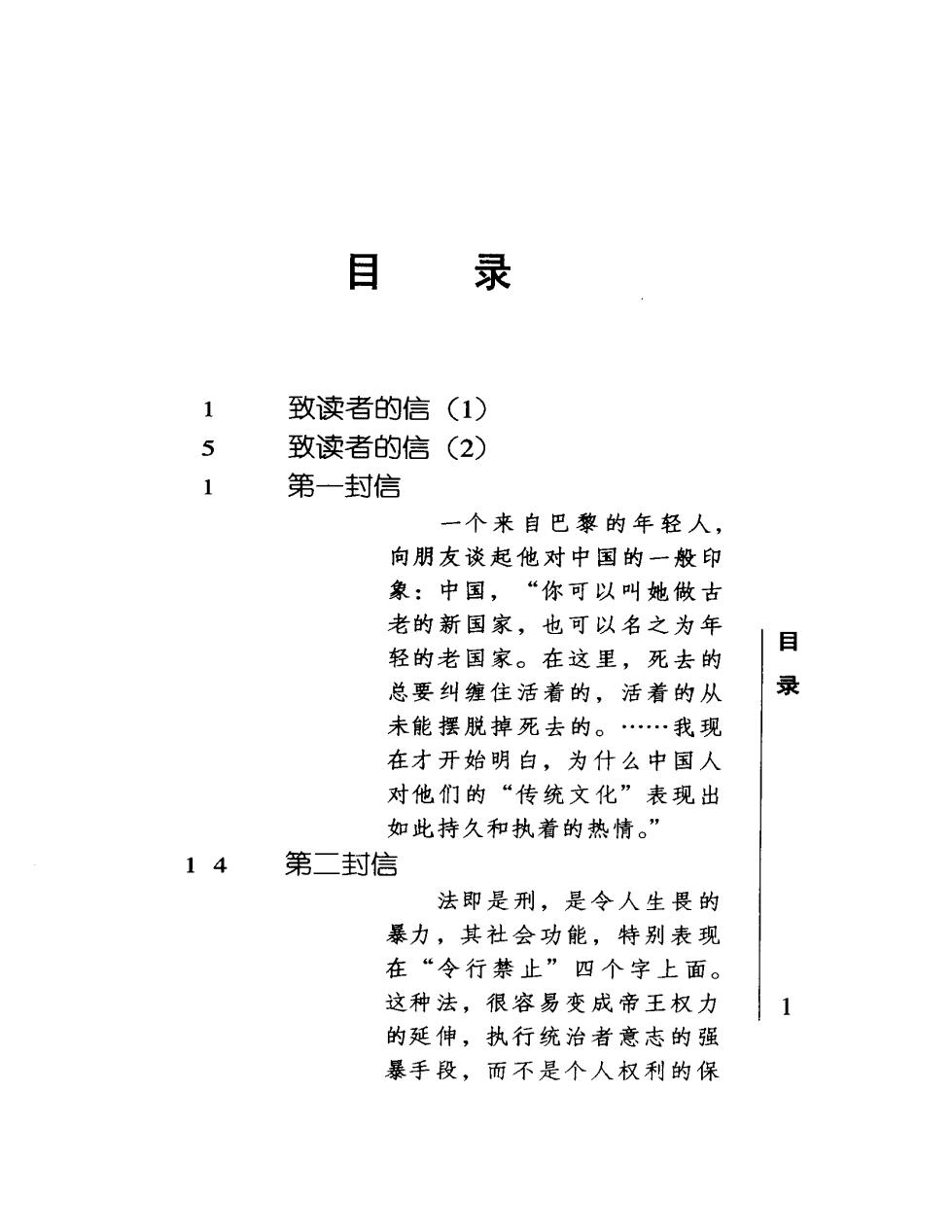
目 录 致读者的信(1) 致读者的信(2) 1 第一封信 一个来自巴黎的年轻人, 向朋友谈起他对中国的一般印 象:中国,“你可以叫她做古 老的新国家,也可以名之为年 目 轻的老国家。在这里,死去的 总要纠缠住活着的,活着的从 录 未能摆脱掉死去的。.我现 在才开始明白,为什么中国人 对他们的“传统文化”表现出 如此持久和执着的热情。” 14 第二封信 法即是刑,是令人生畏的 暴力,其社会功能,特别表现 在“令行禁止”四个字上面。 这种法,很容易变成帝王权力 1 的延伸,执行统治者意志的强 暴手段,而不是个人权利的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