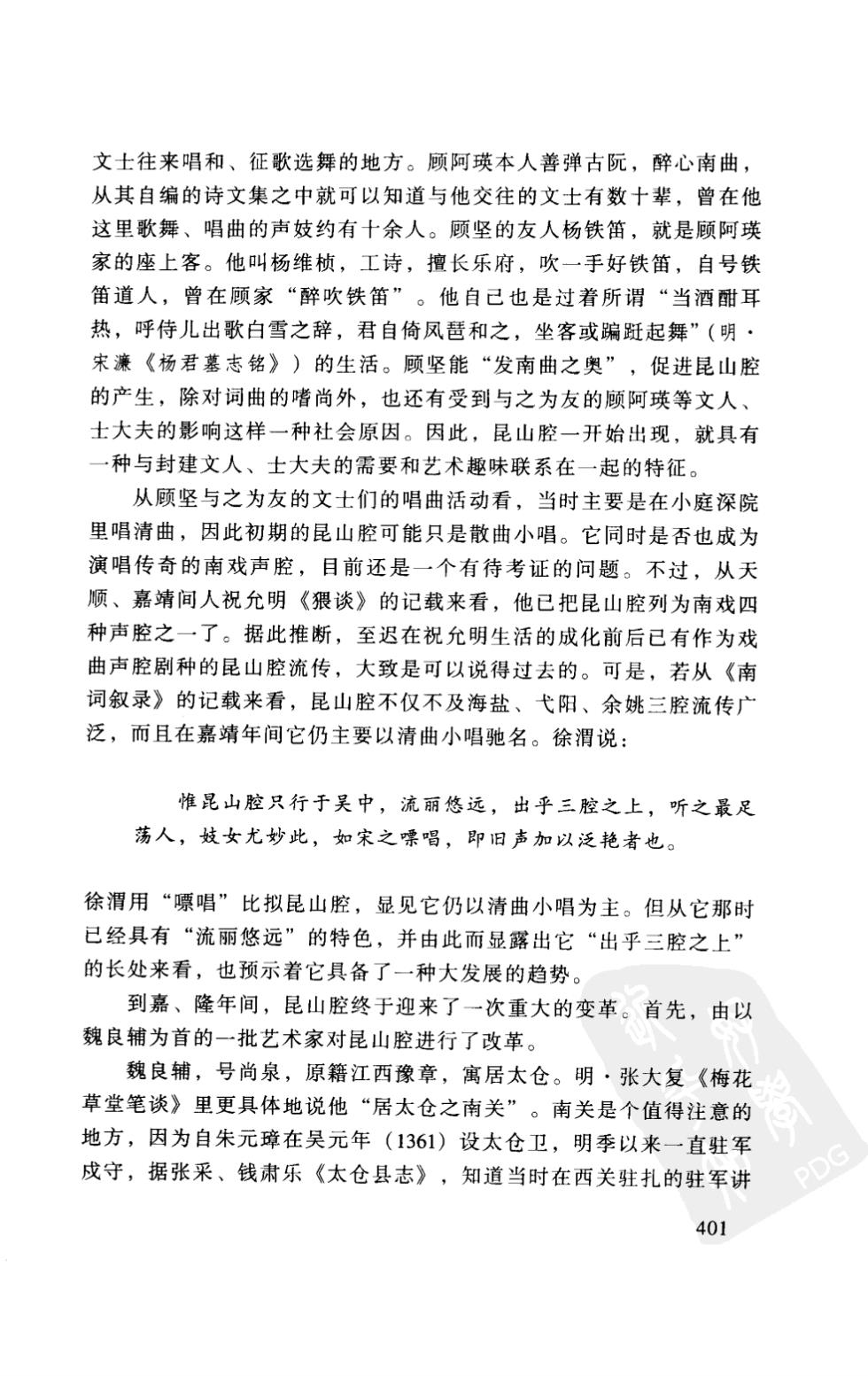
文士往来唱和、征歌选舞的地方。顾阿瑛本人善弹古阮,醉心南曲, 从其自编的诗文集之中就可以知道与他交往的文士有数十辈,曾在他 这里歌舞、唱曲的声妓约有十余人。顾坚的友人杨铁笛,就是顾阿瑛 家的座上客。他叫杨维桢,工诗,擅长乐府,吹一手好铁笛,自号铁 笛道人,曾在顾家“醉吹铁笛”。他自己也是过着所谓“当酒酣耳 热,呼侍儿出歌白雪之辞,君自倚凤琶和之,坐客或骗跹起舞”(明· 宋濂《杨君墓志铭》)的生活。顾坚能“发南曲之奥”,促进昆山腔 的产生,除对词曲的嗜尚外,也还有受到与之为友的顾阿瑛等文人、 士大夫的影响这样一种社会原因。因此,昆山腔一开始出现,就具有 种与封建文人、士大夫的需要和艺术趣味联系在一起的特征。 从顾坚与之为友的文士们的唱曲活动看,当时主要是在小庭深院 里唱清曲,因此初期的昆山腔可能只是散曲小唱。它同时是否也成为 演唱传奇的南戏声腔,目前还是一个有待考证的问题。不过,从天 顺、嘉靖间人祝允明《猥谈》的记载来看,他已把昆山腔列为南戏四 种声腔之一了。据此推断,至迟在祝允明生活的成化前后已有作为戏 曲声腔剧种的昆山腔流传,大致是可以说得过去的。可是,若从《南 词叙录》的记载来看,昆山腔不仅不及海盐、弋阳、余姚三腔流传广 泛,而且在嘉靖年间它仍主要以清曲小唱驰名。徐渭说: 帷昆山腔只行于吴中,流丽悠远,出乎三腔之上,听之最足 荡人,妓女尤妙此,如宋之噪唱,即旧声加以泛艳者也 徐渭用“嘌唱”比拟昆山腔,显见它仍以清曲小唱为主。但从它那时 已经具有“流丽悠远”的特色,并由此而显露出它“出乎三腔之上” 的长处来看,也预示着它具备了一种大发展的趋势。 到嘉、隆年间,昆山腔终于迎来了一次重大的变革。首先,由以 魏良辅为首的一批艺术家对昆山腔进行了改革。 魏良辅,号尚泉,原籍江西豫章,寓居太仓。明·张大复《梅花 草堂笔谈》里更具体地说他“居太仓之南关”。南关是个值得注意的 地方,因为自朱元璋在吴元年(1361)设太仓卫,明季以来一直驻军 成守,据张采、钱肃乐《太仓县志》,知道当时在西关驻扎的驻军讲 4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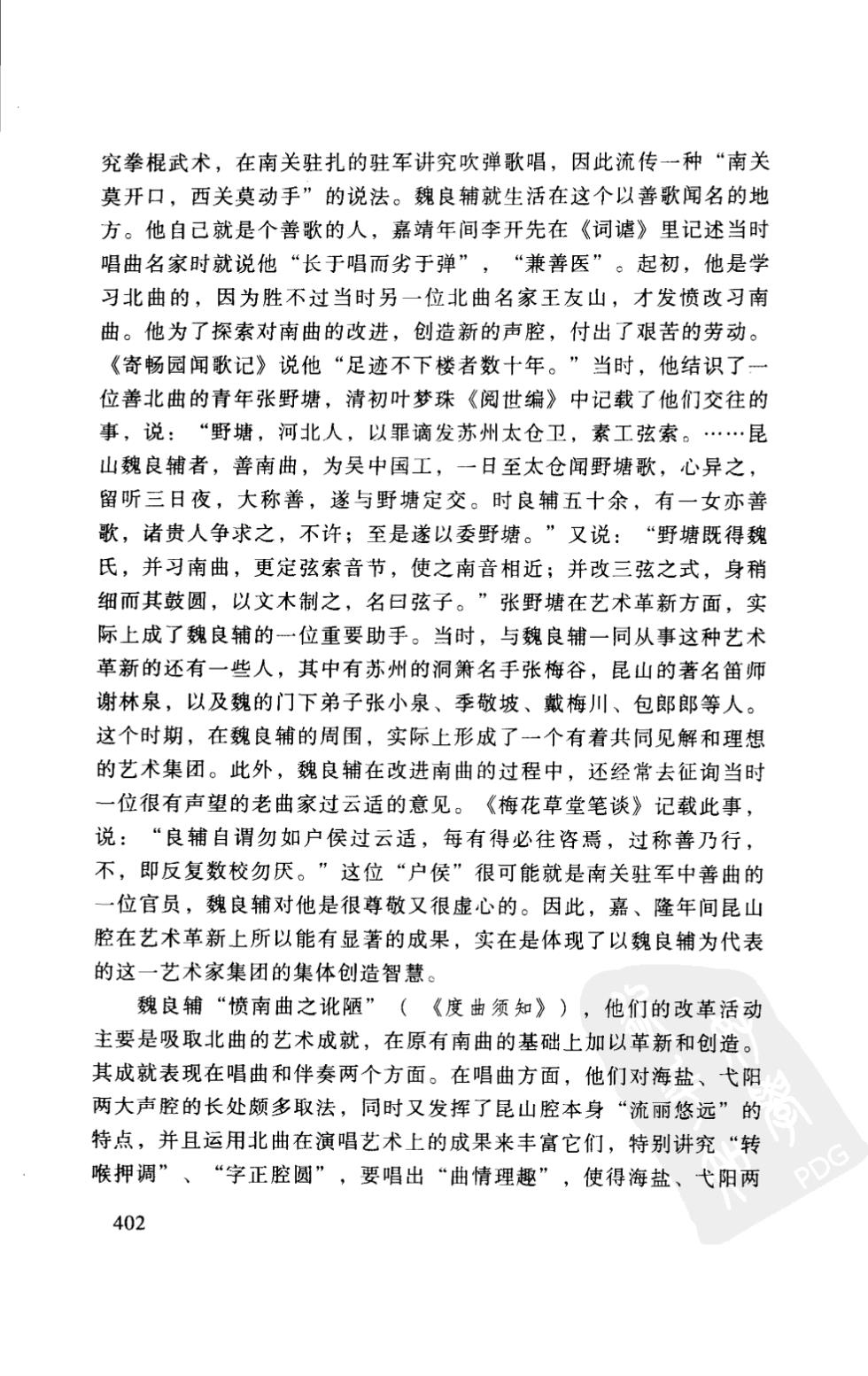
究拳棍武术,在南关驻扎的驻军讲究吹弹歌唱,因此流传一种“南关 莫开口,西关莫动手”的说法。魏良辅就生活在这个以善歌闻名的地 方。他自己就是个善歌的人,嘉靖年间李开先在《词谑》里记述当时 唱曲名家时就说他“长于唱而劣于弹”,“兼善医”。起初,他是学 习北曲的,因为胜不过当时另一位北曲名家王友山,才发愤改习南 曲。他为了探索对南曲的改进,创造新的声腔,付出了艰苦的劳动。 《寄畅园闻歌记》说他“足迹不下楼者数十年。”当时,他结识了 位善北曲的青年张野塘,清初叶梦珠《阅世编》中记载了他们交往的 事,说:“野塘,河北人,以罪谪发苏州太仓卫,素工弦索。.昆 山魏良辅者,善南曲,为吴中国工,一日至太仓闻野塘歌,心异之, 留听三日夜,大称善,遂与野塘定交。时良辅五十余,有一女亦善 歌,诸贵人争求之,不许;至是遂以委野塘。”又说:“野塘既得魏 氏,并习南曲,更定弦索音节,使之南音相近;并改三弦之式,身稍 细而其皱圆,以文木制之,名曰弦子。”张野塘在艺术革新方面,实 际上成了魏良辅的一位重要助手。当时,与魏良辅一同从事这种艺术 革新的还有一些人,其中有苏州的洞箫名手张梅谷,昆山的著名笛师 谢林泉,以及魏的门下弟子张小泉、季敬坡、戴梅川、包郎郎等人。 这个时期,在魏良辅的周围,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有着共同见解和理想 的艺术集团。此外,魏良辅在改进南曲的过程中,还经常去征询当时 位很有声望的老曲家过云适的意见。《梅花草堂笔谈》记载此事, 说: “良辅自谓勿如户侯过云适,每有得必往咨焉,过称善乃行, 不,即反复数校勿厌。”这位“户侯”很可能就是南关驻军中善曲的 一位官员,魏良辅对他是很尊敬又很虚心的。因此,嘉、隆年间昆山 腔在艺术革新上所以能有显著的成果,实在是体现了以魏良辅为代表 的这一艺术家集团的集体创造智慧。 魏良辅“愤南曲之讹陋”(《度曲须知》),他们的改革活动 主要是吸取北曲的艺术成就,在原有南曲的基础上加以革新和创造。 其成就表现在唱曲和伴奏两个方面。在唱曲方面,他们对海盐、弋阳 两大声腔的长处颇多取法,同时又发挥了昆山腔本身“流丽悠远”的 特点,并且运用北曲在演唱艺术上的成果来丰富它们,特别讲究“转 喉押调”、“字正腔圆”,要唱出“曲情理趣”,使得海盐、弋阳两 4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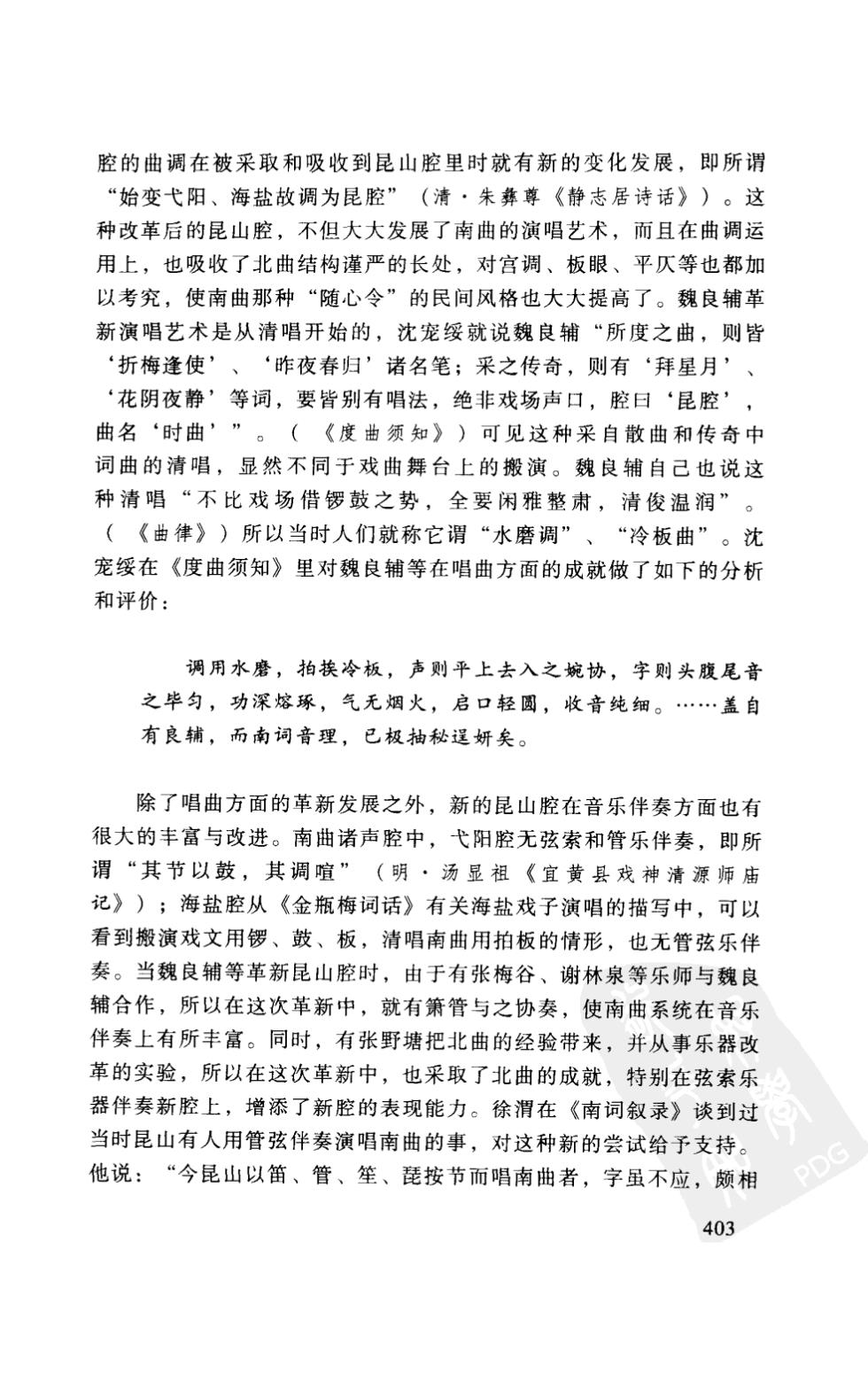
腔的曲调在被采取和吸收到昆山腔里时就有新的变化发展,即所谓 “始变弋阳、海盐故调为昆腔”(清·朱彝尊《静志居诗话》)。这 种改革后的昆山腔,不但大大发展了南曲的演唱艺术,而且在曲调运 用上,也吸收了北曲结构谨严的长处,对宫调、板眼、平仄等也都加 以考究,使南曲那种“随心令”的民间风格也大大提高了。魏良辅革 新演唱艺术是从清唱开始的,沈宠绥就说魏良辅“所度之曲,则皆 ‘折梅逢使’ ‘昨夜春归’诸名笔;采之传奇,则有‘拜星月’、 ‘花阴夜静’等词,要皆别有唱法,绝非戏场声口,腔日‘昆腔’, 曲名‘时曲’ (《度曲须知》)可见这种采自散曲和传奇中 词曲的清唱,显然不同于戏曲舞台上的搬演。魏良辅自己也说这 种清唱“不比戏场借锣鼓之势,全要闲雅整肃,清俊温润” (《曲律》)所以当时人们就称它谓“水磨调”、 “冷板曲”。沈 宠绥在《度曲须知》里对魏良辅等在唱曲方面的成就做了如下的分析 和评价: 调用水磨,拍挨冷板,声则平上去入之婉协,字则头腹尾音 之毕匀,功深熔琢,气无烟火,启口轻圆,收音纯细。.盖自 有良辅,而南词音理,已极抽秘逞妍矣。 除了唱曲方面的革新发展之外,新的昆山腔在音乐伴奏方面也有 很大的丰富与改进。南曲诸声腔中,弋阳腔无弦索和管乐伴奏,即所 谓“其节以鼓,其调喧”(明·汤显祖《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 记》);海盐腔从《金瓶梅词话》有关海盐戏子演唱的描写中,可以 看到搬演戏文用锣、敱、板,清唱南曲用拍板的情形,也无管弦乐伴 奏。当魏良辅等革新昆山腔时,由于有张梅谷、谢林泉等乐师与魏良 辅合作,所以在这次革新中,就有箫管与之协奏,使南曲系统在音乐 伴奏上有所丰富。同时,有张野塘把北曲的经验带来,并从事乐器改 革的实验,所以在这次革新中,也采取了北曲的成就,特别在弦索乐 器伴奏新腔上,增添了新腔的表现能力。徐渭在《南词叙录》谈到过 当时昆山有人用管弦伴奏演唱南曲的事,对这种新的尝试给予支持。 他说:“今昆山以笛、管、笙、琵按节而唱南曲者,字虽不应,颇相 403

谐和,殊为可听,亦吴俗敏妙之事。或者非之,以为妄作,请问〔点 绛唇)、〔新水令),是何圣人著作?”《南词叙录》成书于嘉靖三 十八年,它没有关于魏良辅的任何记载,可能这时魏良辅的“新声” 还未成功,但是从上面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当时有人在从事革新南曲 音乐的活动,与嘉、隆间魏良辅以“新声”享名的时间相距不太远。 推断起来,徐渭所说的也许正是魏良辅等人不断尝试,进行革新活动 的那个过程。总之,魏良辅等在乐队的发展上完成了一次重大的革 新,即弦索、箫管、鼓板三类乐器合在一起,集南北之所长,创立了 一个规模完整的乐队伴奏,不只用于清唱,而且后来也用于戏曲舞 台,其意义正如沈宠绥《弦索辨讹》中所说: 嘉隆间,昆山有魏良辅者,乃渐改旧习,始备众乐器而剧场 大成,至今遵之。 经过魏良辅等人改革之后的昆山腔,在表达人物情感的能力和艺 术技巧等方面都达到了这一时期的高峰。因此,当昆山腔以“新声” 的姿态出现在歌坛上时,立即引起士大夫和广大市民阶层的注意和惊 奇,就连当时吴中的老曲师如袁髯、尤驼等也都钦佩不已,认为已超 过了自己所达到的水平。 魏良辅还著有《南词引正》(即《曲律》),记录了自己的学习 心得和实践体会,在艺术理论方面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魏良辅等改革昆山腔的成就虽然很高,但是对昆山腔这一声腔剧 种来说,还只是走了重要的第一步,因为“新声”在当时还只是清 唱,尚未走上戏曲舞台。把新的昆山腔应用于戏曲舞台演唱传奇的 是梁伯龙。他继魏良辅之后,完成了又一重要的变革,又前进了一 步。张元长《梅花草堂笔谈》在叙述了魏良辅的革新活动之后,紧接 着说: 梁伯龙闻,起而效之,考订元剧,自翻新调,作《江东白 芋》《浣纱》诸曲。又与郑思笠精研音理,唐小虞、陈梅泉五七 辈杂转之,金石铿然,谱传藩邸戚畹、金紫熠擒之家,而取声必 4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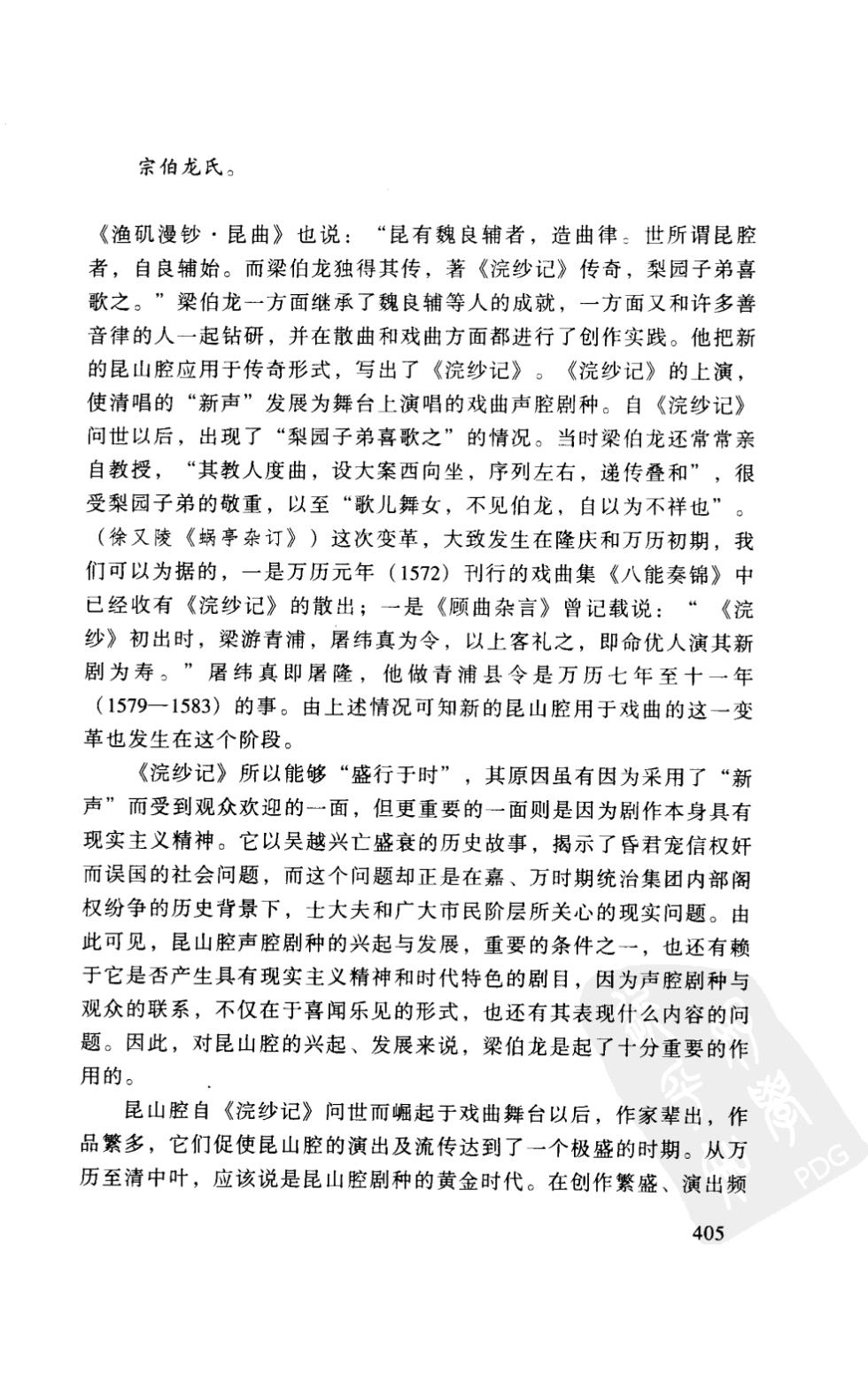
宗伯龙氏 《渔矶漫钞·昆曲》也说:“昆有魏良辅者,造曲律。世所谓昆腔 者,自良辅始。而梁伯龙独得其传,著《浣纱记》传奇,梨园子弟喜 歌之。”梁伯龙一方面继承了魏良辅等人的成就,一方面又和许多善 音律的人一起钻研,并在散曲和戏曲方面都进行了创作实践。他把新 的昆山腔应用于传奇形式,写出了《浣纱记》。《浣纱记》的上演, 使清唱的“新声”发展为舞台上演唱的戏曲声腔剧种。自《浣纱记》 问世以后,出现了“梨园子弟喜歌之”的情况。当时梁伯龙还常常亲 自教授,“其教人度曲,设大案西向坐,序列左右,递传叠和”,很 受梨园子弟的敬重,以至“歌儿舞女,不见伯龙,自以为不祥也 (徐又陵《蜗亭杂订》)这次变革,大致发生在隆庆和万历初期,我 们可以为据的,一是万历元年(1572)刊行的戏曲集《八能奏锦》中 已经收有《浣纱记》的散出;一是《顾曲杂言》曾记载说:“《浣 纱》初出时,梁游青浦,屠纬真为令,以上客礼之,即命优人演其新 剧为寿。”屠纬真即屠隆,他做青浦县令是万历七年至十一年 (1579一1583)的事。由上述情况可知新的昆山腔用于戏曲的这一变 革也发生在这个阶段。 《浣纱记》所以能够“盛行于时”,其原因虽有因为采用了“新 声”而受到观众欢迎的一面,但更重要的一面则是因为剧作本身具有 现实主义精神。它以吴越兴亡盛衰的历史故事,揭示了昏君宠信权奸 而误国的社会问题,而这个问题却正是在嘉、万时期统治集团内部阁 权纷争的历史背景下,土大夫和广大市民阶层所关心的现实问题。由 此可见,昆山腔声腔剧种的兴起与发展,重要的条件之一,也还有赖 于它是否产生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和时代特色的剧目,因为声腔剧种与 观众的联系,不仅在于喜闻乐见的形式,也还有其表现什么内容的问 题。因此,对昆山腔的兴起、发展来说,梁伯龙是起了十分重要的作 用的。 昆山腔自《浣纱记》问世而崛起于戏曲舞台以后,作家辈出,作 品繁多,它们促使昆山腔的演出及流传达到了一个极盛的时期。从万 历至清中叶,应该说是昆山腔剧种的黄金时代。在创作繁盛、演出频 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