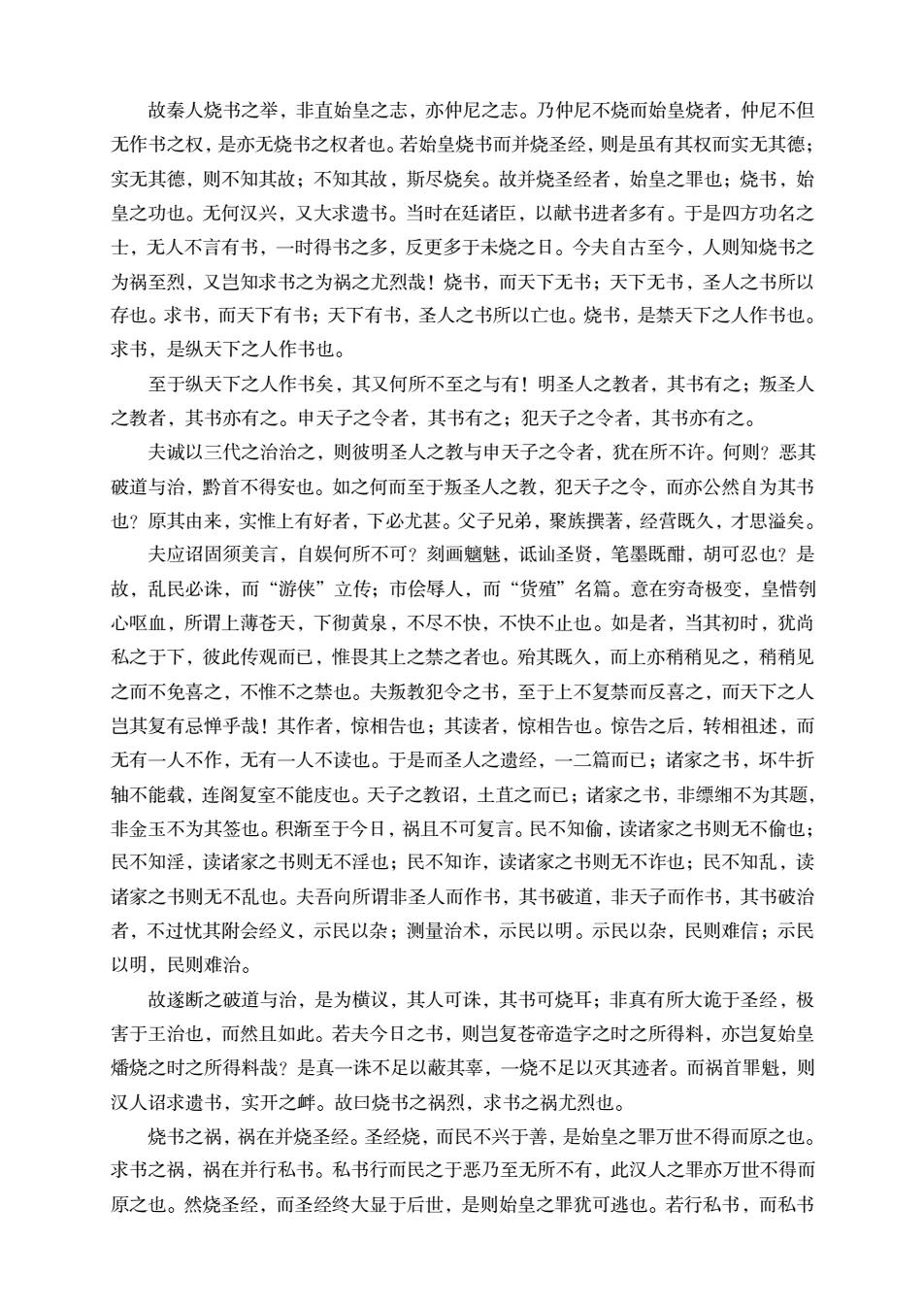
故秦人烧书之举,非直始皇之志,亦仲尼之志。乃仲尼不烧而始皇烧者,仲尼不但 无作书之权,是亦无烧书之权者也。若始皇烧书而并烧圣经,则是虽有其权而实无其德; 实无其德,则不知其故;不知其故,斯尽烧矣。故并烧圣经者,始皇之罪也:烧书,始 皇之功也。无何汉兴,又大求遗书。当时在廷诸臣,以献书进者多有。于是四方功名之 士,无人不言有书,一时得书之多,反更多于未烧之日。今夫自古至今,人则知烧书之 为祸至烈,又岂知求书之为祸之尤烈哉!烧书,而天下无书;天下无书,圣人之书所以 存也。求书,而天下有书:天下有书,圣人之书所以亡也。烧书,是禁天下之人作书也。 求书,是纵天下之人作书也。 至于纵天下之人作书矣,其又何所不至之与有!明圣人之教者,其书有之;叛圣人 之教者,其书亦有之。申天子之令者,其书有之;犯天子之令者,其书亦有之。 夫诚以三代之治治之,则彼明圣人之教与申天子之令者,犹在所不许。何则?恶其 破道与治,黔首不得安也。如之何而至于叛圣人之教,犯天子之令,而亦公然自为其书 也?原其由来,实惟上有好者,下必尤甚。父子兄弟,聚族撰著,经营既久,才思溢矣。 夫应诏固须美言,自娱何所不可?刻画魑魅,诋讪圣贤,笔墨既酣,胡可忍也?是 故,乱民必诛,而“游侠”立传;市侩辱人,而“货殖”名篇。意在穷奇极变,皇惜刳 心呕血,所谓上薄苍天,下彻黄泉,不尽不快,不快不止也。如是者,当其初时,犹尚 私之于下,彼此传观而已,惟畏其上之禁之者也。殆其既久,而上亦稍稍见之,稍稍见 之而不免喜之,不惟不之禁也。夫叛教犯令之书,至于上不复禁而反喜之,而天下之人 岂其复有忌惮乎哉!其作者,惊相告也;其读者,惊相告也。惊告之后,转相祖述,而 无有一人不作,无有一人不读也。于是而圣人之遗经,一二篇而已;诸家之书,坏牛折 轴不能载,连阁复室不能皮也。天子之教诏,土苴之而已;诸家之书,非缥绵不为其题, 非金玉不为其签也。积渐至于今日,祸且不可复言。民不知偷,读诸家之书则无不偷也: 民不知淫,读诸家之书则无不淫也;民不知诈,读诸家之书则无不诈也;民不知乱,读 诸家之书则无不乱也。夫吾向所谓非圣人而作书,其书破道,非天子而作书,其书破治 者,不过忧其附会经义,示民以杂:测量治术,示民以明。示民以杂,民则难信;示民 以明,民则难治。 故遂断之破道与治,是为横议,其人可诛,其书可烧耳;非真有所大诡于圣经,极 害于王治也,而然且如此。若夫今日之书,则岂复苍帝造字之时之所得料,亦岂复始皇 燔烧之时之所得料哉?是真一诛不足以蔽其率,一烧不足以灭其迹者。而祸首罪魁,则 汉人诏求遗书,实开之衅。故日烧书之祸烈,求书之祸尤烈也。 烧书之祸,祸在并烧圣经。圣经烧,而民不兴于善,是始皇之罪万世不得而原之也。 求书之祸,祸在并行私书。私书行而民之于恶乃至无所不有,此汉人之罪亦万世不得而 原之也。然烧圣经,而圣经终大显于后世,是则始皇之罪犹可逃也。若行私书,而私书
故秦人烧书之举,非直始皇之志,亦仲尼之志。乃仲尼不烧而始皇烧者,仲尼不但 无作书之权,是亦无烧书之权者也。若始皇烧书而并烧圣经,则是虽有其权而实无其德; 实无其德,则不知其故;不知其故,斯尽烧矣。故并烧圣经者,始皇之罪也;烧书,始 皇之功也。无何汉兴,又大求遗书。当时在廷诸臣,以献书进者多有。于是四方功名之 士,无人不言有书,一时得书之多,反更多于未烧之日。今夫自古至今,人则知烧书之 为祸至烈,又岂知求书之为祸之尤烈哉!烧书,而天下无书;天下无书,圣人之书所以 存也。求书,而天下有书;天下有书,圣人之书所以亡也。烧书,是禁天下之人作书也。 求书,是纵天下之人作书也。 至于纵天下之人作书矣,其又何所不至之与有!明圣人之教者,其书有之;叛圣人 之教者,其书亦有之。申天子之令者,其书有之;犯天子之令者,其书亦有之。 夫诚以三代之治治之,则彼明圣人之教与申天子之令者,犹在所不许。何则?恶其 破道与治,黔首不得安也。如之何而至于叛圣人之教,犯天子之令,而亦公然自为其书 也?原其由来,实惟上有好者,下必尤甚。父子兄弟,聚族撰著,经营既久,才思溢矣。 夫应诏固须美言,自娱何所不可?刻画魑魅,诋讪圣贤,笔墨既酣,胡可忍也?是 故,乱民必诛,而“游侠”立传;市侩辱人,而“货殖”名篇。意在穷奇极变,皇惜刳 心呕血,所谓上薄苍天,下彻黄泉,不尽不快,不快不止也。如是者,当其初时,犹尚 私之于下,彼此传观而已,惟畏其上之禁之者也。殆其既久,而上亦稍稍见之,稍稍见 之而不免喜之,不惟不之禁也。夫叛教犯令之书,至于上不复禁而反喜之,而天下之人 岂其复有忌惮乎哉!其作者,惊相告也;其读者,惊相告也。惊告之后,转相祖述,而 无有一人不作,无有一人不读也。于是而圣人之遗经,一二篇而已;诸家之书,坏牛折 轴不能载,连阁复室不能庋也。天子之教诏,土苴之而已;诸家之书,非缥缃不为其题, 非金玉不为其签也。积渐至于今日,祸且不可复言。民不知偷,读诸家之书则无不偷也; 民不知淫,读诸家之书则无不淫也;民不知诈,读诸家之书则无不诈也;民不知乱,读 诸家之书则无不乱也。夫吾向所谓非圣人而作书,其书破道,非天子而作书,其书破治 者,不过忧其附会经义,示民以杂;测量治术,示民以明。示民以杂,民则难信;示民 以明,民则难治。 故遂断之破道与治,是为横议,其人可诛,其书可烧耳;非真有所大诡于圣经,极 害于王治也,而然且如此。若夫今日之书,则岂复苍帝造字之时之所得料,亦岂复始皇 燔烧之时之所得料哉?是真一诛不足以蔽其辜,一烧不足以灭其迹者。而祸首罪魁,则 汉人诏求遗书,实开之衅。故曰烧书之祸烈,求书之祸尤烈也。 烧书之祸,祸在并烧圣经。圣经烧,而民不兴于善,是始皇之罪万世不得而原之也。 求书之祸,祸在并行私书。私书行而民之于恶乃至无所不有,此汉人之罪亦万世不得而 原之也。然烧圣经,而圣经终大显于后世,是则始皇之罪犹可逃也。若行私书,而私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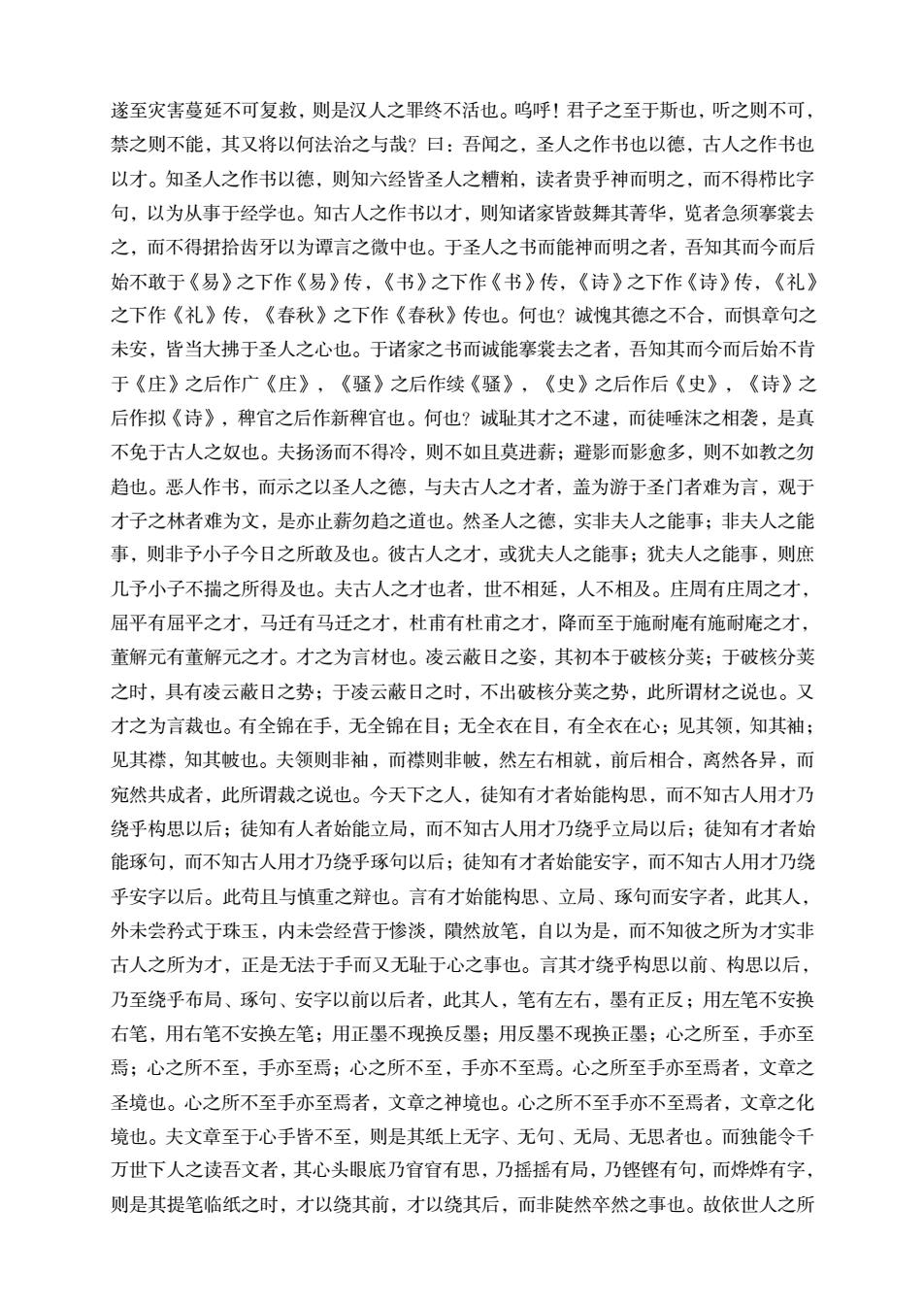
遂至灾害蔓延不可复救,则是汉人之罪终不活也。鸣呼!君子之至于斯也,听之则不可, 禁之则不能,其又将以何法治之与哉?日:吾闻之,圣人之作书也以德,古人之作书也 以才。知圣人之作书以德,则知六经皆圣人之糟粕,读者贵乎神而明之,而不得栉比字 句,以为从事于经学也。知古人之作书以才,则知诸家皆鼓舞其菁华,览者急须塞裳去 之,而不得裙拾齿牙以为谭言之微中也。于圣人之书而能神而明之者,吾知其而今而后 始不敢于《易》之下作《易》传,《书》之下作《书》传,《诗》之下作《诗》传,《礼》 之下作《礼》传,《春秋》之下作《春秋》传也。何也?诚愧其德之不合,而惧章句之 未安,皆当大拂于圣人之心也。于诸家之书而诚能塞裳去之者,吾知其而今而后始不肯 于《庄》之后作广《庄》,《骚》之后作续《骚》,《史》之后作后《史》,《诗》之 后作拟《诗》,稗官之后作新稗官也。何也?诚耻其才之不逮,而徒唾沫之相袭,是真 不免于古人之奴也。夫扬汤而不得冷,则不如且莫进薪;避影而影愈多,则不如教之勿 趋也。恶人作书,而示之以圣人之德,与夫古人之才者,盖为游于圣门者难为言,观于 才子之林者难为文,是亦止薪勿趋之道也。然圣人之德,实非夫人之能事;非夫人之能 事,则非予小子今日之所敢及也。彼古人之才,或犹夫人之能事;犹夫人之能事,则庶 几予小子不揣之所得及也。夫古人之才也者,世不相延,人不相及。庄周有庄周之才, 屈平有屈平之才,马迁有马迁之才,杜甫有杜甫之才,降而至于施耐庵有施耐庵之才, 董解元有董解元之才。才之为言材也。凌云蔽日之姿,其初本于破核分荚;于破核分荚 之时,具有凌云蔽日之势:于凌云蔽日之时,不出破核分荚之势,此所谓材之说也。又 才之为言裁也。有全锦在手,无全锦在目;无全衣在目,有全衣在心;见其领,知其袖 见其襟,知其帔也。夫领则非袖,而襟则非敲,然左右相就,前后相合,离然各异,而 宛然共成者,此所谓裁之说也。今天下之人,徒知有才者始能构思,而不知古人用才乃 绕乎构思以后;徒知有人者始能立局,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绕乎立局以后;徒知有才者始 能琢句,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绕乎琢句以后:徒知有才者始能安字,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绕 乎安字以后。此苟且与慎重之辩也。言有才始能构思、立局、琢句而安字者,此其人, 外未尝矜式于珠玉,内未尝经营于惨淡,喷然放笔,自以为是,而不知彼之所为才实非 古人之所为才,正是无法于手而又无耻于心之事也。言其才绕乎构思以前、构思以后, 乃至绕乎布局、琢句、安字以前以后者,此其人,笔有左右,墨有正反;用左笔不安换 右笔,用右笔不安换左笔:用正墨不现换反墨;用反墨不现换正墨;心之所至,手亦至 焉;心之所不至,手亦至焉;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心之所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 圣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神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者,文章之化 境也。夫文章至于心手皆不至,则是其纸上无字、无句、无局、无思者也。而独能令千 万世下人之读吾文者,其心头眼底乃窅育有思,乃摇摇有局,乃铿铿有句,而烨烨有字 则是其提笔临纸之时,才以绕其前,才以绕其后,而非陡然卒然之事也。故依世人之所
遂至灾害蔓延不可复救,则是汉人之罪终不活也。呜呼!君子之至于斯也,听之则不可, 禁之则不能,其又将以何法治之与哉?曰:吾闻之,圣人之作书也以德,古人之作书也 以才。知圣人之作书以德,则知六经皆圣人之糟粕,读者贵乎神而明之,而不得栉比字 句,以为从事于经学也。知古人之作书以才,则知诸家皆鼓舞其菁华,览者急须搴裳去 之,而不得捃拾齿牙以为谭言之微中也。于圣人之书而能神而明之者,吾知其而今而后 始不敢于《易》之下作《易》传,《书》之下作《书》传,《诗》之下作《诗》传,《礼》 之下作《礼》传,《春秋》之下作《春秋》传也。何也?诚愧其德之不合,而惧章句之 未安,皆当大拂于圣人之心也。于诸家之书而诚能搴裳去之者,吾知其而今而后始不肯 于《庄》之后作广《庄》,《骚》之后作续《骚》,《史》之后作后《史》,《诗》之 后作拟《诗》,稗官之后作新稗官也。何也?诚耻其才之不逮,而徒唾沫之相袭,是真 不免于古人之奴也。夫扬汤而不得冷,则不如且莫进薪;避影而影愈多,则不如教之勿 趋也。恶人作书,而示之以圣人之德,与夫古人之才者,盖为游于圣门者难为言,观于 才子之林者难为文,是亦止薪勿趋之道也。然圣人之德,实非夫人之能事;非夫人之能 事,则非予小子今日之所敢及也。彼古人之才,或犹夫人之能事;犹夫人之能事,则庶 几予小子不揣之所得及也。夫古人之才也者,世不相延,人不相及。庄周有庄周之才, 屈平有屈平之才,马迁有马迁之才,杜甫有杜甫之才,降而至于施耐庵有施耐庵之才, 董解元有董解元之才。才之为言材也。凌云蔽日之姿,其初本于破核分荚;于破核分荚 之时,具有凌云蔽日之势;于凌云蔽日之时,不出破核分荚之势,此所谓材之说也。又 才之为言裁也。有全锦在手,无全锦在目;无全衣在目,有全衣在心;见其领,知其袖; 见其襟,知其帔也。夫领则非袖,而襟则非帔,然左右相就,前后相合,离然各异,而 宛然共成者,此所谓裁之说也。今天下之人,徒知有才者始能构思,而不知古人用才乃 绕乎构思以后;徒知有人者始能立局,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绕乎立局以后;徒知有才者始 能琢句,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绕乎琢句以后;徒知有才者始能安字,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绕 乎安字以后。此苟且与慎重之辩也。言有才始能构思、立局、琢句而安字者,此其人, 外未尝矜式于珠玉,内未尝经营于惨淡,隤然放笔,自以为是,而不知彼之所为才实非 古人之所为才,正是无法于手而又无耻于心之事也。言其才绕乎构思以前、构思以后, 乃至绕乎布局、琢句、安字以前以后者,此其人,笔有左右,墨有正反;用左笔不安换 右笔,用右笔不安换左笔;用正墨不现换反墨;用反墨不现换正墨;心之所至,手亦至 焉;心之所不至,手亦至焉;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心之所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 圣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神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焉者,文章之化 境也。夫文章至于心手皆不至,则是其纸上无字、无句、无局、无思者也。而独能令千 万世下人之读吾文者,其心头眼底乃窅窅有思,乃摇摇有局,乃铿铿有句,而烨烨有字, 则是其提笔临纸之时,才以绕其前,才以绕其后,而非陡然卒然之事也。故依世人之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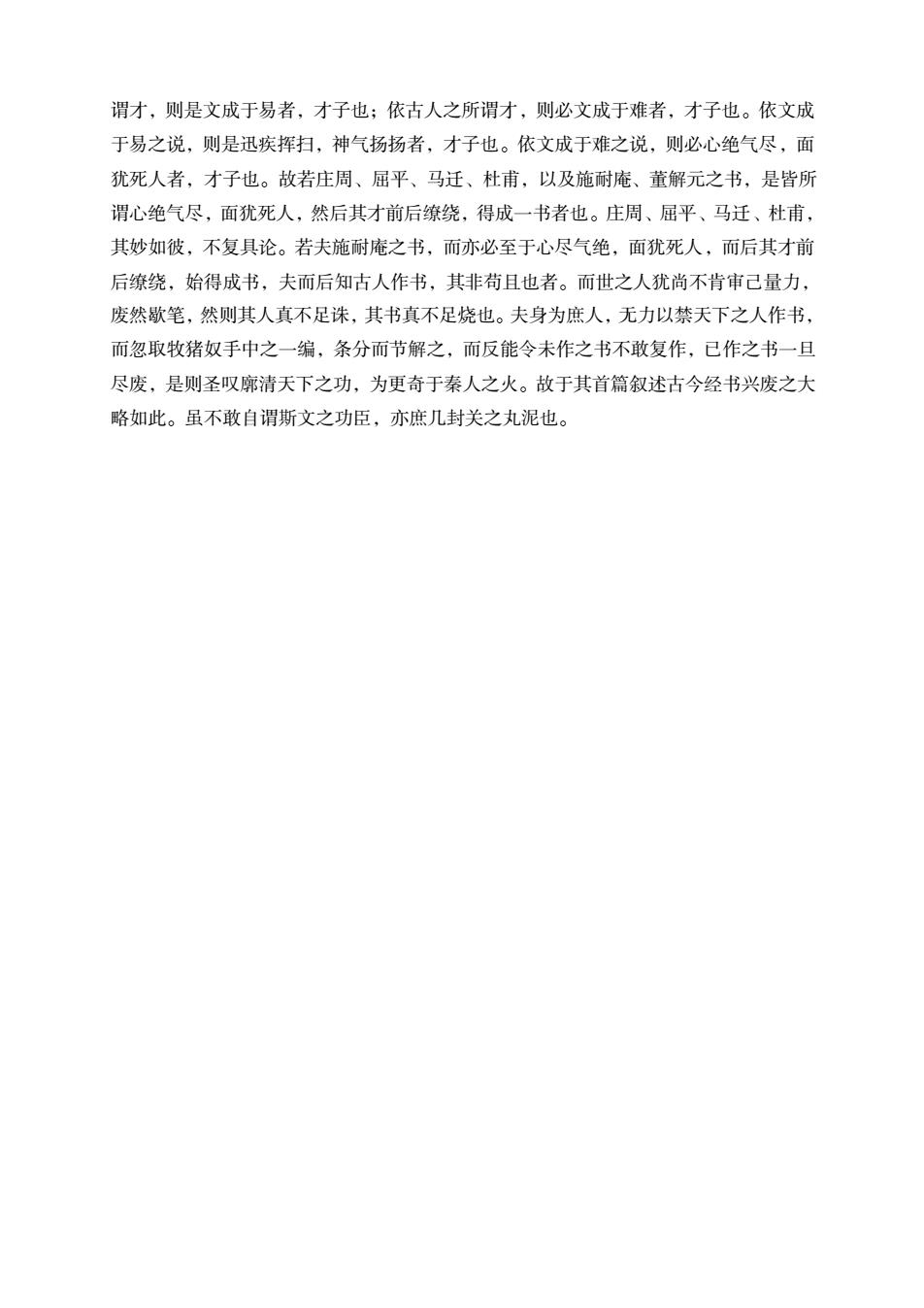
谓才,则是文成于易者,才子也:依古人之所谓才,则必文成于难者,才子也。依文成 于易之说,则是迅疾挥扫,神气扬扬者,才子也。依文成于难之说,则必心绝气尽,面 犹死人者,才子也。故若庄周、屈平、马迁、杜甫,以及施耐庵、董解元之书,是皆所 谓心绝气尽,面犹死人,然后其才前后缭绕,得成一书者也。庄周、屈平、马迁、杜甫, 其妙如彼,不复具论。若夫施耐庵之书,而亦必至于心尽气绝,面犹死人,而后其才前 后缭绕,始得成书,夫而后知古人作书,其非苟且也者。而世之人犹尚不肯审己量力, 废然歇笔,然则其人真不足诛,其书真不足烧也。夫身为庶人,无力以禁天下之人作书, 而忽取牧猪奴手中之一编,条分而节解之,而反能令未作之书不敢复作,已作之书一旦 尽废,是则圣叹席清天下之功,为更奇于秦人之火。故于其首篇叙述古今经书兴废之大 略如此。虽不敢自谓斯文之功臣,亦庶几封关之丸泥也
谓才,则是文成于易者,才子也;依古人之所谓才,则必文成于难者,才子也。依文成 于易之说,则是迅疾挥扫,神气扬扬者,才子也。依文成于难之说,则必心绝气尽,面 犹死人者,才子也。故若庄周、屈平、马迁、杜甫,以及施耐庵、董解元之书,是皆所 谓心绝气尽,面犹死人,然后其才前后缭绕,得成一书者也。庄周、屈平、马迁、杜甫, 其妙如彼,不复具论。若夫施耐庵之书,而亦必至于心尽气绝,面犹死人,而后其才前 后缭绕,始得成书,夫而后知古人作书,其非苟且也者。而世之人犹尚不肯审己量力, 废然歇笔,然则其人真不足诛,其书真不足烧也。夫身为庶人,无力以禁天下之人作书, 而忽取牧猪奴手中之一编,条分而节解之,而反能令未作之书不敢复作,已作之书一旦 尽废,是则圣叹廓清天下之功,为更奇于秦人之火。故于其首篇叙述古今经书兴废之大 略如此。虽不敢自谓斯文之功臣,亦庶几封关之丸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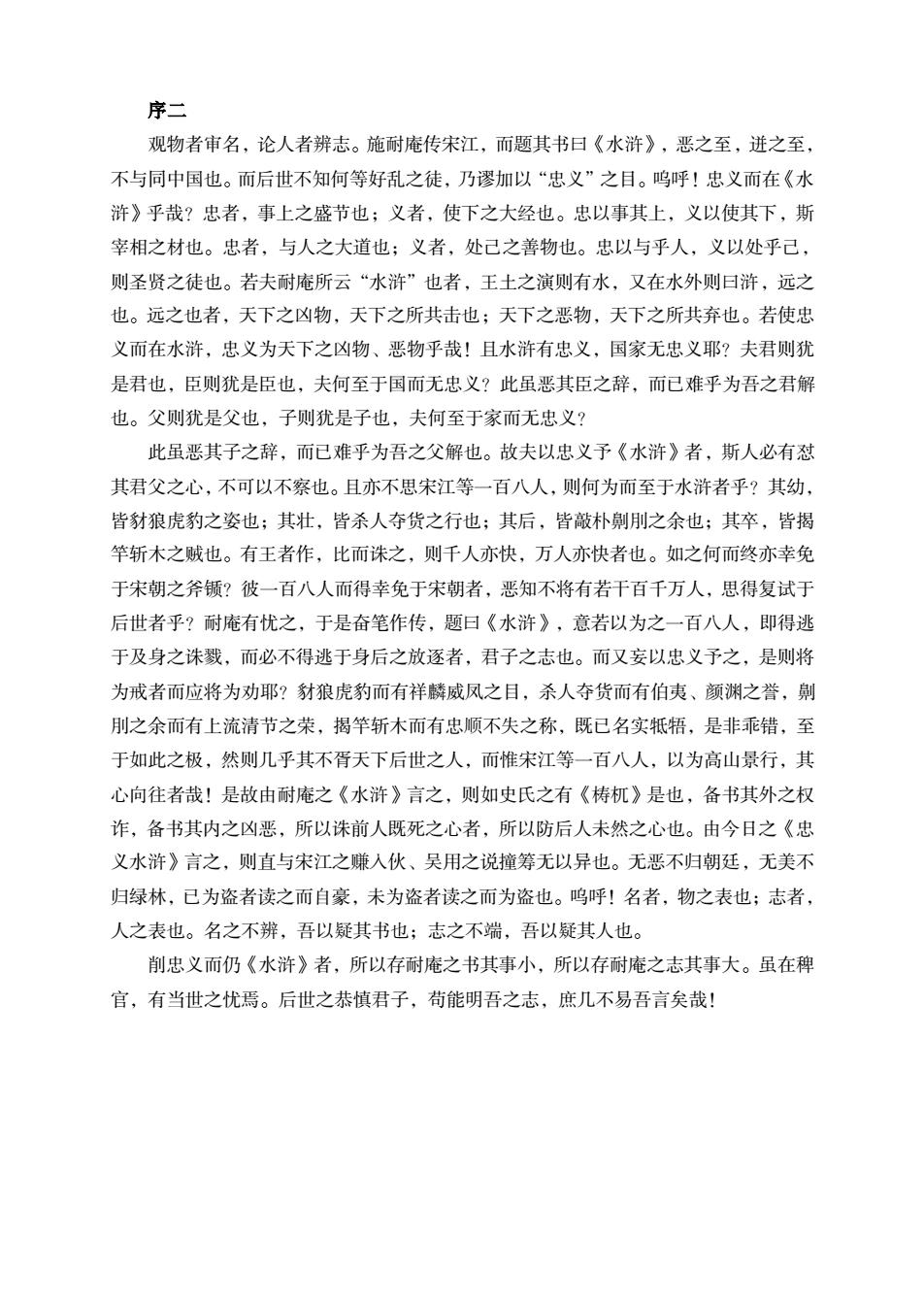
序二 观物者审名,论人者辨志。施耐庵传宋江,而题其书日《水浒》,恶之至,迸之至, 不与同中国也。而后世不知何等好乱之徒,乃谬加以“忠义”之目。鸣呼!忠义而在《水 浒》乎哉?忠者,事上之盛节也;义者,使下之大经也。忠以事其上,义以使其下,斯 宰相之材也。忠者,与人之大道也;义者,处已之善物也。忠以与乎人,义以处乎已, 则圣贤之徒也。若夫耐庵所云“水浒”也者,王土之演则有水,又在水外则日浒,远之 也。远之也者,天下之凶物,天下之所共击也;天下之恶物,天下之所共弃也。若使忠 义而在水浒,忠义为天下之凶物、恶物乎哉!且水浒有忠义,国家无忠义耶?夫君则犹 是君也,臣则犹是臣也,夫何至于国而无忠义?此虽恶其臣之辞,而已难乎为吾之君解 也。父则犹是父也,子则犹是子也,夫何至于家而无忠义? 此虽恶其子之辞,而已难乎为吾之父解也。故夫以忠义予《水浒》者,斯人必有怼 其君父之心,不可以不察也。且亦不思宋江等一百八人,则何为而至于水浒者乎?其幼, 皆豺狼虎豹之姿也;其壮,皆杀人夺货之行也;其后,皆敲朴劓刖之余也;其卒,皆揭 竿斩木之贼也。有王者作,比而诛之,则千人亦快,万人亦快者也。如之何而终亦幸免 于宋朝之斧领?彼一百八人而得幸免于宋朝者,恶知不将有若干百千万人,思得复试于 后世者乎?耐庵有忧之,于是奋笔作传,题日《水浒》,意若以为之一百八人,即得逃 于及身之诛戮,而必不得逃于身后之放逐者,君子之志也。而又妄以忠义予之,是则将 为戒者而应将为劝耶?豺狼虎豹而有祥麟威风之目,杀人夺货而有伯夷、颜渊之誉,劓 刑之余而有上流清节之荣,揭竿斩木而有忠顺不失之称,既已名实牴牾,是非乖错,至 于如此之极,然则儿乎其不胥天下后世之人,而惟宋江等一百八人,以为高山景行,其 心向往者哉!是故由耐庵之《水浒》言之,则如史氏之有《梼机》是也,备书其外之权 诈,备书其内之凶恶,所以诛前人既死之心者,所以防后人未然之心也。由今日之《忠 义水浒》言之,则直与宋江之赚入伙、吴用之说撞筹无以异也。无恶不归朝廷,无美不 归绿林,已为盗者读之而自豪,未为盗者读之而为盗也。呜呼!名者,物之表也;志者, 人之表也。名之不辨,吾以疑其书也;志之不端,吾以疑其人也。 削忠义而仍《水浒》者,所以存耐庵之书其事小,所以存耐庵之志其事大。虽在稗 官,有当世之忧焉。后世之恭慎君子,苟能明吾之志,庶几不易吾言矣哉!
序二 观物者审名,论人者辨志。施耐庵传宋江,而题其书曰《水浒》,恶之至,迸之至, 不与同中国也。而后世不知何等好乱之徒,乃谬加以“忠义”之目。呜呼!忠义而在《水 浒》乎哉?忠者,事上之盛节也;义者,使下之大经也。忠以事其上,义以使其下,斯 宰相之材也。忠者,与人之大道也;义者,处己之善物也。忠以与乎人,义以处乎己, 则圣贤之徒也。若夫耐庵所云“水浒”也者,王土之演则有水,又在水外则曰浒,远之 也。远之也者,天下之凶物,天下之所共击也;天下之恶物,天下之所共弃也。若使忠 义而在水浒,忠义为天下之凶物、恶物乎哉!且水浒有忠义,国家无忠义耶?夫君则犹 是君也,臣则犹是臣也,夫何至于国而无忠义?此虽恶其臣之辞,而已难乎为吾之君解 也。父则犹是父也,子则犹是子也,夫何至于家而无忠义? 此虽恶其子之辞,而已难乎为吾之父解也。故夫以忠义予《水浒》者,斯人必有怼 其君父之心,不可以不察也。且亦不思宋江等一百八人,则何为而至于水浒者乎?其幼, 皆豺狼虎豹之姿也;其壮,皆杀人夺货之行也;其后,皆敲朴劓刖之余也;其卒,皆揭 竿斩木之贼也。有王者作,比而诛之,则千人亦快,万人亦快者也。如之何而终亦幸免 于宋朝之斧锧?彼一百八人而得幸免于宋朝者,恶知不将有若干百千万人,思得复试于 后世者乎?耐庵有忧之,于是奋笔作传,题曰《水浒》,意若以为之一百八人,即得逃 于及身之诛戮,而必不得逃于身后之放逐者,君子之志也。而又妄以忠义予之,是则将 为戒者而应将为劝耶?豺狼虎豹而有祥麟威凤之目,杀人夺货而有伯夷、颜渊之誉,劓 刖之余而有上流清节之荣,揭竿斩木而有忠顺不失之称,既已名实牴牾,是非乖错,至 于如此之极,然则几乎其不胥天下后世之人,而惟宋江等一百八人,以为高山景行,其 心向往者哉!是故由耐庵之《水浒》言之,则如史氏之有《梼杌》是也,备书其外之权 诈,备书其内之凶恶,所以诛前人既死之心者,所以防后人未然之心也。由今日之《忠 义水浒》言之,则直与宋江之赚入伙、吴用之说撞筹无以异也。无恶不归朝廷,无美不 归绿林,已为盗者读之而自豪,未为盗者读之而为盗也。呜呼!名者,物之表也;志者, 人之表也。名之不辨,吾以疑其书也;志之不端,吾以疑其人也。 削忠义而仍《水浒》者,所以存耐庵之书其事小,所以存耐庵之志其事大。虽在稗 官,有当世之忧焉。后世之恭慎君子,苟能明吾之志,庶几不易吾言矣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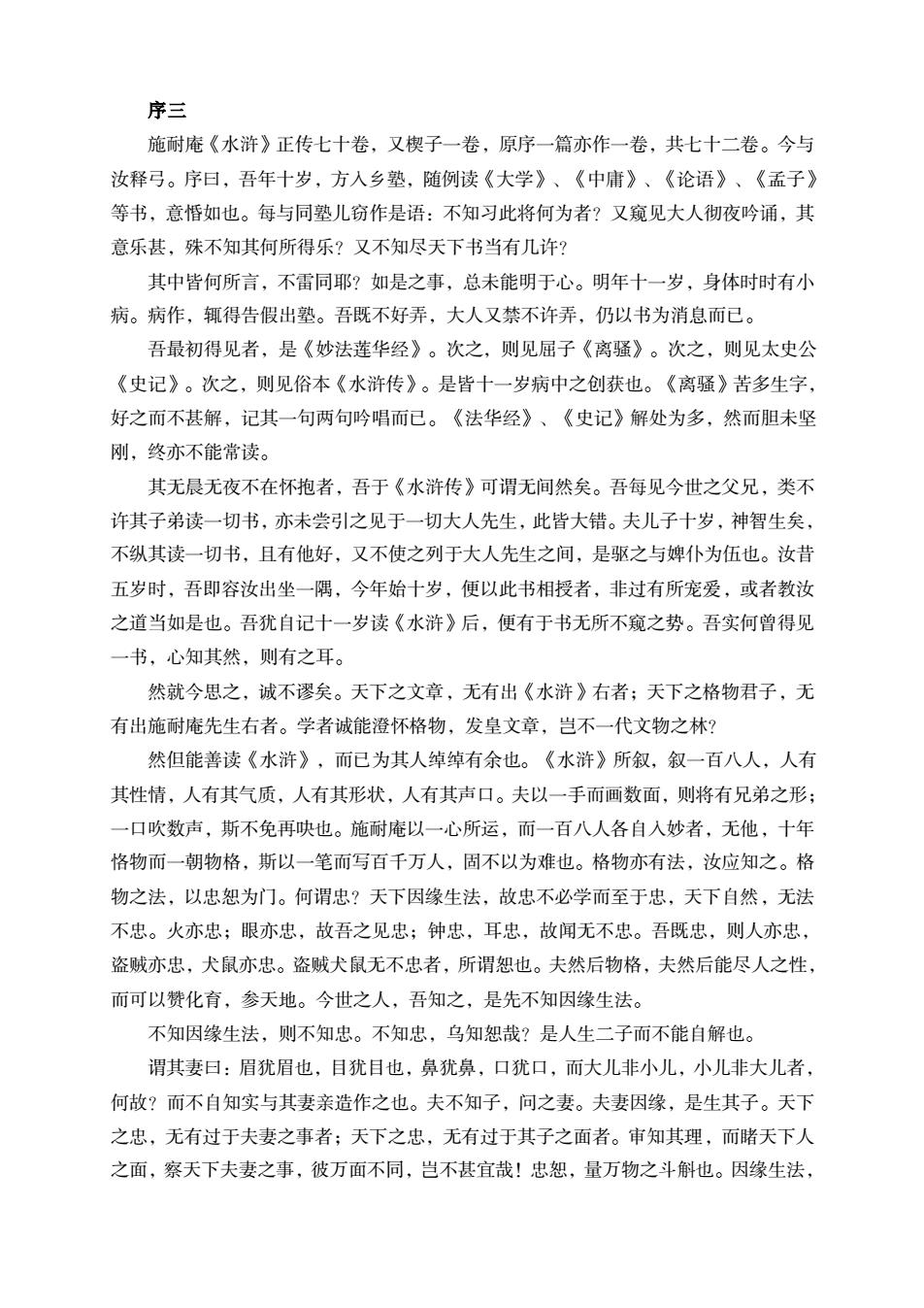
序三 施耐庵《水浒》正传七十卷,又楔子一卷,原序一篇亦作一卷,共七十二卷。今与 汝释弓。序日,吾年十岁,方入乡塾,随例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等书,意悟如也。每与同塾儿窃作是语:不知习此将何为者?又窥见大人彻夜吟诵,其 意乐甚,殊不知其何所得乐?又不知尽天下书当有几许? 其中皆何所言,不雷同耶?如是之事,总未能明于心。明年十一岁,身体时时有小 病。病作,辄得告假出塾。吾既不好弄,大人又禁不许弄,仍以书为消息而已。 吾最初得见者,是《妙法莲华经》。次之,则见屈子《离骚》。次之,则见太史公 《史记》。次之,则见俗本《水浒传》。是皆十一岁病中之创获也。《离骚》苦多生字, 好之而不甚解,记其一句两句吟唱而已。《法华经》、《史记》解处为多,然而胆未坚 刚,终亦不能常读。 其无晨无夜不在怀抱者,吾于《水浒传》可谓无间然矣。吾每见今世之父兄,类不 许其子弟读一切书,亦未尝引之见于一切大人先生,此皆大错。夫儿子十岁,神智生矣, 不纵其读一切书,且有他好,又不使之列于大人先生之间,是驱之与婢仆为伍也。汝昔 五岁时,吾即容汝出坐一隅,今年始十岁,便以此书相授者,非过有所宠爱,或者教汝 之道当如是也。吾犹自记十一岁读《水浒》后,便有于书无所不窥之势。吾实何曾得见 一书,心知其然,则有之耳。 然就今思之,诚不谬矣。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 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学者诚能澄怀格物,发皇文章,岂不一代文物之林? 然但能善读《水浒》,而已为其人绰绰有余也。《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 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夫以一手而画数面,则将有兄弟之形: 一口吹数声,斯不免再映也。施耐庵以一心所运,而一百八人各自人妙者,无他,十年 格物而一朝物格,斯以一笔而写百千万人,固不以为难也。格物亦有法,汝应知之。格 物之法,以忠恕为门。何谓忠?天下因缘生法,故忠不必学而至于忠,天下自然,无法 不忠。火亦忠;眼亦忠,故吾之见忠;钟忠,耳忠,故闻无不忠。吾既忠,则人亦忠, 盗贼亦忠,犬鼠亦忠。盗贼犬鼠无不忠者,所谓恕也。夫然后物格,夫然后能尽人之性, 而可以赞化育,参天地。今世之人,吾知之,是先不知因缘生法。 不知因缘生法,则不知忠。不知忠,乌知恕哉?是人生二子而不能自解也。 谓其妻日:眉犹眉也,目犹目也,鼻犹鼻,口犹口,而大儿非小儿,小儿非大儿者 何故?而不自知实与其妻亲造作之也。夫不知子,问之妻。夫妻因缘,是生其子。天下 之忠,无有过于夫妻之事者;天下之忠,无有过于其子之面者。审知其理,而睹天下人 之面,察天下夫妻之事,彼万面不同,岂不甚宜哉!忠恕,量万物之斗斛也。因缘生法
序三 施耐庵《水浒》正传七十卷,又楔子一卷,原序一篇亦作一卷,共七十二卷。今与 汝释弓。序曰,吾年十岁,方入乡塾,随例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等书,意惛如也。每与同塾儿窃作是语:不知习此将何为者?又窥见大人彻夜吟诵,其 意乐甚,殊不知其何所得乐?又不知尽天下书当有几许? 其中皆何所言,不雷同耶?如是之事,总未能明于心。明年十一岁,身体时时有小 病。病作,辄得告假出塾。吾既不好弄,大人又禁不许弄,仍以书为消息而已。 吾最初得见者,是《妙法莲华经》。次之,则见屈子《离骚》。次之,则见太史公 《史记》。次之,则见俗本《水浒传》。是皆十一岁病中之创获也。《离骚》苦多生字, 好之而不甚解,记其一句两句吟唱而已。《法华经》、《史记》解处为多,然而胆未坚 刚,终亦不能常读。 其无晨无夜不在怀抱者,吾于《水浒传》可谓无间然矣。吾每见今世之父兄,类不 许其子弟读一切书,亦未尝引之见于一切大人先生,此皆大错。夫儿子十岁,神智生矣, 不纵其读一切书,且有他好,又不使之列于大人先生之间,是驱之与婢仆为伍也。汝昔 五岁时,吾即容汝出坐一隅,今年始十岁,便以此书相授者,非过有所宠爱,或者教汝 之道当如是也。吾犹自记十一岁读《水浒》后,便有于书无所不窥之势。吾实何曾得见 一书,心知其然,则有之耳。 然就今思之,诚不谬矣。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 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学者诚能澄怀格物,发皇文章,岂不一代文物之林? 然但能善读《水浒》,而已为其人绰绰有余也。《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 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夫以一手而画数面,则将有兄弟之形; 一口吹数声,斯不免再吷也。施耐庵以一心所运,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者,无他,十年 恪物而一朝物格,斯以一笔而写百千万人,固不以为难也。格物亦有法,汝应知之。格 物之法,以忠恕为门。何谓忠?天下因缘生法,故忠不必学而至于忠,天下自然,无法 不忠。火亦忠;眼亦忠,故吾之见忠;钟忠,耳忠,故闻无不忠。吾既忠,则人亦忠, 盗贼亦忠,犬鼠亦忠。盗贼犬鼠无不忠者,所谓恕也。夫然后物格,夫然后能尽人之性, 而可以赞化育,参天地。今世之人,吾知之,是先不知因缘生法。 不知因缘生法,则不知忠。不知忠,乌知恕哉?是人生二子而不能自解也。 谓其妻曰:眉犹眉也,目犹目也,鼻犹鼻,口犹口,而大儿非小儿,小儿非大儿者, 何故?而不自知实与其妻亲造作之也。夫不知子,问之妻。夫妻因缘,是生其子。天下 之忠,无有过于夫妻之事者;天下之忠,无有过于其子之面者。审知其理,而睹天下人 之面,察天下夫妻之事,彼万面不同,岂不甚宜哉!忠恕,量万物之斗斛也。因缘生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