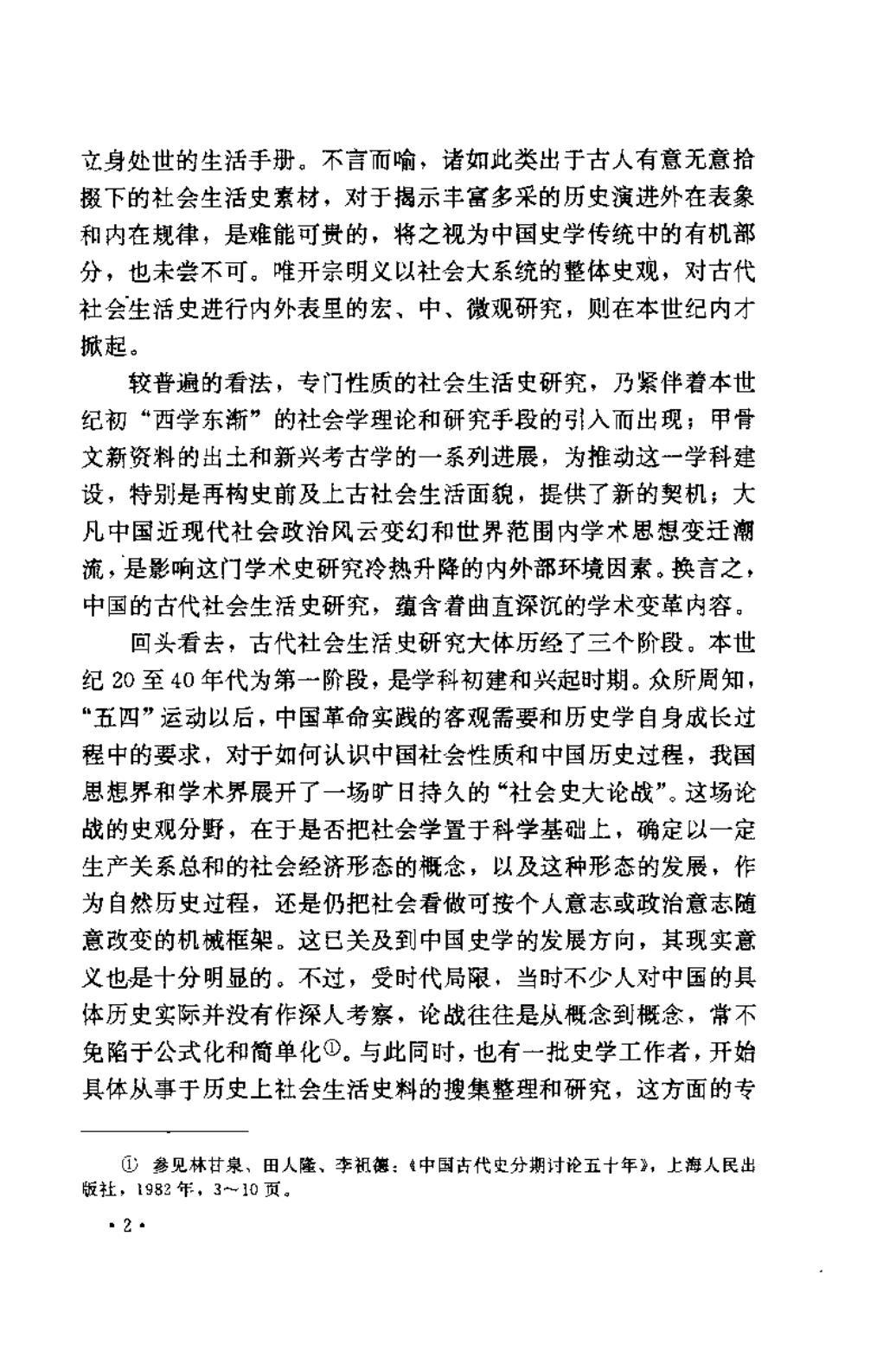
立身处世的生活手册。不言而喻,诸如此类出于古人有意无意拾 掇下的社会生活史素材,对于揭示丰富多采的历史演进外在表象 和内在规律,是难能可贵的,将之视为中国史学传统中的有机部 分,也未尝不可。唯开宗明义以社会大系统的整体史观,对古代 社会生活史进行内外表里的宏、中、微观研究,则在本世纪内才 掀起。 较普遍的看法,专门性质的社会生活史研究,乃紧伴着本世 纪初“西学东渐”的社会学理论和研究手段的引入而出现;甲骨 文新资料的出土和新兴考古学的一系列进展,为推动这一学科建 设,特别是再构史前及上古社会生活面貌,提供了新的契机;大 凡中国近现代社会政治风云变幻和世界范围内学术思想变迁潮 流,是影响这门学术史研究冷热升降的内外部环境因素。换言之, 中国的古代社会生活史研究,蕴含着曲直深沉的学术变革内容。 回头看去,古代社会生活史研究大体历经了三个阶段。本世 纪20至40年代为第一阶段,是学科初建和兴起时期。众所周知,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革命实践的客观需要和历史学自身成长过 程中的要求,对于如何认识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历史过程,我国 思想界和学术界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社会史大论战”。这场论 战的史观分野,在于是否把社会学置于科学基础上,确定以一定 生产关系总和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以及这种形态的发展,作 为自然历史过程,还是仍把社会看做可按个人意志或政治意志随 意改变的机械框架。这已关及到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其现实意 义也是十分明显的。不过,受时代局限,当时不少人对中国的具 体历史实际并没有作深人考察,论战往往是从概念到概念,常不 免陷于公式化和简单化①。与此同时,也有一批史学工作者,开始 具体从事于历史上社会生活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这方面的专 ①心参见林甘泉、田人隆、李祖德: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上海人民出 版社,1982年,3一10页。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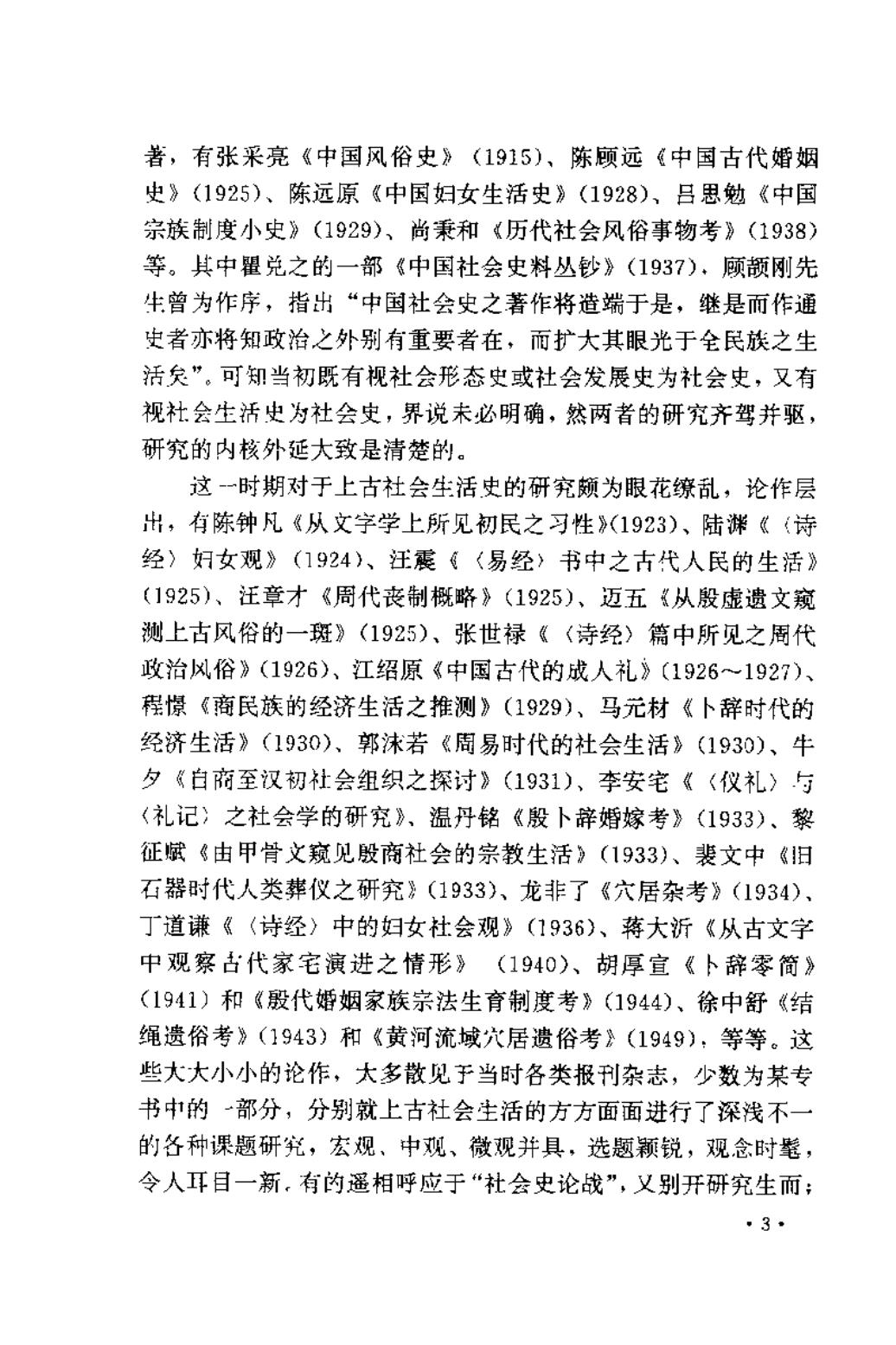
者,有张采亮《中国风俗史》(1915)、陈顾远《中国古代婚姻 史》(1925)、陈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1928)、吕思勉《中国 宗族制度小史》(1929)、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1938) 等。其中瞿兑之的一部《中国社会史料丛钞》(1937),顾颉刚先 生曾为作序,指出“中国社会史之著作将造端于是,继是而作通 史者亦将知政治之外别有重要者在,而扩大其眼光于全民族之生 活矣”。可知当初既有视社会形态史或社会发展史为社会史,又有 视社会生活史为社会史,界说未必明确,然两者的研究齐驾并驱, 研究的内核外延大致是清楚的。 这一时期对于上古社会生活史的研究颇为眼花缭乱,论作层 出,有陈钟凡《从文字学上所见初民之习性》(1923)、陆渊《(诗 经〉妇女观》(1924)、汪震《〈易经〉书中之古代人民的生活》 (1925)、汪章才《周代丧制概路》(1925)、迈五《从殷虚遗文窥 测上古风俗的一斑》(1925)、张世禄《〈诗经〉篇中所见之周代 政治风俗》(1926)、江绍原《中国古代的成人礼》(1926~1927)、 程憬《商民族的经济生活之推测》(1929)、马元材《卜辞时代的 经济生活》(1930)、郭沫若《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1930)、牛 夕《自商至汉初社会组织之探讨》(1931)、李安宅《〈仪礼〉与 (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温丹铭《殷卜辩婚嫁考》(1933)、黎 征赋《由甲骨文窥见殷商社会的宗教生活》(1933)、裴文中《旧 石器时代人类葬仪之研究》(1933)、龙非了《穴居杂考》(1934)、 丁道谦《〈诗经)中的妇女杜会观》(1936)、蒋大祈《从古文字 中观察古代家宅演进之情形》(1940)、胡厚宣《卜辞零简》 (1941)和《殷代婚姻家族宗法生育制度考》(1944)、徐中舒《结 绳遗俗考》(1943)和《黄河流域穴居遗俗考》(1949),等等。这 些大大小小的论作,大多散见于当时各类报刊杂志,少数为某专 书中的一部分,分别就上古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了深浅不一 的各种课题研究,宏规、中观、微观并具,选题颖锐,观念时髦, 令人耳目一新,有的遥相呼应于“杜会史论战”,义别开研究生而;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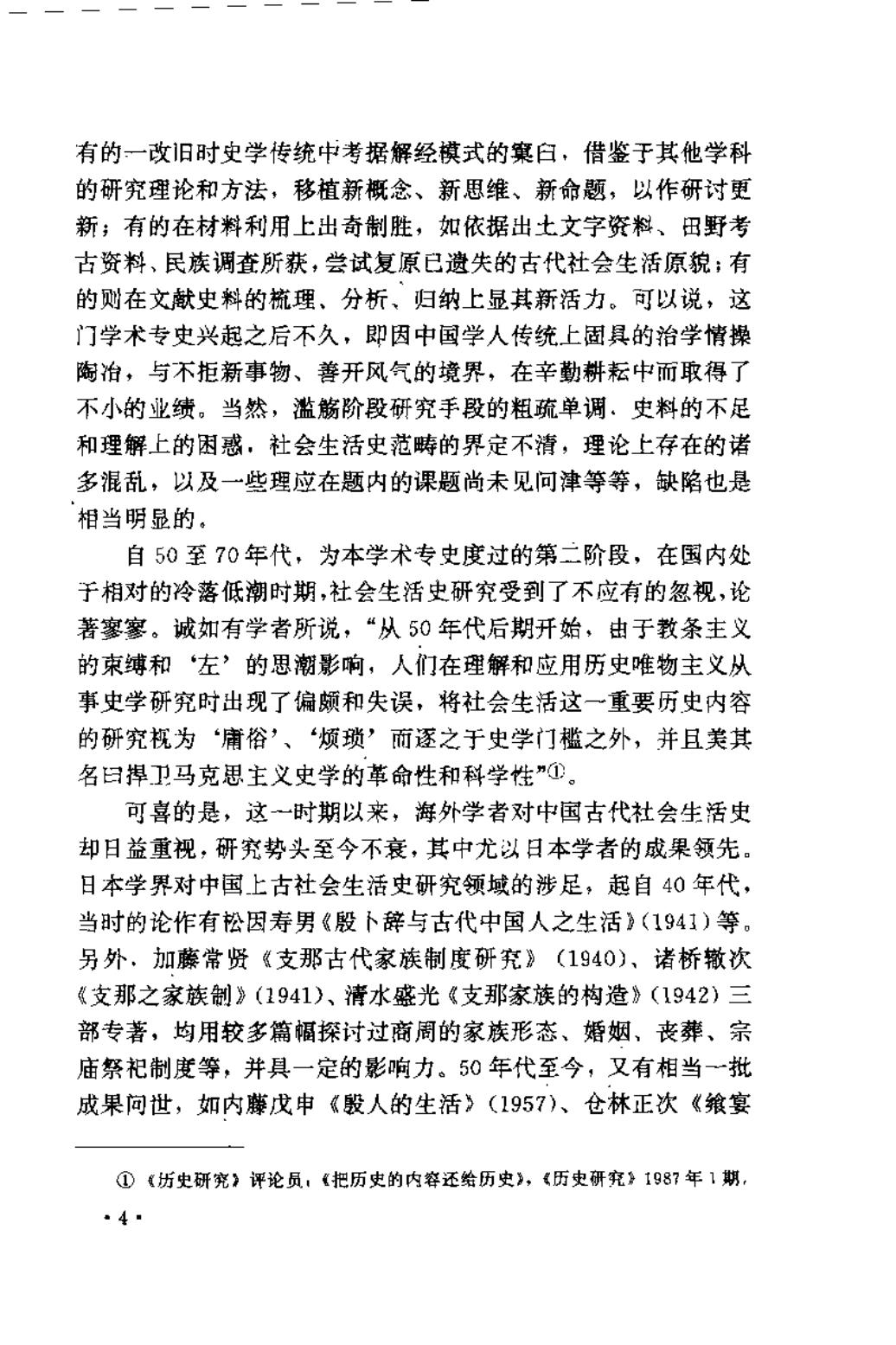
有的一改旧时史学传统中考据解经模式的窠白,借鉴于其他学科 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移植新概念、新思维、新命题,以作研讨更 新;有的在材料利用上出奇制胜,如依据出土文字资料、田野考 古资料、民族调查所获,尝试复原已遗失的古代社会生活原貌:有 的则在文献史料的杭理、分析、归纳上显其新活力。可以说,这 门学术专史兴起之后不久,即因中国学人传统上固具的治学情操 陶治,与不拒新事物、善开风气的境界,在辛勤耕耘中而取得了 不小的业绩。当然,滋觞阶段研究手段的粗疏单调、史料的不足 和理解上的困惑,社会生活史范畴的界定不清,理论上存在的诺 多混乱,以及一些理应在题内的课题尚未见问津等等,缺陷也是 相当明显的。 自50至70年代,为本学术专史度过的第二阶段,在国内处 于相对的冷落低潮时期,社会生活史研究受到了不应有的忽视,论 著寥寥。诚如有学者所说,“从5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教条主义 的束缚和‘左’的思潮影响,人们在理解和应用历史唯物主义从 事史学研究时出现了编颇和失误,将杜会生活这一重要历史内容 的研究枧为庸俗’、烦琐’而逐之于史学门槛之外,并且美其 名日捍卫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革命性和科学性”①。 可喜的是,这一时期以来,海外学者对中国古代杜会生活史 却日益重视,研究势头至今不衰,其中尤以日本学者的成果领先。 日本学界对中国上古社会生活史研究领域的涉足,起自40年代, 当时的论作有松因寿男《殷下辞与古代中国人之生活》(1941)等。 另外,加藤常贤《支那古代家族制度研究》(1940)、诸桥辙次 《支那之家族制》(1941)、清水盛光《支那家族的构造》(1942)三 部专著,均用校多篇幅探讨过商周的家族形态、婚姻、丧葬、宗 庙祭祀制度等,并具一定的影响力。50年代至今,又有相当一批 成果问世,如内藤戊申《殷人的生活》(1957)、仓林正次《飨宴 ①《历史研究》评论员,《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历史研究》198?年1期, ·4·

之研究一-仪礼篇》(1965)、泽田大多郎《从考古资料看中国商 - 汉的住居形态》(1966)、池田末利《古代中国的神与人间》 (1967)、加藤常贤《中国古代的生活与文字》(1970)、谷田孝之 《中国古代丧服的基础研究》(1970)、池田雄一中国古代的聚落 形态》(1971)、藤野岩友《中国古代的坐法》(1972)、伊藤道治 《殷代的宗教与社会》(1975)、深津胤房《古代中国人的思想与生 活》(1975~1976)、宇都宫清吉《诗经)时代的社会》(1978)、 松本雅明《中国古代的村落和生活仪礼》(1979)、笠川直树《殷 代社会的子和宗教仪礼》(1981)等。最近日本东京吉川弘文馆出 版了一部林巳奈夫撰《中国古代的生活史》(1992),该书列服饰、 往居和村落、什器和饮食、农工商业、乘物和道路、娱乐、武器 战争、文书与书物、神神、祭祀等十方面、对两汉以前社会生活 作了勾述。日本学者的论著,大都以勤于资料搜汇、辨析细腻、微 中见大和不为成见所宥而各呈风彩。 这一时期内,台湾也有一批上古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成果相继 问世,如董作宾《殷代的奴隶生活》(1950)、高去寻《殷礼的含 贝握贝》(1954)、石璋如《殷代头饰举例》(1957)、杨希枚《联 名与姓氏制度的研究》(1957)、曹德宣《殷之下辞与中国古代社 会的生活》(1965)、赵林《中国商周的婚姻、继承及世系结构》 (1970)、许倬云《周代的衣食住行》(1976)、庄万寿《上古的食 物》(1976)、贾士衡《殷周妇女生活的几个面》(1980),等等。美 籍华裔学者张光直先后撰有《中国远古时代仪式生活的若干资 料》(1960)、《有关都市生活起源》(1962)、《中国古代的饮食与 饮食具》(1973)等。一位华裔学者周策纵则撰有《生子神话与 古代中国医学》(l978)。美国吉德炜(David N.Keightley)撰有 《中国商代的嫡嗣》(1975)等文。原苏联学者刘克甫(M.B。 Kpok©B)撰有《古代中国人的社会组织形式》(1967)。韩国赵振靖 撰有《殷代的宗教信仰与祭杷》(19?1)。新加玻威特 (R.O. Whyte)写有《中国风俗之进化》(1978)。 *5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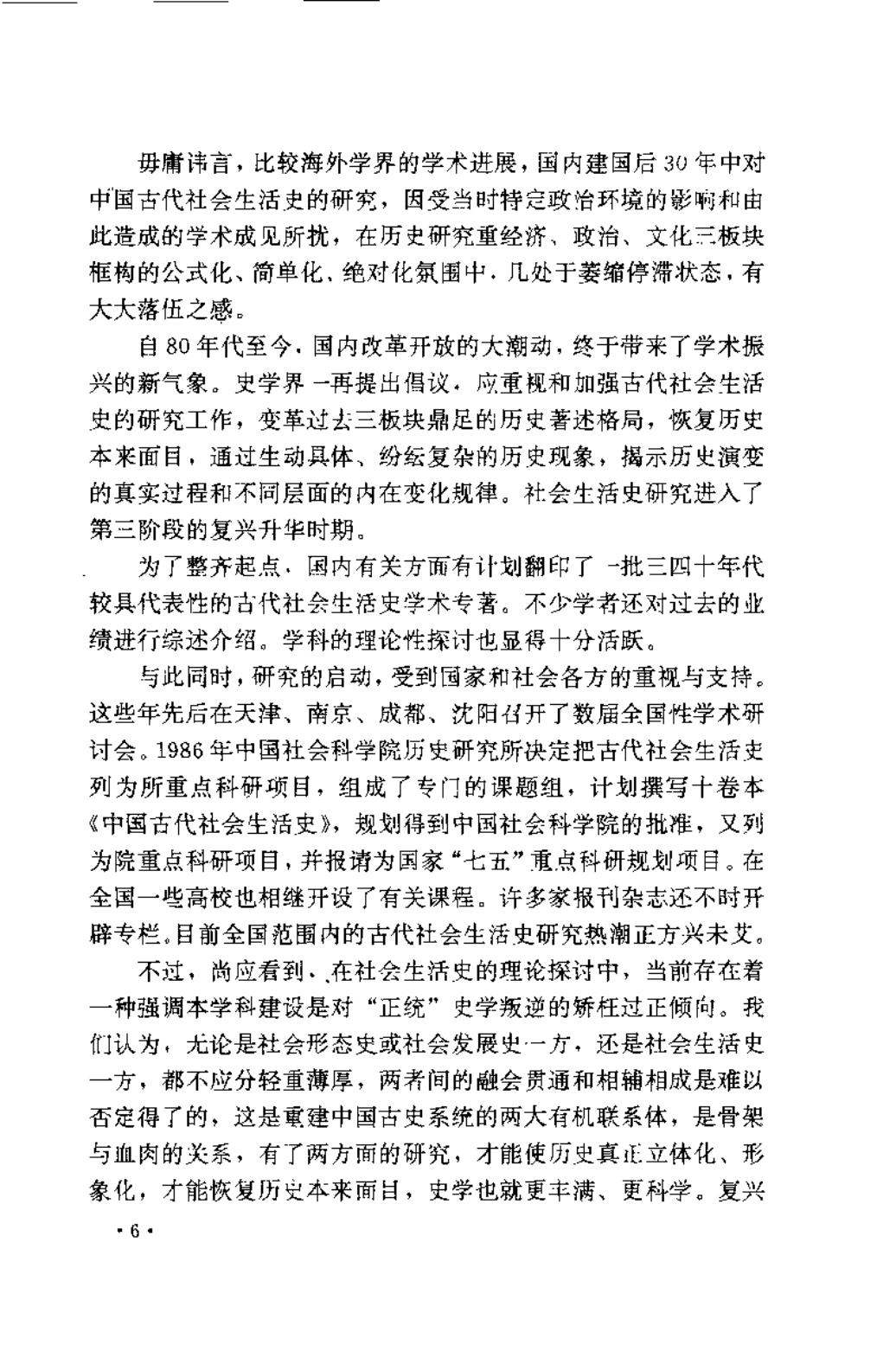
毋庸讳言,比较海外学界的学术进展,国内建国后30年中对 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的研穷,因受当时持定政治环境的影啊和由 此造成的学术成见所扰,在历史研究重经济、政治、文化三板块 框构的公式化、简单化、绝对化氛围中,几处于萎缩停滞状态,有 大大落伍之感。 自80年代至今,国内改革开放的大潮动,终于带来了学术振 兴的新气象。史学界一再提出倡议。应重视和加强古代社会生活 史的研究工作,变革过去三板块鼎足的历史著述格局,恢复历史 本来面目,通过生动具体、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揭示历史演变 的真实过程和不同层面的内在变化规律。社会生活史研究进入了 第三阶段的复兴升华时期。 为了整齐起点、国内有关方面有计划翻印了一批三四十年代 较具代表性的古代社会生活史学术专著。不少学者还对过去的业 绩进行综述介绍。学科的理论性探讨也显得十分活跃。 与此同时,研究的启动,受到国家和社会各方的重视与支持。 这些年先后在天津、南京、成都、沈阳召开了数届全国性学术研 讨会。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决定把古代社会生活吏 列为所重点科研项目,组成了专门的课题组,计划撰写十卷本 《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规刻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批准,又列 为院重点科研项自,并报请为国家“七五,”重点科研规划项目。在 全国一些高校也相继开设了有关课程。许多家报刊杂志还不时开 辟专栏。目前全国范围内的古代社会生活史研究热潮正方兴未艾。 不过,尚应看到、,在社会生活史的理论探讨中,当前存在着 一种强调本学科建设是对“正统”史学叛逆的矫枉过正倾向。我 们认为,尤论是社会形态史或社会发展史一方,还是社会生活史 一方,都不应分轻重薄厚,两者间的融会贯通和相辅相成是难以 否定得了的,这是重建中国古史系统的两大有机联系体,是骨架 与血肉的关系,有了两方面的研究,才能使历史真正:立体化、形 象化,才能恢复历史本来面甘,史学也就更丰满、更科学。复兴 6